女性作家与作品握笔的女人们
记者 | 何映宇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在烈日骄阳中再度来临。
和往年一样,作为半边天的女性作家,从来都是上海书展上美丽的风景。阿列克谢耶维奇、韩国女作家李惠敬、美国女作家加·泽文、日本女作家角田光代、乐黛云、张悦然、陈丹燕……都带来她们的新作品,她们的学识、智慧、风度为书展增色不少,她们带来的作品细腻、动人,有着迥异于男性作家的倾向与风度。
新科诺奖状元:只要发生过,就有真相!
今年最大的大牌,毫无疑问是中信出版社请来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新科状元S.A.阿列克谢耶维奇。
8月19日上午,出现在思南公馆,短发、沉稳、说话不疾不徐,她说她的每一本书采取的都是不同的方法:“当我写和战争有关的故事时,我会去和阿富汗战争有关的采访对象打交道,了解他们身上的故事。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有关人员肯定不只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居民而已,我希望尽可能地了解这一事件的影响。关于苏联解体后的这本书,就是我最新的这本:《二手时间》。我总是在寻找那些能够让人们感觉震惊的人,或者那些他们思考自己过去,也在思考未来的人。我认为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必须有一种猜测力,能猜测出这些人他们内心的所想所思。”
作为女性,她的每一本书都那么特别,打上女性这一性别的深深烙印。比如《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在书中,她写:“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作家,她坚持用女性的视角来看问题,看这个世界,所以,她很重视战争中最弱势的群体——女人和儿童。在她看来,女性,相对男性,是柔弱的。所以,在她的书中,她的视角永远是从最弱势、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女人出发,来看待所有的灾难。她谈到自己为什么要写《锌皮娃娃兵》,是为了表示抗议,抗议用男性的视角看待战争!“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我发现,这些成年人都沆瀣一气,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嗓冲出了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实文学体裁。
作为纪实文学,真实,是第一位的。这些鲜活的、第一手的素材,很容易就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受访人在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前敞开尘封已久的心扉,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把他们的内心紧紧包裹起来,不去回忆失去亲人的痛苦。可是此时,他们向这个陌生人吐露了最真实、深刻、沉痛的内心感受。
有的母亲生下了残疾的孩子,这种经历在核辐射之后很常见,但是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它就成了最可怕的厄运。
母亲和孩子,总是能轻易打动这位女性的心,也因为感动,她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文字,又进一步打动了读者。
但有时候,她又不简单的是一位女性,她似乎比男性更勇敢。她坚毅、果敢,面对强大的阻力,她的内心比普通的男性更加的强大。有几个人敢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深入切尔诺贝利,采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却肩负起男性都难以扛起的职责,光这一点,就令人心生敬意。她来到那里,某个村庄,村里的人已经全部搬走(有些村庄连同茅屋、水井、圣像都一起被埋了起来)——只留下一尊列宁纪念碑。她还记得,有一次,黄昏时分,他们乘车开进一座村庄,那里只有阵亡烈士墓,公墓和列宁纪念碑……她们等待出现双头的雏鸡、无刺的刺猬。最初,谁也不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规模,谁也不了解可以杀死你身上的未来。
她说她不敢坐在草地上,不敢吃苹果。“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怕?人类新的生态历史开始了。面对这一切,民族性已经退让到后边去了:我是什么人——是白俄罗斯女性,是俄罗斯女性——这已无关紧要。我是一个生物种类的代表,我可以像猛犸一样消逝。”
“普里皮亚季镇的一位妇女对我讲过,他们怎样通宵达旦地观赏反应堆冒起来的大火。大火五彩缤纷,像一种非人间的光彩,满天辉煌。殊不知这美——致人于死命。”
“切尔诺贝利成了生物坟场,那儿枪杀了成千上万的牲畜。离反应堆10公里,有个地方就是牲畜的集中营,庞大的坟场。把人运走了,把牲畜枪杀了,其中有狗,有猫,有奶牛,有牛犊。这是一种极其野蛮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人们坐进了装甲运输车,可是狗却站在外边望着他们。有位妇女对我说:我忘不了我的小猫是怎么哭的!”
有人宣称她看见了辐射。“我看得到辐射,是蓝色的,辐射把所有一切都毁了。”一个疯女人像塔可夫斯基《乡愁》中的疯癫教士一样在市场中喃喃自语地走着。
所有人都被动地卷入这场科技悲剧,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去反思和调查事实真相。苏联解体前这是禁忌,苏联解体后,这里似乎被人遗忘了,大多数人的看法都是:那么遥远的地方,和我有什么关系?让当局有关负责人去操心吧!真相?也许根本就没有真相。
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她的书告诉虚无的你们:不!有真相!只要发生过,就有真相!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能确定发生事情了。
乐黛云的传承和守望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女性学者乐黛云是已故的汤一介先生的夫人,这次来沪,她是为先生的遗著《我们三代人》做宣传,也向读者解读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和守望。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三代人》曾经尘封12年,用42万字的赤诚讲述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自省和三代国学大师的传承守望。“我们三代人”,指的是汤一介的祖父、清光绪十六年进士汤霖,汤一介的父亲、著名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和汤一介本人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从这三代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
在这个汤家的朋友圈中,乐黛云女士当然也是重要的成员,她既是学术家风的继承者,又是亲历者和旁观者。

在夫人乐黛云眼中,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又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不会遗憾。汤一介知识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就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知心朋友也就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不大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她是最懂汤一介的人。
汤一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乐黛云觉得他是想要留下一点历史的痕迹,给后人看看那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不要添油加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在书中,汤一介浓墨重彩写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胡适派飞机接过汤用彤和沈从文,飞机就停在北京东安市场,最后只有钱思亮走了。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老先生虽然和共产党接触不是很多,但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很清廉,和国民党不一样,由于是供给制,所以大家拿的钱也是一样的,公平、平等,在那个时代,是一缕春风。”
乐黛云说:“那时候大家是真心热爱这个国家。”
乐黛云觉得汤一介很想分析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而他父亲汤用彤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汤一介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她和贺麟的夫人在北大家属妇女会带头把家里的金银宝贝都捐出去,捐了一架飞机。
严歌苓:上海女人看上海男人
虽然严歌苓女士没有来到书展会展现场,但严歌苓的最新长篇《舞男》仍然是今年上海书展上备受关注的一本书。
1958年出生的严歌苓,今年已经58岁了,可在旁人看来,严歌苓的年龄似乎已定格,白色短袖连衣裙,娥眉淡扫,略施薄妆,头发简简单单在脑后挽了一个发髻,显得清新大方,又不落俗套。永远是美丽中略带忧郁的少女模样,将人生悲喜,藏在心中。
严歌苓当然是个“有故事的人”,否则,怎么能将那么多人世间的男女、生死、人性的挣扎、苍凉与繁华写得入木三分?
“大概因为我善于讲故事,也喜欢刻画人物吧。”在之前的上海发布会上,严歌苓这样淡淡地说。
可能也是太有故事性的缘故,她的小说似乎特别容易改成影视作品并大获成功。严歌苓透露,她的新作《舞男》,影视改编权的争夺可谓异常激烈。一个光怪陆离的上海滩舞场,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的两个男女,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还暗藏着她对中国社会新阶级的观察,怎么说呢?有很多卖点,让人异常期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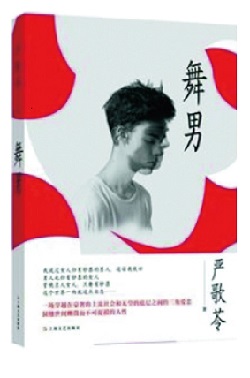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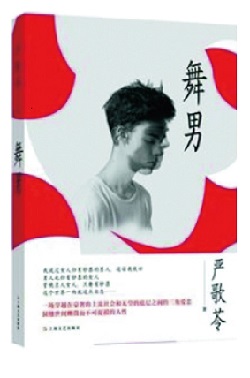
很多人都忘记了,虽然旅居海外,但严歌苓出生在上海,是上海人,父母离异后,她和弟弟严歌平留在安徽。从此,漂泊在外,但是她对上海,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感情,也许就是流淌在血管之中的那种难以割断的乡情,所以,她写上海的故事,也是顺理成章。
严歌苓用一个上世纪30年代在百乐门的舞男鬼魂的视角来看今天的男女、今天的爱情、今天性的关系,来看今天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的身份关系。
在写作的过程中,除了文学性的一面,她也有一些社会性方面的思考。严歌苓说:“我觉得中国社会新的阶层正在形成,矛盾和分歧也正在形成。现在的上海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上海,和过去的上海大不一样。我对现在上海的不同阶层:讲英语的海归、本地土著以及那些漂泊在上海、底层的外来者,他们的不同命运感兴趣。我原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社会的旁观者,现在我觉得我参与其中越来越多了,比早两年写中国本土的故事要自信得多。我每隔两个月都要回来一次,我不再是侧目而视的人了,这样,我写的时候就非常有激情,牢牢把控着故事、人物和氛围。应该讲,这本《舞男》是我写当代生活最有自信、最有把握的一本书。”
张悦然破茧成蝶
距上一本长篇小说《誓鸟》的出版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张悦然长篇小说《茧》一经在《收获》发表,就引起了媒体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批评家李敬泽就认为,张悦然的《茧》是80后共同的书,也是80后与父辈对话的书,也是80后可以向自己的孩子讲述的故事。
曾经,张悦然是80后青春文学的代名词,她主编的《鲤》走的是文艺路线,但其中还是有很浓重的青春文学的味道,记述和体现的,是她们那一代人的任性、叛逆、迷茫、爱与恨、执着与叹息,而这一回,张悦然破茧成蝶,直面历史,证明了一个作家的成长与成熟,也被认为是张悦然的回归与超越。
 这一次,张悦然的文字依然保有女性作家灵动惊艳的婉转,同时,又多了一份谦卑的质朴,她的故事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圈子,落下烟尘,逼近现场,因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用代际来区分作家的人群类别,是一种非常机械的手法,1979年出生的作家和1980年出生的作家,只相差一岁,却被划入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因而人生际遇也不同,这公平吗?难道文学界对文学的判断,只能通过年龄来进行?而张悦然的写作已经证明,80后这一代,也可以摆脱偶像派的包袱,也可以像更年长一些的作家一样,进入纯粹文学的核心世界。当然,这需要勇气。
这一次,张悦然的文字依然保有女性作家灵动惊艳的婉转,同时,又多了一份谦卑的质朴,她的故事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圈子,落下烟尘,逼近现场,因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用代际来区分作家的人群类别,是一种非常机械的手法,1979年出生的作家和1980年出生的作家,只相差一岁,却被划入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因而人生际遇也不同,这公平吗?难道文学界对文学的判断,只能通过年龄来进行?而张悦然的写作已经证明,80后这一代,也可以摆脱偶像派的包袱,也可以像更年长一些的作家一样,进入纯粹文学的核心世界。当然,这需要勇气。 面对历史的沉重,张悦然没有像青春小说家那样避重就轻,她从一个80后女性作家的角度,重新思考历史的血脉,如何辗转在几代人身上流淌,也使得80后的创作瞬见变得开阔辽远。而在故事的自然推进中,二十年前风雨之夜的那一枚钉子,它变得越来越尖利,在某一个时间的节点上,就亮出它的牙齿。
《茧》结构上也很有特色,这部小说采用了双声复调的叙事结构。张悦然将一桩发生在“文革”时期骇人听闻的罪案不断抽丝剥茧,还原历史场景,同时呈现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张悦然用她绵密而婉倩的文字,展示了一个历史的伤口。她提醒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历史的阴影比想象的要长,愈合它的伤口,也比想象中艰难。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