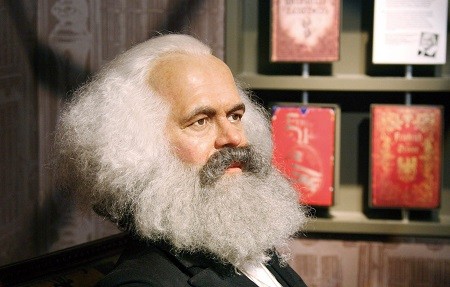朦胧诗:黑夜中的一盏青灯
阅读提示:即使在生活的底层,诗歌也未缺席。在劳作之余,他们用诗歌记录下最真实的生活。电焊工诗人陈开翔说:“感谢文字,让我活成一个有诗意的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批年轻诗人开始崛起于诗坛,给诗苑带来了一股新异的诗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食指、北岛、舒婷、芒克、顾城、多多、江河、杨炼等一批青年诗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其中尤以“白洋淀诗歌群落”最为有名。它是在1969年至1976年间,由北京赴河北白洋淀一带插队的一批知青构成的诗人群体,主要包括芒克、多多、根子等人。由于白洋淀距北京不足二百里,各种新思潮便很快波及这里,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阅读”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等,也很快在白洋淀传阅,从而形成了适宜于诗人成长的独特人文环境,也使许多成员日后成为新诗潮的主将。“白洋淀诗群”于1976年因芒克最后一个离开白洋淀而告终结。陆续返城之后,这些诗人在1978年12月刊印了民间刊物《今天》,这是他们作为朦胧诗群体最初的半公开亮相。
由于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变革,对中国诗歌传统和欣赏习惯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朦胧诗”这一称谓,最初是略含贬义的,它在当代诗坛流行,可追溯到1980年《诗刊》第8期发表的署名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是由老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秋》所引发的:“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戏中的细节回忆。”在章明看来,此诗用语让人感到稀奇、别扭,使人产生思想紊乱,接着他又举出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作为例证,认为这类诗晦涩、怪僻,叫人读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不解之余,他写下了这篇文章,并将此类诗体姑且名之为“朦胧体”。从此,“朦胧诗”这个略含贬义的称谓,便成为日后新诗潮的具有普泛性的命名,并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论战。
而热闹过后,是沉寂。90年代后,诗歌也曾边缘化,虽然关注的人少了,但热爱诗歌的读者和写作者大有人在。
即使在生活的底层,诗歌也未缺席。在劳作之余,他们用诗歌记录下最真实的生活。电焊工诗人陈开翔说:“感谢文字,让我活成一个有诗意的人。”
90后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写下了这样的诗:
夜,好像深了/他用脚试了试/这深,没膝而过/而睡眠/却极浅极浅
——《梦想》
郑小琼的诗歌在技巧上更为圆熟,这使她更像一个冷静的知识分子,在“荒凉的角落”孤独吟唱。打工的经历为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但重要的,恐怕还不是写了什么,而是怎么写。不论是在许立志还是郑小琼的诗歌中,具象的打工经验只是诗中一些微小的种子,大量映入眼帘的,仍然是“镜中”“沉默”“疲倦”“存在”这样的词语,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或者说用“打工诗人”的标签还指称他们,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打工,是他们的一个身份、一个标签、一个背景,但呈现出的,还是纯诗,是诗歌在诗人的心中的萌发和激荡。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