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美国政府,华为用法律与“封杀令”硬刚
扛住当时业界第一的精准阻击,再度被打时适时反击获胜,直至实力强劲后主动出击……无论类型如何、局面怎样,华为都能在主要的诉讼中获得最后的优势。十几年来,华为法务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演绎了“逆袭”的传奇。
这支“常胜军”的制胜秘诀是什么?中国的各类各型企业,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又如何在法律领域打好“有准备之战”?

遭遇巨头诉讼阻击
2003年,华为的地位还只是“2002年中国电子百强”第7位。这一年刚开年不久,华为遭到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网络及电信设备制造商思科的起诉。思科指控华为非法抄袭、盗用包括源代码在内的思科软件,抄袭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其它多项专利。
思科的起诉来势汹汹。它的诉讼请求多达21项,概括起来说,就是至少要将华为的Quidway路由器彻底赶出美国市场,已经在美国的要“消灭”掉,并要华为赔偿全部直接或间接损失。这基本上是要在美国市场上,置华为于死地。
而且,虽然诉讼是向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院提起,却不只起诉了华为美国公司、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FutureWei,还把中国的华为总部列为第一被告。
这种起诉策略,挥舞起了“长臂管辖”的大棒。美国法律规定适用“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认为涉外民事案件中只要有任何相关因素与美国有关,就是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美国法院就有管辖权。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张磊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美国的“长臂管辖”实际上是以其背后的国家实力做支撑的,他们信奉“实力强则管得到”。他认为,“长臂管辖”是一种单边主义,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奉行的多边主义,不利于跨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思科这次起诉华为的真实意图,从其诉讼材料的表述中可见一斑:思科称,华为近来在美国开始销售价格比思科产品低廉的一系列Quidway路由器,而相同或类似产品已经销售到了其他国家或地区。华为在促销中宣称其产品可以在不影响运行和安全的前提下替代思科的产品。思科并不认同华为所宣称的互用性,并认为华为“克隆”思科是建立在对思科知识产权的全盘盗用上。在材料中,思科还特别引用了时任华为副总裁费敏的一段话当作“证据”:“世界上所有的顶级设备供应商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思科认为这种“学习”就是“克隆”。
“因言获罪”的手段都用上了,很显然,思科起诉华为的目的并不在于追究专利侵权,而是要打压华为。当时,华为的市场体量虽然还无法与思科相提并论,但后者已经看到了威胁。时任思科CEO钱伯斯当时就曾明确说过:“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被诉讼后,华为首先声明自己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一贯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同时也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华为的应对相当低调,停售了被思科指控含有非法盗版软件的某些产品,并将Quidway路由器从其美国网站上撤下,还表示回收在美国已售出的此类产品。
低调不等于屈服。华为动用包括法律、政府关系、商业关系等在内的大量国内外资源,全力应对思科的诉讼。在一年半之后的2004年7月28日,双方达成和解,思科撤诉。在华为并没有侵犯思科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华为同意修改其产品的命令行界面、用户手册以及帮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码,以消除思科公司的疑虑。
思科起诉华为被认为是当时中美之间最大的知识产权纠纷。这起案件以和解收场,事实上是以华为的胜利告终。思科的法律手段并没能阻碍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发展。事实上,就在被思科起诉之后的两个月,华为与美国的通信设备商3COM成立了自身控股的合资公司,全力开拓美国市场,而后者正是思科崛起之前全球网络通信市场的领导者。
《中国企业家》如此评论这起诉讼中华为的表现:“在中国企业卷入的国际商业纠纷中,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将官司打得如此酣畅淋漓。”
从反击到主动出击
如果说对思科的诉讼是防御,那么2011年面对美国IDC公司的起诉,华为无疑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当年7月,美国IDC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即 ITC)提交“337调查”的诉状;同时将华为起诉至美国特拉华州法院,称华为侵犯其在美国享有的有关3G通信的7项标准必要专利,请求责令华为停止被控侵权行为,并要求对华为公司启动“337调查”并发布全面禁止进口令、暂停及停止销售令。
“337调查”,是指ITC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为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进口贸易中的其他不公平竞争。
实际上,IDC发动诉讼的目的与此前思科所为如出一辙:为了赢得商业竞争。且看事实:2012年,ITC启动“337调查”前,IDC向华为发出最后要约:从2009年到2016年按照销售额确定支付许可费率为2%;这一许可费率与对苹果、三星等公司的许可相比,费率是它们的数十倍。
在通信标准的专利许可中,国际上通行“FRAND原则”,即公正、合理、非歧视。显然,IDC的做法不符合这项原则。对此,2011年12月,华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以IDC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提起反垄断诉讼;随后的2013年1月,华为在美国对IDC提出反诉,要求法院确定FRAND原则下的专利合理使用费。
2013年6月28日,美国ITC主审法官初裁认定IDC所诉华为的7项专利中1项无效,另外6项华为不侵权。4个月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华为诉IDC垄断一案终审判决,认定IDC公司构成垄断,赔偿华为2000万元。
对IDC反击成功后,华为开始主动出击。2016年5月,华为在美国和中国提起对三星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这些知识产权包括涉及通信技术的高价值专利和三星手机使用的软件。在之前的数年间,二者围绕智能手机的专利纠纷就一直存在。
2019年5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华为与三星最终达成了全球和解,二者将很可能对彼此拥有的专利交叉授权;而在争端中,华为一直占据技术专利权高地,这意味着华为将在这一领域比三星获取更多的专利收益。
华为在法律领域的优秀表现,源于其内部对法律部门的一贯重视。
在2003年面对思科的诉讼时,时任华为法律部部长的张旭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在华为,律师对业务的介入是很深的。”以他从前所在的国际部为例,国际业务的很多法律文件,特别是各类合同,如果没有律师的评审是不能签的。很多法律文件签署时,律师都要把第一关,比如授权文件就必须先有律师审查,行政部才能接着走下面的流程。张旭廷说:“在华为,涉及所有的对外盖公章的事情都由法律部控制。”
在风险防范方面,公司内部制定所有的政策、制度文件都必须经过律师参与,以确保合法合规。公司所有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在做重大决策时,法律部都要出具意见,说明是否能做这个决策,需要经过哪些法律程序以规避可能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华为的内部律师们有机会给公司提供建议,参与公司各种决策。
张旭廷当年提出,国外企业往往是用CEO、CFO、GC(首席律师)“三驾马车”的方式驾驭企业,GC在公司中的地位非常高,都是副总级别。实际上,今天的华为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管理架构: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同时兼任高级副总裁。
上述理念,贯穿于华为近年来的发展中。无疑,华为法律部的部门定义、职位功能的确定、人员素质的提高,是在多年来一次次的诉讼交锋中逐渐完善的。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张磊提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非商业风险两类。上述华为与思科、IDC、三星等企业的诉讼都属于处置商业风险,在这一领域,法律实际上成为企业实现自身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使用是非常复杂和成本高昂的,即使是华为这样高度重视、不断提升的企业,也要付出长久的努力。
在他看来,与华为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不同,中国的中小企业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整体的法律意识、法务能力、得到的法律保障援助等还不容乐观。“行业建立海外诉讼援助基金,以及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援助,或许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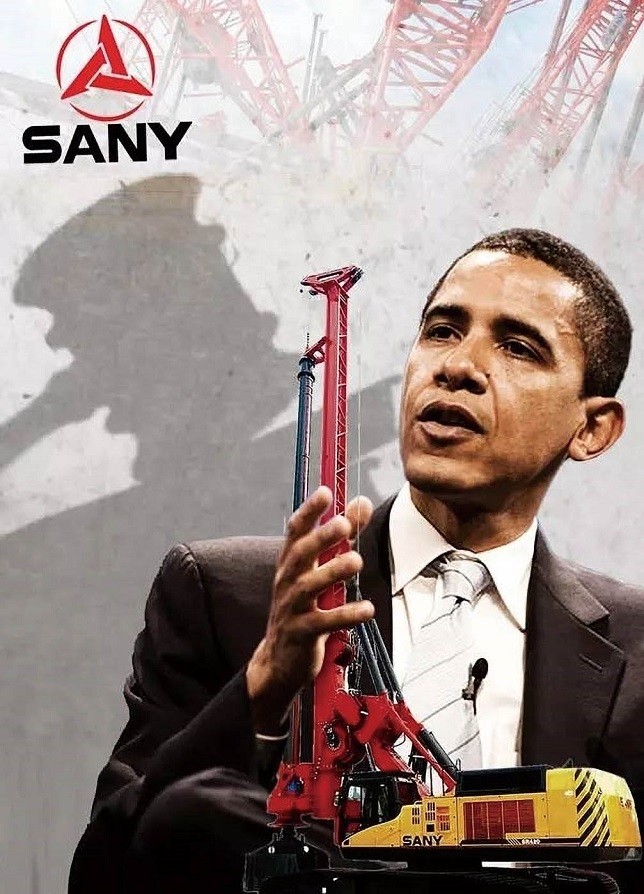
与前述的案例不同,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给华为带来的挑战,则是非商业风险,也就是政治风险。“实际上,知识产权领域的纠纷因为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本身就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的。”张磊说。
美国于2018年8月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中,不仅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还禁止政府机构与购买华为设备或服务的第三方签署合同或向其提供资助和贷款,即使这些交易对美国政府并无影响或并无关联。
对此,华为于2019年3月7日宣布针对该条款的合宪性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判令永久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
华为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第889条明确针对华为,将华为列入黑名单,损害了华为的声誉,且不给华为任何澄清的机会让其免受制裁,这是违宪的。美国对华为的攻击是有企图、带有惩罚性的。”
张磊认为,华为的作为值得认可。在他看来,解决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需要建立“分工合理、分层保护”的一整套体系,其中第一层保护就是由企业自行在海外发起诉讼或仲裁请求。
他举例说,之前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就是很好的范例。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签署总统令叫停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美国罗尔斯公司在俄勒冈州投资的风电项目。随后三一方面向美国哥伦比亚地方法院递交诉状,认为奥巴马此举违宪,未经适当的程序,剥夺了罗尔斯风电项目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并将奥巴马和美国外资委员会(CFIUS)列为共同被告。
初审被判败诉后,三一重工提起上诉。2014年7月15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三一集团胜诉。2015年11月4日,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司罗尔斯宣布与美国政府达成全面和解。罗尔斯公司撤销了对奥巴马的诉讼,美国政府也相应撤销了对罗尔斯公司强制执行总统令的诉讼。三一重工诉奥巴马案以圆满胜利告终。
张磊介绍,在企业自行诉讼之外,第二层应对是“领事保护”。在这一层中,国家对企业提供援助,但是“站在企业背后”,主要还是由企业出面来应对。
第三层则是“外交保护”,此时国家将走到前台,根据国际法规则,直接追究另一个国家的责任。他说,在这种时刻,国家的相关部门是否有成熟的预案,是保护措施成败的关键因素。
他强调,在国际法规则中,开启外交保护之前,也有“要求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即企业本身已经在外国尝试过全部的方式仍无法解决问题时,国家才直接介入,以避免激烈的国家冲突。
张磊说,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在法律领域一定要做好准备,否则受制于人的可能性将非常大。“华为的法务模式是源自其自身特点的,我们也应该鼓励每家企业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