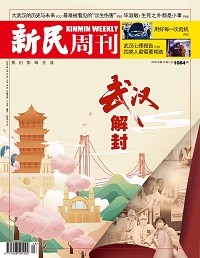助人者,也待人理解
建筑工人、社区工作者、警察、保安、志愿者……在武汉抗疫的一线,有无数人在为这场战斗艰辛付出。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平凡,但他们也渴望得到最简单的认可。这份认可,是对他们最大的心理支持,让他们有力量去继续帮助他人。

心理志愿者两次“心理崩溃”
“你想好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还可以回去,进去了你可能就出不来了。”
2020年2月1日,下定决心去武汉做心理疏导志愿者的毛平,从山东出发、辗转多途,即将在信阳跨过河南与湖北的省界,这时,当地警察给了他这样的提醒。“会出来的,只是会晚点。”他笑着回答警察。
那时,武汉“封城”刚刚一周多。“我决定要去,是觉得我能帮上忙。”
毛平的本职是知识产权领域律师,而他之前的经历很丰富:军人出身;转业后在北京蓝天救援队工作,有急救护理经验;长期学习心理学,是一名心理咨询师。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就到北川做过救灾志愿者。
为了不给当地添麻烦,出发时,他准备了“战斗物资”,带上三个行李箱、两个背包。
“有人跟我说,做心理咨询只要在外地接电话就行了,不用去前线。但我不这么认为。”毛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电话里的交流也许能对当地人做心理紧急干预,但却无法达到真正的心理疏导的效果,隔着电话,无法产生咨询师和被咨询者之间的共情。
在他看来,取得被咨询者的信任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和对方处于同一空间,共同去面对病毒的风险,这才是真正的“与你同在”。“我从风险相对低的地方来到了风险最高的地方,走到他们面前。我这样做了,他们会愿意信任我,向我敞开内心倾诉。”
毛平走进武汉的方舱医院,去安抚老伴因新冠去世的老年患者;他去公路道口,为顶着巨大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的交警排解郁结。做心理疏导的间隙,他还为社区采购运送物资,为街头流浪汉找安身之处。他做到了与武汉人同在。
而这种共情,也让他在情感上一度崩溃。
刚到武汉的前几天,毛平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内容是武汉的一个小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但当时医院无法收治,只能在家中的房间里一个人隔离。“我是一个8岁女孩的父亲,我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最怕的就是孤独、和父母分离,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视频里孩子的那种无助。”看着视频,毛平很难受,大哭起来。为了缓解情绪,他跑去洗了一个多小时的衣服,转移注意力。“哭过之后也就好了,情绪的释放让我更加坚决:一定要帮助像那个孩子一样的当地人。”
第二次“崩溃”是到武汉的第二十天,毛平正在电脑前写报告,这些报告将提交给相关的政府官员,记录他在志愿服务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提出对抗疫工作的建议。写着写着,他的内心突然被一股情绪击中,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他想到,尽管这些天他一直拼命帮助他人,但还是有人在背后说风凉话。
毛平说,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争名争利,但也希望得到认可。那一刻,许久以来因为被误解、被诋毁产生情绪集中爆发了,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做这些事的意义。“真的是很崩溃,我一个大男子汉,哭了很久。”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平复心情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放弃,为当地人做心理疏导的耐心细致,一点也没有减少。
“虽然我的内心承受力比较强大,但我也是个普通人,也‘崩溃’了两次。这么多天的心理疏导做下来,我的内心也积蓄了不少负面的东西。武汉解封之后,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女儿,去回到我自己的生活轨道、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他说。

社区工作者的委屈
情绪失控之前,王强(化名)已经连续加班了23天。今年32岁的王强是武汉某高校的保安,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他每天工作8小时。他是湖北人,但家不在武汉,今年的春节假期他没有提早回家,没想到后来的“封城”让他想回也回不去了。因为有些同事已经提早离开武汉,短期内无法回来,他被要求加班,执勤时间增加到了一天12个半小时,而且没有人能和他轮换,每天都要到岗。
“那23天每天工作时间长,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后门的岗亭里待着,四周没什么人,比较孤单。”王强说。后来,他被调到学校正门执勤,有可以换班的同事了,工作时间恢复到每天8小时左右。但他开始紧张,因为这个岗位要检查出入的车辆和人员,要与他人比较频繁地接触,而一开始他们的防护措施不完善,他特别担心自己会被感染。
这样的情绪萦绕在他心里。一天晚上,他失眠了,到了凌晨三点,他在员工宿舍里突然不由自主地大哭大喊起来。同事安抚他,他把同事都推开,自己倒在地上激烈宣泄。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疫情期间的孤单和紧张,把我之前在心里积累了好多年的不痛快引爆了。”那晚之后,王强在员工宿舍里休息了十几天。
王强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我到现在也不清楚那时为什么会情绪失控,我只记得,当时心里感觉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怀疑周围的人都想来害我”。
后来,王强得到了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家人也到身边给他支持,王强的负面情绪已经缓解,不过他还是迟迟没有走出宿舍回到岗位上。“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天应该是把好多人都吓到了,给他们添麻烦了。”他说,保安应该是为他人服务的,结果他现在没法坚守岗位,还要别人来照顾他,这真不好。
他计划在疫情结束之后,换一个工作,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我以前想自己做点生意,但家人一直觉得我不够成熟,不支持我。疫情之后,他们愿意听听我的想法,帮我去做尝试了。”他觉得,和家人关系的改善,也算是疫情的意外收获。
李芳(化名)比王强更年轻,还不到30岁。她在武汉某居委会上班,承担着社区防疫中最琐碎繁重的那部分工作。2月11日,武汉所有小区封闭以后,居民出入小区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相应的证明资料,她负责把守小区大门。
有一次,一名中年女性居民的证件不全,大声嚷嚷着一定要出去。李芳不放行,居民就对她骂骂咧咧,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李芳忍住了,但没想到第二天居委会领导告诉她,有小区居民打市长热线电话投诉他,理由是她“服务态度不好”。
“像这样的事儿我这些天来一直碰到。比如小区里有户居家隔离的人家,提出一定要我去给他们买鸭脖吃,买不到就冲我发脾气,我真是哭笑不得。我们居委做了那么多事,还被这样对待。委屈,真的是很委屈。”
跟心理志愿者谈到这些,李芳终于宣泄了自己的情绪。“那天我哭了很久,说了很多,谢谢志愿者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还给我很多好的建议。其实,我明白刁难我的人毕竟是少数,该做的工作我还是会好好去做。”
善待疫情中的“发光体”

李芳心里的苦楚,刘惠玲也非常理解。刘惠玲不是居委工作者,她是武汉普通居民,疫情暴发后,她第一个主动要求担任志愿者。
刘惠玲说,她所在的小区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公里,离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疫情之下,这里的居民本来就十分紧张,这时候如果有身边的人能站出来做些事情,可以给其他人鼓舞的力量。
一开始,她和其他志愿者在小区门口执勤,登记出入人员、查验体温。后来,小区封闭后,她又牵头成立“菜篮子志愿者团”,为小区里所有居民团购食物,并配送到他们手中。
刘惠玲在工作岗位上是管理者,还有十年的工会主席工作经验,她知道做一件事情肯定会遭遇很多不同的声音。做“菜篮子志愿者”以来,有居民对供应商的配菜种类不满意,有居民嫌价格高,有人抱怨送菜上门不够及时。“其实,我们这些志愿者,很多人自己家里也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有的是前一分钟还在小区门口站岗,下一分钟就跑来给居民送菜。给小区里所有人送好菜,自己吃中饭都要下午两点钟了。”
但她对这些毫不在意,还是每天乐呵呵地做着志愿服务。“都知道我们武汉人的耿直脾气,爱吃辣椒,爱吃热干面,待人真诚不带水分,遇事也少冷静。对上眼了,两肋插刀赴汤蹈火;遇上烦心事,也难藏着掖着,不迂回打马虎眼,面对面直接就给你干起来。”尽管有时多少会听到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但她相信身边人的善良本性,这种互相帮扶的精神,最终是可以潜移默化的。
谈到还要服务多久,她笑着说:武汉的春风渐暖,我这个团长“解甲归田”的日子也不远了。
要说苦中作乐的志愿者,就不能不提误入武汉的小伙子“大连”。2月12日,小伙子从上海登上高铁,本来是要去长沙谈项目。结果列车开到武汉站,他被列车员阴差阳错赶下火车。
小伙子下了车,却发现自己只能在武汉流浪了。他在网上搜索,发现当地有好几个医院在招志愿者,其中武汉市第一医院能派车来接他,他就去了那里。
小伙子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有个不用露宿街头、管饭的地方就行。他是大连人,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误入武汉,就告诉医院的人叫他“大连”。到了医院,他打扫卫生、清洁病房,一天工作12个小时,换三次防护服,成了医院里的开心果,因为他说话特别直爽喜感。
“大连”说,他在医院一个月把20多年的家务都做了。”医护人员问他进病房打扫怕不怕,他坦诚回答:“这层楼都是重病人,病人一说话,我紧张到死;咳嗽一声,我心都能跳出来。我收他们吃完饭的盒饭,进病房收,我都想要个竹竿挑出来。”
谈到在医院做服务一天有几百元报酬,他说:“我宁愿不赚钱,给我个酒店,管我吃就行了,我没那么伟大,我也惜命。”就是这样的真诚心态,让他成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出名的“九楼女神守护者”。他没有想多做什么,但已经做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