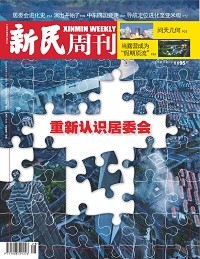重新认识居委会
2022年的春天,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的。奥密克戎来势汹汹,上海史无前例地按下暂停键。
封控在家数月,让许多人与周遭的社区工作人员有了更多交集。原本默默无闻的居委会一下子被推到台前。有人甚至说,那段时间的上海形成了一个怪圈,好像“样样事体找居委”,他们因此成了被骂得最“凶”的一群人。
但这并不代表每个人就此真的了解了自家的居委会,毕竟防疫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其中一项而已。
他们平时到底在忙些什么?是时候,重新认识居委会了。唯有此,才能更好地认识,上海社区治理的难点与痛点。
双重属性
7月18日下午,记者在虹口区香港丽园再次见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苗。他刚刚骑着助动车从街道回到办公室。还没等他坐下,同事就递过来一份名单。当天是虹口区那一周核酸“三天两筛”的第一筛,各个点位的安排和人员的调配等相关事宜都等着刘苗拍板。在另一间房间内,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晚上要用到的核酸采样管,一包包黄色袋子被整齐摆放在工作桌上。
疫情期间,刘苗曾因一段与医护人员的录音火遍全网,被大家称作“哭了的书记”。
“现在每天居委干部都不怎么看到我,因为我基本不在办公室。”刘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自从6月1日回归常态化防疫后,一方面核酸筛查等防疫工作仍不能松懈,另一方面居委会的其他工作也要照常开展,“我一般早晚都会在小区里巡查,中间会穿插一些电话上和做台账的工作。但凡有空我就会去社区里转一转或进行走访”。
通过走访,刘苗说,不仅可以及时掌握居民们的心理动态和现实需求,还能在交流中随机宣传居委会正在开展的一些工作。至于巡查小区,刘苗解释道:“比方说,我早上看到小区花坛边扔了一包垃圾,我不会马上批评保洁,可能当天第一次打扫还没有完成。给他们一点时间,当我再去看的时候,如果垃圾还在,那我就要找他们谈话了。”
就在这天上午,刘苗还跟着保洁员一起去打扫了小区的车库。“如果认为搞卫生就是保洁的活儿,那久而久之,他们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没有荣誉感和归属感。但我书记或者其他居委干部跟着一起,看到他们的辛苦,该表扬表扬,他们做事也会更有动力。小区变整洁了,居民自然会更满意。”刘苗说,“社区治理功夫在诗外,所谓绝招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除了言传,还要有身教。”
如此看来,即便没有疫情,居委会的工作也并非普通人想象的那么轻松。

上图:蔡琪参加了物业调解协调会。
郑家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蔡琪对此感触颇深。“居委会是自治组织,是党建引领下的自治。除了策划一些群众性的活动,发动居民参与进来外,调解民间纠纷或许就是最突出的工作,顾名思义一旦邻里发生矛盾,或是自己家里发生家庭纠纷,都会来找我们居委会帮他们调解。”蔡琪告诉《新民周刊》,还会碰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动迁、旧改等集体性的矛盾,“我虽然是学社工专业出身,但真正来到社区,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完全用上,大多都是突发性的情况”。
除了自治方面的工作,蔡琪介绍,居委会还要对接街道所有条线的下沉工作,包括困难群体救助、民政老龄工作、综治和治安管理、防火安全、安全生产管理、精神文明教育、计生等等。
“还有一些12345热线市容市政方面的回复,每年汛期防台防汛的工作等。我们居委会一共有7个人,一个人至少负责两个条线。”蔡琪表示,“除了条线,我们还分块。每个人大概要管理一两百户居民。块长就要底册清,自己负责的块里,哪家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困难,都要清楚。加上现在人口流动也很快,我们还要及时更新实有人口信息。”
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区工作清单》显示,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多达119项。其中,协助政府56项,包括社区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群众权益保障等;协助党委3项;协助人民(社会)群体5项;协助法院8项;印章使用23项;自治事务24项,包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管。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晓春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坦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城市居委会一直面临着“行政化”和“自治性”双重属性的困扰。
究其原因,无论是1954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还是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明确提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本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位制逐步消解。这就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很多‘最后一公里’的管理任务由谁传达?第二,很多重要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最终谁来投递?”黄晓春表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工作最终都经层层部署落到居委会身上。
1996年,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城区工作会议,会上正式提出了上海城市管理的基本架构,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当时,‘两级政府’指的是市区两级,街道为‘三级管理’,后来又增加了居委会‘四级网络’。”黄晓春表示,可见最终城市管理的末梢还是居委会,“这就客观上导致了居委会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法律属性是自治的,但实际上更像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助手,或者说政府的重要抓手,被行政化”。
尤其是国家负责社区居委会的正常运行及其成员的工资待遇、福利津贴,并保证服务场所和基本设施等资源。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责、人事考核等都由街道负责。“因此,居委会行政化有一定的内在诱因。一部分居委会可能更关心的就会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如何自上而下实现各种目标。”黄晓春直言不讳道,“加上居委干部所负责的各类条线任务包括制作台账等任务也不轻松,这就导致一些居委会把工作重心全放在了‘对上’上,反而对居民到底有怎样的需求和实际困难不是特别清楚。长此以往的结果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不知道居委会在干什么,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成了中国居委会的形象比喻。
当行政化给社区带来的负担过重的问题凸显之后,政府便开始有意识地为社区减负。2015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精简社区会议和台账、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整合社区信息网络、增强社区服务能力等七个方面,对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上图:北京东路的贵州小区弄堂里,石库门外墙上挂着一盆盆的鲜花,把家园建设得更美丽了。摄影/周馨
“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始终高度重视,多次强调建立各级政府给居委会布置工作的审核与准入制度,减少居委会承担的不必要负担。此外,近年来诸如‘一网通办’等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也客观上为居委会减了不少负担,因为通过这些信息化机制,以前不少需要找居委会办理的环节就被跳过了。但尽管如此,居委会减负工作仍然任重道远。”黄晓春分析道,因为整个行政体系跟基层打交道通道太单一,“这个现状不改变,最后总会绕回居委会。因此这些年我们也在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再造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从而降低各级部门对居委会的依赖,替居委会分担一部分压力”。
事在人为
在这次疫情中,人们看到有些居委会几乎无所作为,但有些居委会确实干得非常棒,甚至做了很多超出想象的事情。在黄晓春看来,这就跟居委会的队伍有关,“就要讲到人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上海旧区改造和产业升级轰轰烈烈地进行,100多万的下岗工人要转业,100多万动迁居民要安置,社区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于是,一批原来在企业中从事党群工作、年龄在40岁上下、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中层干部被充实到了社区。
“这些干部的到来,一下子把上海城市基层体系的基石给夯实了,当年解决了大量的群众困难,协助了很多公共事务,比如城市动迁等。”黄晓春表示。
后来,到了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结出果实,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文件。这些文件中就包括了《上海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之所以出台这个文件就是考虑到社区治理关键在人,而之前的那批干部大多都已到龄退出了社区工作舞台,必须常态化补充职业化工作队伍来加强基层工作。
为此,上海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标准,合理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涌现出了一些不错的居委会干部能以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和为民服务的精神兼顾好上级的要求和居民的诉求,既把上级给的任务完成了,同时也比较注重发动居民,强调自治。”黄晓春告诉记者,也正是由于这些居委干部一直有群众意识,在平日里就和大多居民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些居委会才可以在这次疫情中迅速动员群众,主动作为”。
而刘苗和蔡琪所在的居委会都可以算入其中。

上图:抱着材料的刘苗参加社区防疫工作。摄影/杨帆
“任务重、工作多,只是一个正确的借口而已。”在刘苗看来,要做好社区工作,必须要有朴实的为民服务情怀,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真心实意把社区服务化作工作信条,这叫热爱,“这样你自然而然就会挤出时间把事情都做好”。他经常提醒居委干部及社区党员骨干“不要把桌子上的灰擦到地上”,“我们经常埋怨很忙、很累,结果这一地灰都是我们自己因为偷了某种懒而搞出来的;社区干部骨干,不能眼看群众已经上岸了,自己反而还在河里忙着摸石头”。
同时,刘苗表示,走进楼组、贴近群众是社区工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谁要是说呆在办公室就可以做好社区,一定是不接地气的。无数事实证明,走入不了居民家的人在社区迟早会不合格”。
事实上,去年8月,刘苗才来到香港丽园,但仅用了不到4个月,他就组建起了一支近180人的志愿者队伍。“其实就是三句话:了解家底、做好家事、凝聚家和。”部队出身的刘苗向记者透露了他开展社区工作的诀窍。
原来去年8月2日,刘苗刚到社区报到的第一天就特意用半天时间把小区里破损的地面瓷砖数了一遍,一共534块。接下来的一周,他又不停地在小区里转,哪幢楼的哪几层有楼道堆物,哪家的水表箱门是坏的……他都排摸了一遍。
在一周后第一次小区民主协商会上,刘苗先介绍了自己,再把上述情况讲了一遍,最后表示大家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原本打算给新书记来个“下马威”的楼组长和小区骨干立即傻了眼。第二天,刘苗的行事作风就在小区里传了个遍。他甚至发起了一项挑战:居民在小区内任何位置拍的照片都可以发给他,看看他能否精确指出是在哪里拍的。
“这时候就要趁热打铁。居民对你有了初步的印象后,你就要在日常工作中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将居民变为熟人。”当居民喊他“父母官”“小巷总理”时,刘苗指出,不能真把自己当“官”嘚瑟,“要告诉他们,你就是个服务员,是来为他们服务的”。
接下去的日子,刘苗不断召开各种会议,除了全面了解居民需求,还拉上物业一起看看如何改进工作。此外,他还带领居委干部骨干在社区定期开展了一系列为民服务,如他上任的第二个周四就恢复了每周的爱国卫生服务活动,第二个月就把小区中央平台因锈蚀破损困扰居民20年的长椅更换一新。由此,刘苗逐渐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
记者注意到,在刘苗助动车的箱子里放着一些简易的维修工具,还有一些旧布。刘苗解释道,这叫“有备无患”,当居民需要报修时,不能只是简单地让他们找物业。“如果只是螺丝松了,你是不是可以帮着拧紧;如果是小漏水,是不是可以用布先帮着堵上……”刘苗说,“居委干部完成本职只叫称职,本职完成还能做好其他有利于居民和社区的,可以谈优秀。”
“用兵之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社区工作,同样如此。”刘苗开玩笑道,听上去有点像精致的利己主义,但却是最实在、有效的办法。
刘苗自认为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书记,他深知人都有惰性,他常说社区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把为群众服务的目标定得高之又高,最后实现的才有可能是刚刚及格。
已经当了10年书记的蔡琪更是深知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辖区内某幢大楼的楼道内垃圾通道改造,“因为容易滋生细菌,不符合卫生标准了”。但居民不乐意了,尤其是年纪大的,原本出家门就能倒的垃圾,现在要拿到楼下。另外,新的垃圾房造在哪里,谁也不愿意放在自己楼门口。蔡琪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和物业一起给居民做解释工作,很多人不听就围着你吵架,有居民情绪也比较激动,“有人拿着那种医保卡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病,你不要刺激我,要不然我就要昏过去的”。
但作为书记自己不能慌,也不能跟居民吵架。蔡琪的做法是,先要安抚情绪,然后再耐心地讲解政策原因;等所有人都可以心平气和的时候,再召开协调大会。
“有些居民白天要上班,或者有些年轻人觉得父母做不了主要自己参与的,那我们就把协调会放在晚上。大家把顾虑讲出来,把想法和建议提出来。”蔡琪说,垃圾箱房改造是大势所趋,但在过程中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尤其是让老年人方便。就这样通过一个个方案、一次次会议,原本激烈的矛盾被解决了。
“我和大多数居民关系都是很好的,但遇到问题,他们也会急的。居民不是针对你,而是因为只能找到你居委会。”蔡琪感触颇深,很多时候是居民的一种情绪宣泄。
当然,居委会处理的过程也很重要,毕竟有些事情不是一两次就能解决的,要通过多次的磨合。即便是这样,也极有可能达不到居民想要的程度。
“但你为他们做了很多努力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做不成就一口拒绝,和你通过努力达不到,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居民也会认可你。”蔡琪说,将心比心很重要,作为居委会干部要学会换位思考。在疫情期间,蔡琪在和居民说明情况前都会加上一句“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再用最朴素的大白话去和居民说,效果往往也是极好的。
此次上海疫情中,郑家巷居民区所在的石门二路街道在静安区率先实现了社会面清零目标,率先实现全域防范区,率先达成全域“无疫小区”目标……
在实践中探索与成长
令人欣喜的是,通过这次疫情,很多居委会获得了成长,团结了志愿者队伍。因为这样一场涉及公共卫生和每个人健康的事件的发生,让居民自治的参与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疫情以来,刘苗所在的香港丽园从最初只有7个居委干部,发展到10多个楼组长,再变成目前5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居民自治力量不断壮大。
值得深入思考的一点是,疫情过后,未来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何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万胜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从他所在的小区来看,疫情虽然让人们暂时地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却收获了一整个的社区。
熊万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小区内部的整合很难,年轻人忙着上班,很少参与小区内的事情,小区的事务主要是退休老人当家。他将这种现象形容为“社区折叠”。

上图: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申城的社区工作者坚守在各个岗位上。近日,宜川路街道工作人员对垃圾厢房进行消毒处理。 本报记者 孙中钦
“但这次疫情期间,年轻人对于小区事务的参与大大增加,甚至唱了主角,似乎将这种折叠部分地打开来了。”熊万胜坦言,随着大家的生活回归常态,如何保留这股年轻的力量其实并不容易,“这个事情不能勉强,但居委会要做的是继续联系好这些人,时不时邀请他们参与一些活动”。
更重要的是,居委会能不能从中帮助发掘一些骨干和达人,将他们充实到业委会的队伍中,把他培养成业委会的骨干,并建立一套符合上海城市特点的业委会委员骨干的选拔培养机制,打造老中青互补的良性梯队。在熊万胜看来,这或许是疫情给人们带来的重要启发或契机,“毕竟小区的各种差异性本来也离不开应由业委会来面对,若能更进一步与居委会形成紧密协作,小区治理中的很多现实问题就一定能更好地迎刃而解”。
眼下正值香港丽园社区新一届业委会换届选举的阶段。采访中,也有社区骨干给刘苗打来电话,希望他推荐一些有能力的人才,但刘苗当即回复,希望人人都有机会参与社区建设、支持公推海选。
“志愿者和未来业委会委员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志愿者自身忙的时候可以不参加小区活动,但业委会委员作为小区全体业主在物业服务领域内全部利益的代表,是要与物业企业签订很多服务规定和标准的,所以挑选业委会委员必须慎重。”刘苗表示,作为居委会来说,在物业管理领域,业主才是第一主体人,“所以我们不会帮小区敲定人选,我们更多的是帮他们搭台子,通过问需问计,用心用情于民的群众路线来推选一些确实能够公平公正有操守,真正乐于为社区扛起大旗和护航的人,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新型社区治理服务”。
刘苗的理想规划里,未来社区治理的主力是“老和中”,“青”则是后备力量,可以通过搭建社区共治平台及时将他们纳入并重点进行储备培养;现实中,社区所有骨干,不仅要做救灾粮,更应能当种子用。
当然,作为党和政府派驻到社区“最后一公里”的代表,居委会也有义务指导社区各方进行党建引领下的一些工作方向的制定,包括协助业委会制定小区“三项议事规则”等。刘苗说,作为社区书记或居委干部一定要主动靠向群众,唯有这样,方能从最初的跟跑,到熟悉后的并跑,再到完成居民所有期待后的领跑。

上图:封控过后,为了留住疫情中涌现出的社区治理能人、达人继续为社区治理赋能,浦东隧成小区注重“以情留人”,设计了一款定制T恤。
在这个过程中,蔡琪认为,居委会自身的班底也很重要。令她颇为头疼的是,每次居委会换届选举,都找不到最合适的人选。
上海居(村)委会历年换届公开报告显示,目前基层治理队伍人员构成整体上在优化,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从2012年的50.7岁降为2018年的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也增加到69.16%。
“因为居委干部有属地化的要求,每年选举又要求‘年龄降一降,学历提一提’,但我们的薪资待遇在年轻人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蔡琪坦言,职业发展前景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无论如何,上海居委会如果能通过此次疫情的洗礼来一次本质的提升,重塑威望,今后便能在关键时刻,充当好居民协调的组织者、居民利益的保障者、政民之间的沟通者。(记者 应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