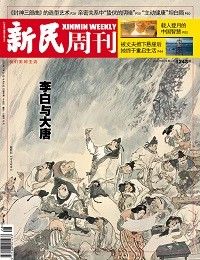从人祭到封神
人牲被献祭,有了《封神榜》
读《封神演义》的明朝原本,你会发现,上了封神榜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代表了一种永生的承诺,是在另一个空间中继续此世的生活,而是对此世生活的中断;而且是强行的事故性的中断,不是寿终正寝那样的自然中断。直白地说,上了封神榜就意味着退出或即将退出人世,也就是“死”了,它的历史原型是李硕在《翦商》一书中着力考证的人祭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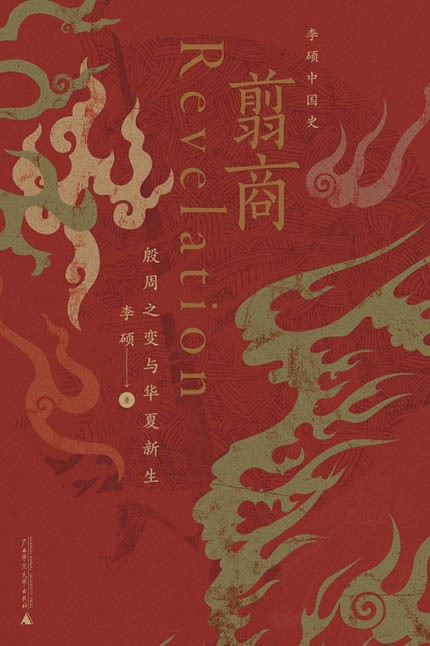
李硕像一个细节强迫症患者——我其实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种病症,如果有的话,此处的李硕就是——一样地描写安阳后冈祭祀圆坑中的人类骨殖状态:数量、性别、年龄、姿势,肢体是否残缺,以及如果残缺的话,缺的又是哪一块或哪几块?……人祭是商朝的“真相时刻”(hour of truth),它揭示了这个社会的观念基础,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主客体关系颠倒的神话(宗教)世界,人祭则是神话以颠倒的方式想象世界的制度后果。按照现代神话学的理解,神话就是把人性写入神性的内部构造,把人的心灵秩序向外部秩序投射,按照自己的内在本质创造了诸神的世界,转而又把诸神的世界看成了独立的存在。也就是说,尽管神话的本质是把人类自身的道德剧目读入了世界,从而大胆地设想整个宇宙都渗透着人道,但神话的信仰者却是从世界中读出了人类的道德剧目。人与世界关系的异化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神祇们由本来的宾语变成了人类心中的主语和暴君,这样的神祇必然反过来要求来自人类信仰者的祭献,这是神话时代最可怖的地方。这里的“神话时代”指的是,神话在其中作为一种真实的主宰性和弥漫性的力量存在着。这种真实当然不是指神话内容在视觉或光学意义上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指人们“相信”有关神的叙事是真的,并且他们的生活会因这种“相信”而发生改变。使人祭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的观念背景中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指出这一点在道德上是令人难堪的——那就是,即便人牲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自己在人祭仪式中确实“升天”了。尽管这仍是一杯令人恐惧的难以下咽的“苦酒”,就像对于临刑前的耶稣一样。而且,也如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后有了《新约圣经》,人牲被推下献祭坑之后才有了《封神榜》。人牲这些为神话时代所纳的税,经此艺术变形却转化为一段美丽的文化乡愁。
对于商朝人而言,这种作为存在中心和核心语境的神话,就是作为本体论的神话,它可以被感知,却无法被思考,更不必说反思,对它的祛魅只能借助外来的力量。

上图: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
周代商,文明形态的嬗变
众所周知,是地处僻远的周族把商朝推进了太平间。李硕进一步告诉我们,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朝的人祭制度,并清除了有关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从而也清洗了周朝屈辱的前史。据李硕的考证,周族自己没有文字——垄断造字和命名的权力当时是商朝霸权的一部分。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系“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而“用”字专指献祭之“用”,这表明,“周”族就是专供商人献祭“用”的人口,他们是人祭制度最主要的受害者。周昌就是在长子伯邑考被“用”之后,才毅然举起了翦商的大旗。甚至——当然还是据李硕的考证——姜子牙的历史原型也是来自羌人部族的首领之子,被周人俘获后作为人牲送到了商都朝歌待祭,只是后来侥幸逃脱了。姜子牙在《封神》中孑然一身辅佐周昌的形象背后,却是周族与羌人联合倒商的宏阔史诗。从这个意义上,商朝其实是被一个被迫上了封神榜的群体及其部族翦灭的。
周族成为翦商事业的起点和中心,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观念事实:他们作为一个部族很难从根本上认同那种把他们的父母或子女推入祭祀坑的神话叙事。由于这种神话是商朝的意识形态,是它用来组织政治社会生活的中介和中保,因此与意识形态的疏离很容易发展成政治上的疏离乃至反叛。
当然,如果把周朝对相关历史档案的销毁看成类似一个对容貌不自信的女孩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窘境的行为,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象征意义。人祭的历史性退场,根本原因在于,周代商,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王朝更替,更是文明形态的嬗变,即商业——神话时代的结束,以及农业——理性时代的来临。商朝的历史性存在曾经为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作证——汉语中的“商业”“商人”都是基于这个事实而产生的概念。而上古的商业时代一定是神话的时代,古希腊神话只是另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案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神话无非是前概念(以形象代替概念)、前逻辑(超自然的因果联系)的构想世界的方式。在地道的农业社会,生活给予人类的自然启示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果关系高度确定,且能为人类充分地把握和利用,几乎不必诉诸超自然的解释。商业社会则相反,投入与产出并非正相关,其间牵涉太多的变量,太多的非人力可控的因素,以致最终结果完全不可把握。命运、神话作为终极性的力量就是用来填补这种不确定性的空间的。只有置放在这个文明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废除人祭只是周朝重构中华文明源头叙事的浩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个文化工程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砍掉商朝礼制中作为前言的神话叙事,直接从作为正文的“礼法”开始加固和完善,敬鬼神而远之,从而造就了一个早熟的现代社会。根据雷海宗先生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解读,西方的当下在历史阶段上才相当于周朝后期,即秦朝统一前的战国时代(雷先生的“战国策派”由此而来)。在文化形态上,周朝诸子用概念和逻辑替代和囚禁神话形象和神话思维的方式,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现代社会才发生的事情。

上图:《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
被打造成白日梦的神话
悖论的是,神话只有在被解除了其作为本体论或存在论的重负之后,或者说,只有在遗忘了产生它的时代,告别了它的源头叙事之后,才成为真正的神话,与信仰或意识形态脱钩了的神话本身。在此,我用“神话本身”这个概念来指涉不再具有解释和改造世界功能的纯粹作为白日梦的神话。对于这种神话,人们不是在这里安身立命,而是到这里来逃避生活;换言之,人们不是到这里求索生命的意义,而是在这里清空人生的意义。这样的神话在现代的功能等价物就是电影院,这决定了神话与现代电影的联姻,尤其是在电影发展出了足以表现神话奇幻体验的特效技术之后。当下的电影市场垂青神话题材,这是《阿凡达》、《指环王》之后日益凸显的现象,《封神》和“新封神榜”系列只是来自华语片的最切近的证据。
电影院是现代人的白日梦,兜售神话的电影院是白日梦的二次方。封神序列要被打造成这样的白日梦,它就必须切断与历史原型的联系,像在彩条屋和追光动画所构建的封神宇宙那样,完成由逃避封神到主动追求封神的嬗变。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或即将奔赴这场封神狂欢时,另一些人却在李硕的文字中受难。“然后开始杀人”,李硕在《翦商》中写道,“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颗骨一块、右腿一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李硕相当粗暴地把作为人类一部分的我们带到人类的另一部分人的面前,越过时空的离间和人为的抹杀,迫使我们目睹、倾听、见证人牲在现场的哭喊声,并且提醒我们别忘了现场之外他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深渊般的痛苦。对于这样的历史,任何的概括或抽象都是不合适的,都表明了它们作为钝化或瘫痪历史感的手段的性质。人类历史的进步主要地并非体现在杀戮和暴力的减少上,而是体现在对隐匿或掩饰它们的方法的创新上。李硕通过这种寓言式的血腥场景及其对人的主体性的戕害,意在促使我们回望从中一路走过来的过去,并据此向现实和未来发问。

上图: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
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
当然,李硕的这种书写置于当下注意力经济的背景下,很容易被看成是以消费苦难的方式哗众取宠。——否则,这种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场景,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历史已经过去了,尸骨已经掩埋了,重提这一段历史,除了有煞风景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且,除了被杀时的叫喊,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历史的客体姓甚名谁——他们进入历史的理由只是他们被杀死了——这种匿名(者)的痛苦即便进入了历史的书页,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李硕相信感性的力量,相信痛苦是可以负载足够深刻复杂的认知内涵的。在人祭制度中,得到与损失分属于两个对立的群体,献祭者迫使人牲成为纯粹的代价,而自己收获了以此为代价带来的全部好处,哪怕这种好处只是想象中的宗教利益。——宗教利益并不意味着把幻象当作现实,而是他们对现实有着跟今天的我们不一样的理解。——在这个制度语境中,人牲的哭喊,连同他们身后留下的残骸遗骨,正可以视为对这种一部分人得到全部,另一部分人失去全部的权利分配格局提出的强有力的质疑,而这种质疑难道不应该转化为我们的质疑?难道人祭的历史仅仅与这些特定的人牲有关?难道历史的苦痛注定只能由他们承担?难道三千多年前的人牲的命运不会以某种隐秘的方式支配着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不能作为人类共同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无限延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去感受这种痛苦,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在我们这里就仍旧没有被清算,从而这种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性就并没有被清除,尽管造成痛苦的方式可能不再是人祭了。
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事,好像只是我们向他们投去一抹同情的目光。因为只有他们被置放在人类的位置上时,他们作为“人”的痛感体验才能被指认和认同。这个意义上的痛苦体验可以进一步用来改变知识的结构关系乃至人类的命运:从终极意义上,如果这些人牲被想象成被剥光了衣服也会感到羞辱,被刀子切割时也会感觉剧痛,离开世界时也会把整个世界带走的跟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姊妹一样的人,对他们的杀戮就是不可能的。
“然后开始杀人”——坐在《封神》的巨大银幕前,李硕的声音突然响起来了——声音有些喑哑,但我相信那就是李硕的声音。撰稿|毕会成(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