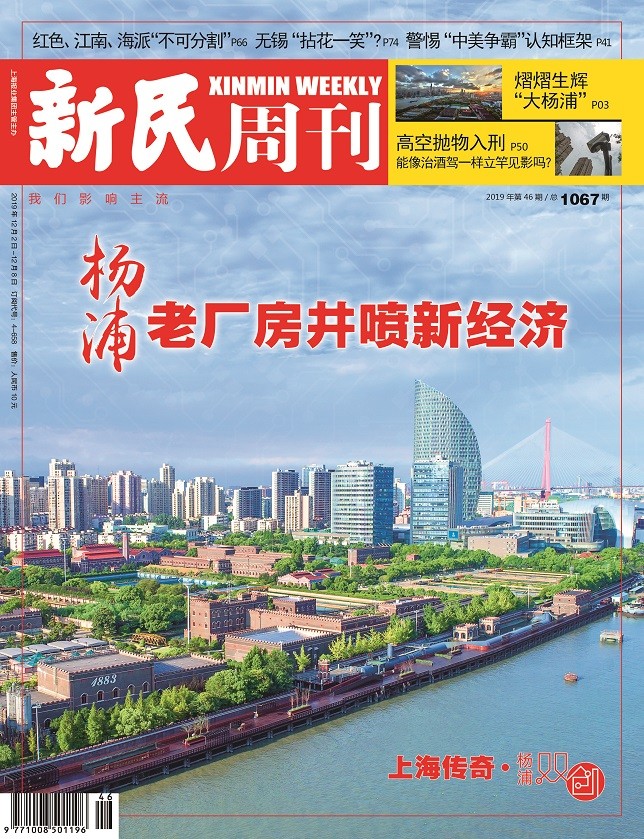“记”者鲁杰
和鲁杰认识20多年,前些天加他微信,发现他的昵称是“山东好汉”。明明江苏人,怎么自称山东汉?后来问鲁杰本尊,他哈哈一笑,“鲁”,山东简称,“杰”,好汉。老实本分的鲁杰玩起文字来,也有一套。
鲁杰的父亲,当年是县饮服公司人秘股股长,母亲一直在农村务农。鲁家四个子女,他是老小。父亲退休时,按照政策,可以有一个未婚子女顶替,哥哥姐姐都已成家,高考两次名落孙山的鲁杰,顺理成章地顶替父亲到县城上班。
鲁杰并不安分,业余时间比上班都忙,到处跑,到处看,到处问,而后关起门来写稿,投稿。高考落榜那年,在村里听到一些奇事趣事,他便开始有记下来的冲动,而后寄给县广播站。等到村头喇叭里播出他的名字,一般都在一周或几周之后。哪怕是两三句话,他也很兴奋,甚至有成就感,好像全县老百姓都知道许河乡有个“鲁杰”。
“文学青年”的标签诱惑着鲁杰。那时候他经常跑报社、电台送稿,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结识。有一次,他发现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台历,上面标注的24节气时间居然不同,有的相差30多分钟,有的相差一个小时。鲁杰特意来请教时任小报记者的我,写了初稿,要我帮他改改。后来,他的《搞不懂的“时差”》发表在1994年5月的《中国青年报》上。他说,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作品。
鲁杰今年正式退休,他给自己做了一次盘点:30多年发表各类作品数百篇,短的简讯百把字,长的通讯1000多字。他觉得自己跟专业写手比,差距不小。不过,鲁杰用近四十年的坚持,从“记事哥”到“记事爷”,写出了“大部头”:随杂簿。
“随杂簿”是个系列,一年一本,一本40多页,每本大致内容分为:看电影看戏记录,借阅、购买书刊记录,信件往来记录,存款缴费记录,借款借物记录,亲友互请记录,请人代办事记录,回家记录,回家带东西记录,理发、洗澡及其他记录。家乡的媒体记者最近采访发现,小到一只烧饼,大到烟酒,他都事无巨细记录下来。1982年,他刚刚参加工作不久,“随杂簿”上记道:4只烧饼0.20元、购计划大米10斤1.26元、电影票0.20元、《电影评价》第12期0.30元、双沟大曲1瓶2.22元、香烟两条8.80元、购计划粉丝0.3斤0.17元、购云片糕10条3.30元、付唱道情者0.10元、给父亲红包2元……对比30多年后的“随杂簿”,不仅可以发现物价的变化,更能感受百姓日常用品的丰富,生活水平的改善,消费层次的提升。
估计鲁杰的初衷也就是随便记记杂事而已,而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人,认认真真记了37年,名符其实的“记”者了。
有趣的是,“随杂簿”里翻出两段与我相关的记录。“1993年3月20日:今晚7时,为周云龙友调至《盐城晚报》工作饯行。参加的朋友有:周云龙女朋友小万,周、施、杨、邹、胡等共8人。在我店水晶厅。散席后,周为各位合影留念”;3月24日:“今晚9点钟,周云龙友在电视台点歌台为我点播一首歌《我想有个家》,原唱潘美辰,同时在报社为我刊登征婚启事……”感谢他给我做了一个记忆的备份。
前几年,鲁杰呆过的酒家被私人承包经营,他从此下岗失业。洗过碗,摆过摊。鲁杰个头不大,却打不倒,始终有一副招牌式笑容,是个内心强大的“硬汉”。
做了二三十年会计,鲁杰学会了打“倒算盘”:要不是顶替,家里本来会让他到小街上修钟表的。而现在,摄影和文字的爱好,让他一直奔波在路上,让他一路上遇见很多人,每一位都出现在他的“随杂簿”里,他们的故事每每带给他慰藉、感动,还有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