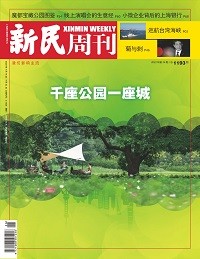西方的治理为何失效了?
西方的“美丽风景线”,今年格外“耀眼”。仅仅在过去的11月,就从美国、英国、法国一路轮番上演,竟然让不止一次地声称香港示威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无言以对。
11月1日夜间,因为对警察在地铁站内的暴力执法不满,美国示威者走上纽约布鲁克林街头抗议。抗议者直接翻越闸机,逃票进入站内,高举“别让这些猪碰我们”“别碰黑人孩子”“揍那个警察”等标语。纽约积怨已久的种族矛盾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在此次集会中爆发。
美国的好盟友英国此时也正处在焦头烂额的危机关头。在英国苏格兰地区,上千人在当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举行游行集会,继续奋力要求脱离英国独立,与之相伴的还有间歇性大闹独立的北爱尔兰,“日不落帝国”在“三分天下”的焦灼中形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11月8日,法国里昂一名22岁的学生Anas·K在里昂第二大学的学生援助中心大楼外自焚,来抗议自己困难的经济状况。此举导致他全身90%被烧伤,目前情况危急。
11月12日,法国里昂、巴黎和里尔等地的大学生爆发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以回应自焚者的“绝望姿态”。在里昂,数百人聚集在学生援助中心外抗议示威。里昂第二大学学生会不得不在学校入口处放置垃圾桶等障碍物,以阻止抗议者进入。学校第二天的课程被迫取消。在巴黎,抗议者们强行打开了法国高等教育部的大门,要求部长维达尔下台,并在墙上写上“生活不稳定会杀死学生”的涂鸦。在里尔,抗议者们高喊着“奥朗德是刽子手”闯进里尔大学法学院,迫使前总统奥朗德取消题为“应对民主危机”的演讲,并撕毁了同名书籍……
“选择性失明”“选择性失语”,让西方部分政客的双标又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在世界面前。正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所言,从美国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愤怒的民众从祸乱香港的暴徒身上汲取所谓“灵感”。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是现实给予被傲慢与偏见支配的一些国家最响亮的耳光。
西方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发现要从坑里爬出来并不容易。当然,他们可以继续扯开大嗓门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无法蒙上全世界的眼睛。
曾经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在他的早期成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过一个“政治衰朽”的概念。后来以“历史终结论”出名的福山,也发文讨论过“美国政治的衰朽还是涅槃”的问题。亨廷顿及福山等反复提及的“政治衰朽”,指的是失去自我迭代更新的能力,不愿意再通过反思政策和执政能力积极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反而沉浸在所谓“回音壁”或是“信息茧房”之中。
眼下,以美国政客的陈旧心态为典型代表的霸权衰朽,表现为一度引以为豪的美国创新精神的失落,面对新来的竞争者和挑战者,美国精英优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良性竞争,不是如何用外部刺激实现有效的自我创新与变革,而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把外部挑战和威胁消除掉。这一点,从怼天怼地的特朗普及其智囊的身上已经显露无遗。
凭臆想捏造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极其恶毒地攻击抹黑中国,还著书立说四处兜售,作为“对华鹰派”的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这名以专家学者自诩的美国总统首席中国政策顾问,在造假事件暴露后,竟然对自己一手炮制的这一超级闹剧毫无羞愧之意,仅以“这只是一个隐藏多年的笑话”自我圆场,敷衍了事。而白宫更是对此装聋作哑,闭口不提。纳瓦罗们的伎俩也再次刷新了人们对美国“鹰派”人物“黑中国”无底线的认知。在他们看来,不遏制中国是不行的,北京不愿成为“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秩序中……西方化和负责任的参与者”。
旅法20年的著名时评专家郑若麟多次撰文指出,当今世界正分化成为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阵营,所以中下层的极左翼和极右翼民众都在“反对全球化”的旗号下联手站在了一起,而他们的背后还有一部分传统高层右翼的产业资本力量。而中间派和传统左、右翼的大部分,因为支持全球化,也站到了一起……西方政治阵营正在发生大分裂、大分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日益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分歧,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在英国,全球精英阶层作为科技革命及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坚定地反对脱欧,但在大城市边缘、主流媒体之外,被发展所遗忘的草根百姓却通过脱欧公投发出了被埋没的声音。
而在美国,主张顺应全球化、赞同文化多元主义的阶级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失去了最高权力,以媒体为渠道激烈地宣泄着不满,特朗普被主流媒体“标志化”“妖魔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也在一定意义上暴露、加剧着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眼下,英美遵守的共同价值——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及其所导致的世界精英与社会分裂正在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性、结构性的矛盾而走向政治衰朽。
沈逸尖锐地指出,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无法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继续实施有效的治理。这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衰朽,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矫正,则整个世界将加速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种矛盾的根源,深埋在更加深刻的经济基础之中。2016年,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的首席操盘手斯蒂夫·班农曾经有过一个经典描述:中国出口过剩,导致英国和美国的产业工人被掏空。班农说对了部分的事实,这一轮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及暴力运动的兴起,关键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由产业工人构成的阶层塌陷了。但是,班农也应该非常清楚,真正需要为此负责的,不是中国,而是华尔街的金融肥猫们,他们对利润的贪婪,超过了对上帝的敬畏,更不要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热爱。
郑若麟更是以自身的经历见证了这种塌陷。郑若麟告诉《新民周刊》,目前,法国人的失业率已经高达8%—9%,一半以上的人拿的都是最低工资,大约1600多欧元,扣完税以后拿到手也就是1100多欧元,相当于人民币大概8000到9000元人民币,问题是法国的物价比中国国内贵得多得多,房价在巴黎也高得惊人。租一个20平方米的小房间,房租可能就要七八百,甚至于近千欧元。“今天50%拿着最低工资的法国人,跟中国北上广深等一些大城市的居民相比,他们的收入从绝对数到相对购买力,都已经落后于中国”。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民主体制下的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福利政策的时候,贫富差距一度有所缩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10%收入最高的人群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到了2000年,在西欧和美国这一占据总财富的比例已经达到60%;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10%的高收入人群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
现在法国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急剧萎缩,大多数都掉进了穷人的阶层,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上升到富裕阶层,而且富裕阶层的财富还越来越集中。这一惊人的现象证明世界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其实质就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全面胜利。
郑若麟指出,因为中国向中高端生产链的进发,损害了西方产业资本的利益,尤其是损害了西方产业资本所雇佣的中下层劳动力的利益。所以当产业资本开始以极右翼的政治色彩,开始反移民,反对企业外移,反对金融资本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中下层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左翼民众的强烈支持,这个时候百年未遇的一个新现象出现——那就是西方的统治阶级,西方的财团出现分裂,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益分道扬镳的现象。而这两大利益之间的冲突,可能正在成为今后影响整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冲突。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支持全球化的欧洲、中国等国家,与反对全球化的特朗普的美国等国家正在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个对立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对立。它可能超过了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因为第一霸主国家和挑战者之间的不同而带来的冲突。
郑若麟说:“中国走的发展道路正在取得空前的、历史性的成功。这就给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新的发展样式。这对西方来说是非常难堪,也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西方一直向全世界宣传,西方的普世价值和发展道路是唯一的一条能够致富致强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树立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对西方的选举、民主体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一个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西方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太好,甚至有日益下行的趋势,这样一来,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道路就对他们形成了一种威胁,更加重了传统霸权国家美国的恐惧。“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早就被西方舆论,更重要的是被西方理论界说成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发展只有一个道路,一个出口就是民主化,选举化,走向西方的政治体制。今天的中国不但没有出现这样的趋势,相反却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郑若麟说。
沈逸则指出,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不能触及资本主义体系问题的反思,相反,还必须要继续论证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以及社会治理如今都遇到了巨大的问题。
“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香港一直是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严格执行的缩影,10月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的全球竞争力从2018年的第7位上升到第三位,排在新加坡和美国之后。可是今天的香港,持续数月的修例风波使香港经济受创、社会撕裂,也令昔日被繁华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陆续暴露出来。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1月公布的报告显示,香港贫穷人口攀升至137.66万,贫穷率达到20.1%。”
沈逸说,“高薪的金融及保险业只提供7%的就业岗位,雇佣劳动力最多的零售、旅游等行业往往收入微薄,无法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普通人根本看不到前途。由于资源高度集中在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少部分利益相关者迅速积累财富,但绝大多数香港市民无法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从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终结了。”沈逸说,香港乃至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几十乃至上百年间,奉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虽有助于吸引企业投资兴业,但也缺乏对经济的主导力,在面临外部发展环境变迁、市场调控失效时,很难推动经济结构改革,扭转困境。“欧美心里很清楚问题在哪,但在既存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约束下,只能采取注定是无效的解决方案。他们都逃不过衰朽的宿命。”
沈逸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借着互联网兴起的契机,向全球输出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并在多个“不听话”的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可以说,在初期,这种煽动性宣传和颠覆性渗透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把戏,迟早会出现“失控”进而“反噬”。
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没必要陪着西方国家陷入“比谁更糟”的无聊游戏。着力提升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造福人民,努力建设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真正值得为之奋斗的正确方向。“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自觉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到底哪个更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