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五四?
8月18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著名的“三陈”(陈平原、陈子善、陈思和)齐聚上海图书馆,重返生气淋漓的五四时代,对话关键时刻、关键人物与关键学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刚刚推出了《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一书,陈平原教授是当代重要的五四研究学者。五四运动过去100多年了,现在我们如何回到生气淋漓的历史现场,触摸五四的温度,深入五四的肌理?100多年前的运动,如何与今天的人发生关系,如何让两者之间产生对话?
陈平原教授有话说。

新媒体如何改变写作方式
《新民周刊》:这本书的书名是“未完的五四”,“未完”是未完成、未完美、未完结、未完待续,对五四不断追问、研究与反思,使得五四成为现代学人的重要思想资源,用您的话说:“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您不断地讨论五四,就是要将历史照进现实,让学术上升为精神,是这样的吗?
陈平原:在《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一文中,我曾谈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不无区隔。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喜欢混用这两个概念,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我的立场很明确:“若谈论新文化运动,尽可能往上走,从晚清说起;若辨析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或五四时代,则最好往下延伸,仔细倾听那些遥远的回声。往前追溯,从晚清说起,主要是史学研究;往后延伸,牵涉整个20世纪,更侧重思想操练。或者说,谈论小五四(指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重在考证与还原;研究大五四(指作为思想潮流的五四时代),关键在于阐释与介入。”我的五四研究三书,第一本直接面对,第二本往前追溯,第三本往后延伸。之所以选择三种不同路径,基于五四话题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与现实性。
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们今天有无需要/能力/机缘与日渐隐入历史深处的五四展开深入细致的学术及思想对话?同样潜心学问,不是所有题目都能“将历史照进现实,让学术上升为精神”的。但在我看来,五四这个话题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我多次提及基于学术而又超越学院门墙的愿望,曾表达四个担忧,其中最重要的是“怕成为纯粹的书斋学问,没能因应时代话题,也无法介入现实生活”。这也正是我所说的五四作为论题的重要性,即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新民周刊》: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您提出,从晚清到五四,这种对国家失败的不满与怨恨,透过各种大众传媒与文学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新媒体的产生,危机意识得以迅速蔓延,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因而是产生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这种传播媒介的转变,决定了一代人的思考及表达方式。某种意义上,像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杂文、小品文、随笔的写作,都是这种传播媒体发生改变后的产物?
陈平原:在太平年代,一切波澜不惊,且似乎都顺理成章,你不会想那么多、那么远的。只有设身处地,与五四那代人同样置身于“危机时刻”,你才能感同身受,理解他们的焦虑、愤懑、激情、胆识,以及仓卒应战所选择的策略。这里包含奋斗的方向、思考的深度,还有文体选择。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二章“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中,我专门谈论《新青年》同人基于思想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与个人、责任与趣味、政治与文学之间,保持良好的对话状态,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通信”和“随感”。关于“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这方面的论述好理解,我较为得意的是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新青年》的“通信”,认定其“拟书札”的姿态,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独立思考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力:“通信”作为一种“思想草稿”,既允许提出不太成熟的见解,也可提前引爆潜在的炸弹。除此之外,“通信”还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将不同栏目、不同文体、不同话题纠合在一起,很好地组织或调配。在某种意义上,《新青年》不是由开篇的“专论”定调子,反而是由末尾的“通信”掌舵。如此琐碎的文章,竟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实在是个奇迹。
《新民周刊》:五四时期,旧的教育体制已被打破,新体制及师资建设仍在路上,晚清至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更多地得益于自由阅读,而不是学校的系统训练。这就决定了这一代文化人所吸收的养分,主要来自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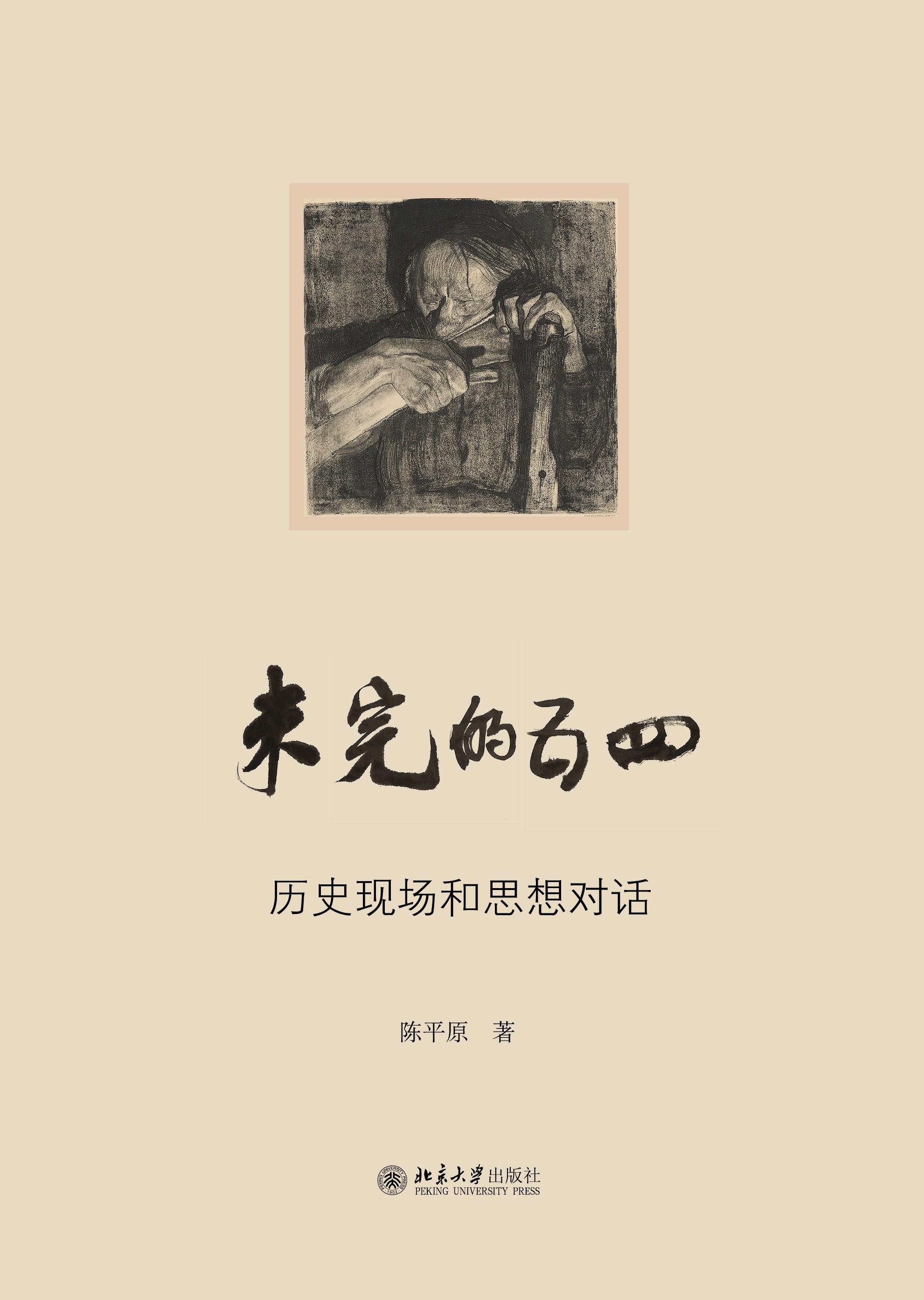
陈平原先生刚刚推出了《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一书。
陈平原:“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不同历史时期,朝野之间力量对比有很大差异。五四时期,政府的控制力度不强,各种思想学说风起云涌,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应该讨论的是,同样属于梁启超所说的“传播文明三利器”,学校与报章之间,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方面有何不同。我谈青年学生“自由阅读”的趣味及习惯,既缘于学校规章制度的相对松懈,也来自各种新媒体在传播新知方面的竞争优势。我们都晓得,一般而言,学校传授的知识比较系统,但相对滞后;媒体对于新知的介绍及时,论述自由,但松散或肤浅。身处狂飙突进年代,知识日新月异,青年学生的阅读趣味很容易偏向于媒体。而在五四时期,媒体不受政府控制,所以,说那一代文化人吸收的知识及精神养分“主要来自民间”,也可以成立。
《新民周刊》:您认为正因为媒体“短平快”的特性,也因为身处危机时刻,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往往脱口而出,不够周密,多思想火花,而少了一些系统性的思考,这个判断是不是同样适用于鲁迅?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该如何思考与表达?
陈平原:我不认为“系统性”就是思维和表达的最高境界。某种意义上,过分强调“系统性”,反而可能落入重床叠屋、夸夸其谈的学院派的窠臼。对于鲁迅等新文化人来说,直面人生苦难的同情心、理解历史的洞察力,以及介入当下社会变革的直接性,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上海十年,鲁迅主要选择匕首与投枪的“杂文”,明摆着就不是以“系统性”为奋斗目标。
关于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思考与表达,我写过不少文章,比如二十多年前的《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强调“阅读过程”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以及‘生命境界’。前者属于公共资源,确实可以金钱购买;后者包含个人体验,别人实际上帮不了多少忙。”至于表达,我关注时势、技术、学养、文体四者之间的张力。之所以表达越来越情绪化,受众立场越来越趋极端,与算法精准推送导致的“信息茧房”有关,也与追求流量以获取收益的写作心态有关。这个状态,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于有理想、有良知的读书人来说,“修辞立其诚”,成了必须坚守的写作底线。
五四运动同时也是说出来的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五四精神非常突出。
《新民周刊》:海伦·斯诺在《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朝鲜三一运动的影响,关于朝鲜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您是否有关注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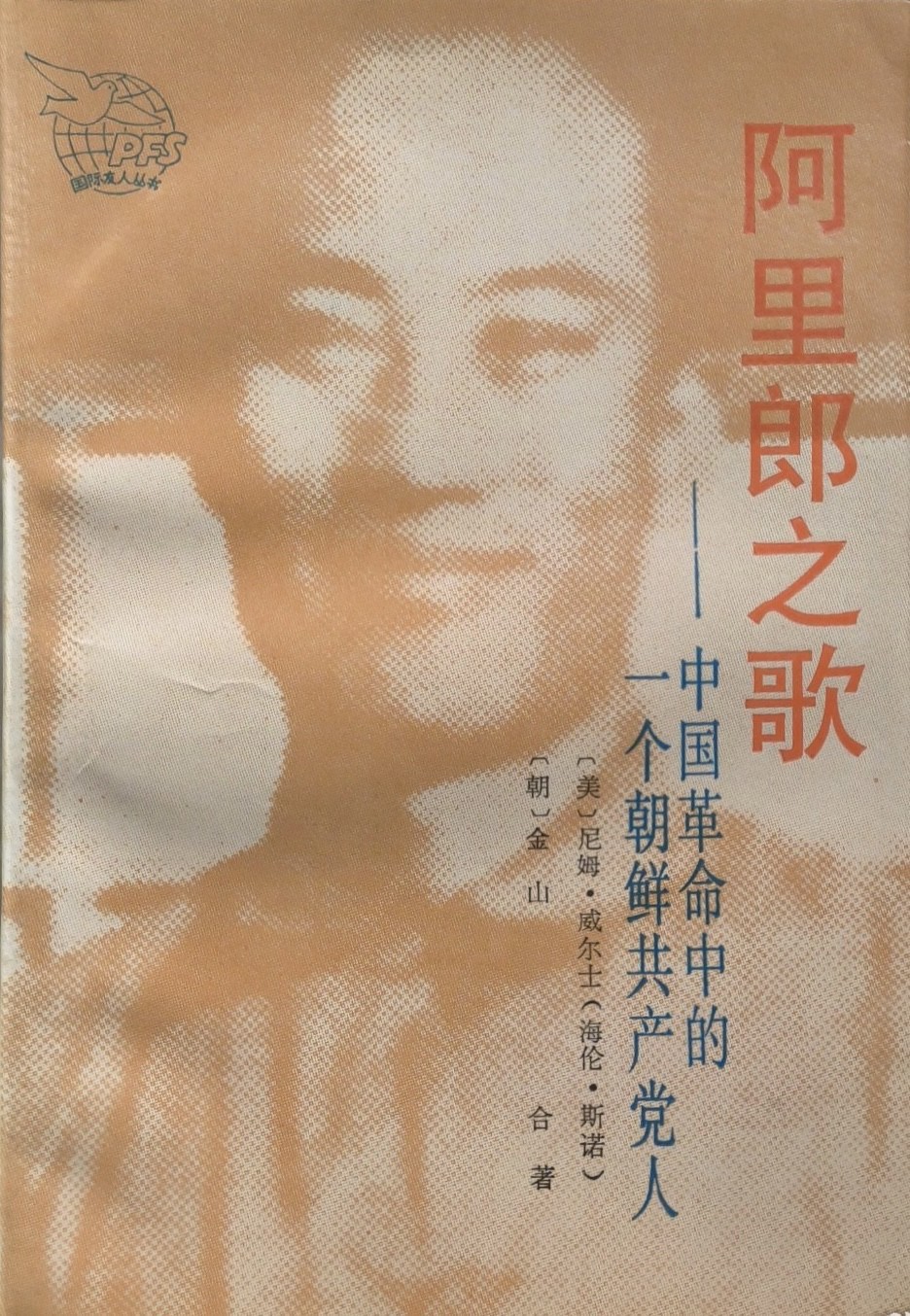
海伦·斯诺《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种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
陈平原:多年前我在韩国演讲,就碰到这样的提问。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朝鲜的三一运动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历史事实,我们从不否认。翻阅五四时期旧报刊,大量有关三一运动的报道,而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等,都曾写过文章大加赞许,表达敬佩之意。应该说,这些资料中国学者都熟悉,比如《世界历史》1979年就已刊发杨昭全的《现代中朝友谊关系史的开端——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间两国人民相互支援的史实》,此后,学界更是不时出现这两个运动的比较论述。可是,为什么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很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都不怎么看重这一影响呢?其中奥秘,王晴佳曾谈及,那是因为我们强调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连续性:“由是,五四就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而五四作为一场由于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谈判挫折而引发的学生游行示威,便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因此它与朝鲜三一运动之间的相似,也就少人注意了。”还应该补充一点,前有新文化运动的牵引,后有中共建党的升华,中间还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群众运动的五四,不再是外交事件的直接反应,更像是兼及启蒙、救亡与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意义不断叠加的过程中,五四运动最初的触媒也就逐渐隐没在历史深处。
《新民周刊》:作为北京大学教授,您如何看待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陈平原: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是干出来的,可同时也是说出来的。作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的主体,北大学生日后不断的追忆与阐释,是五四运动获得巨大声誉且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最早为五四运动或五四精神“命名”的,一是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孟余)发表在1919年5月9日《晨报》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二是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再就是张东荪在同年5月27日《时事新报》上刊出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还有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杨亮功和他的表兄蔡晓舟合编的《五四》,那是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集,出版于1919年9月。也就是说,北大师生很早就有意识地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而从1920年起,连续六年《晨报》及其副刊的“五四纪念”,主角都是北大学生及教授。而后,不管外界压力多大,坚持不懈地记忆、叙述与阐释五四,成了北大师生的职责与传统。这个话题,可参见我的《未完的五四》中谈论“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那一章。
《新民周刊》:普通人对五四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教科书和文学史的经典叙述中,而那些五四时期出版的报章杂志,普通人又比较难看到,那么您认为普通人要了解更为真实的五四该怎么做?
陈平原:非专业读者若想了解更为真实的五四,阅读若干基本文献,我以为是必须的。教科书传播面广,但在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方面,有很大的限制,作者不能不瞻前顾后、左右平衡。有感于此,二十多年前,我选编《〈新青年〉文选》,附有长篇导言,2003年贵州教育出版社初版,201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修订版,至今已印行十二刷。除了选文精到,论述简要,篇幅不太大,适合一般人阅读,更重要的是适逢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故销售状态很好。我甚至以为,若实在太忙,没时间阅读基本文献,那不妨精读以下三文,就能大致理解思想、文化及精神层面的五四:发表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的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的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以及刊于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的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至于学有余力,关注具体史实的考辨,或者学理方面的阐发,那当然是多多益善。记者|何映宇
本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内容和准确性由提供消息的原单位或组织独立承担完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