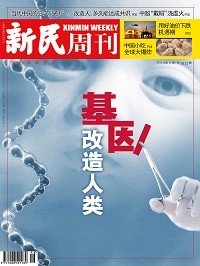张艺谋的岔路
这是一部让我不安的电影。因为它的制作那么精美,有许多动人的细节;获得了如此高的口碑和票房,受到众多追捧。然而奥斯卡眼睛雪亮地拒绝了它。否则殊荣之下,我们再难审视其中的缺陷,我们或者会追从导演编剧们的思路,一味把战争当作罪恶的源头,一味把侵略者们送进审判室,一味暴露他人丑恶的人性;却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需要上手术台的罪人。
看过电影,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那些女人却不是女孩?
这个问题叫我想起著名的哈佛公开课视频,关于正义的第一讲中,桑德尔老师让学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题:你驾驶的火车面临着岔路,却无法刹车,继续笔直向前开,你会压死前面铁轨上的五个人;你也可以选择转弯,岔道上只有一条无辜的生命。你会怎么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大部分人都选择压死岔道上的那个人,因为,五条生命的价值似乎大于一条生命。然而,如果换一个情境:手术室里五个病人,各自因为某个器官坏死而生命垂危,隔壁来了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你会不会偷走他的五个器官去救那五个快要病死的人呢?一样是一比五,你会怎么做呢?这一次,大部分人都摇头了……
《金陵十三钗》向我们渲染的,就是一个类似于此的正义命题:要么开上岔道,让妓女们去受死;要么继续前行,让少女们接受她们的命运?虽然这个命题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这个故事有着先天性的缺陷:一个美国人是否可以接受中国人这样的处女情结,一面拯救少女们的性命,一面把年轻的妓女们推向死亡;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少女,是否真的会无视所受的人生而平等的信仰教育,坦然接受别人性命的馈赠?
让我们姑且假设这样的故事成立吧,的确,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会在潜意识里觉得:处女的性命比妓女的性命更为珍贵。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即使我们讨不得人数上的便宜(这个故事里是13比13),但也不要把苦难加在那些纯洁无瑕的年轻生命上,加在那些残花败柳的头上吧……
在哈佛公开课上,师生们一起发现所谓正义论中的悖论;然而,观众们,是否看到了导演和编剧正义立场背后的虚假了呢?
如果我们的感情和反思只是停留在电影最后书娟“我再也没见过她们”此类平静的回忆和追溯中,却没有为自己性命被挽回、为自己的生存感到些许不安,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因为这样的平静缺少了最起码的生命观,更不要遑论人性和正义了。
那么,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生命观呢?张艺谋严歌苓们其实找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群体:妓女。每次谈到这个群体,我都会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回答。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住了,按照当时的律法,这样的妇人可以被人用石头打死。文士和法利赛人抓着她带到耶稣面前,想看他会怎么处置她。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人们听到这话,渐渐散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决定妓女们的价值甚至生死呢?这些被送上车的十三钗,是双重罪恶的牺牲品:第一重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和侵略者;第二重是隐性的,可以称之为处女情结,文化歧视,或者更彻底地,称之为人性的罪。
岔路前的选择,自然是最有戏剧性的。否则,这个故事就不足以支撑野心勃勃的商业计划。商业也未见得有错,只是,岔路前的选择,原也是纠结的;否则,桑德尔就不用带着学生反复推演其中的种种悖论了——可张艺谋驾驶的列车压过一群风尘女子的身体时,是那样理所当然,毫不迟疑,那粗暴的声音听上去,竟然如此鄙陋而空洞。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