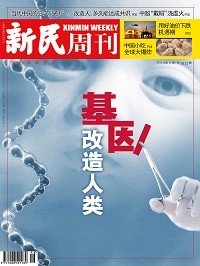连环画的天空
最近小半年里,连环画大师贺友直老先生特别忙,在报刊电视里大出风头,前天,与外孙联袂办画展,昨天,他的《上海风情》上了地铁车站的墙,今天,一列地铁干脆命名为“贺友直号”,明天,贺友直的《孩时玩耍》将被中华艺术宫收藏。有人问:上海难道就没有其他画家了吗,偏要靠一个连环画家顶天立天为上海增光添彩?大上海怎么会没有画家呢?画家遍天下,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数不胜数的画家在上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各领风骚三五天,只有九十高龄的贺友直像艺坛长青树,每天两顿老酒管饱,似乎可以一直画下去。
贺友直以连环画立足画坛,他是一个时代的化身。当然,贺友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上海是中国连环画的发祥地、大本营、大市场,数十年间涌现出许多连环画家,共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现在,光芒正在褪去,恰如晚霞一般美丽的景象让人读出了无尽忧伤。
将贺友直推到聚光灯下,体现了尊老传统,给予至尊的荣誉,也是对连环画历史功绩的肯定。
有人说连环画在长沙西汉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就有了,也有人说连环画是电影的祖宗,更有人考证清末吴友如是上海连环画的教父,还有人发现1927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连环画三国志》,这就是中国第一套连环画。这些话与考证或许都没错,但我更愿意引用连环画收藏爱好者崔永元的一句话:“小人书(连环画的另一种称谓)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上路了。”
正是如此,成千上万个孩子就是看着连环画来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观的。归琪就是这样的孩子。
归琪认为:中国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进入高潮,这缘于中国80%的文盲基数和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及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解读的要求。连环画在新的形势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连环画创作任务重塑艺术家的艺术品格,画家根据时代要求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再塑造读者的人格。这个大循环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小环境,也是特别让我们怀念的理由。
“败家子”在连环画中获得启蒙
归琪出生在供应极度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7岁时刚刚进学校,又遭遇了不能正常读书的“文革”,他跟随父母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地老天荒、孤苦伶仃的日子里,幸亏有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几本连环画,使他的童年出现了一抹惨淡的亮色。“一本是杨青华画的《擒孟达》,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本,另一本是顾炳鑫画的《列宁在十月》,里面的字和情节我不能全懂,但看得如饥似渴,差不多翻烂了。这两本连环画里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阶级斗争的迫切性与残酷性,有古代圣人的足智多谋,还有革命阵营里伟大人物的风采,主导那一时期中国人思想行为的要素,差不多都满足了。”归琪说。
不久归琪又跟父母来到江西南昌,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识字越来越多的他理所当然地迷上了连环画,而那时政治气候也有所松动,为了配合宣传样板戏和英雄人物,连环画画家也走出牛棚,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动笔了,这构成了中国连环画另一个繁荣的景观。为了买连环画看,归琪伸手向父母要钱,但要的次数多了,常常吃“弹皮弓”,于是归琪整理家里旧报纸、旧雨鞋、废铜烂铁,拿去与收旧货的小贩换钱,甚至在刷牙时会恶狠狠地将牙膏挤出一长条来,缩短一支牙膏的寿命,然后将牙膏皮拿去换钱,得了钱再去买连环画——他就是这样的败家子。历史证明,以败家子作风爱好某件事,必定会获得成功。归琪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说:“当时连环画里英雄人物的言行举止,以现在的眼光看也许有点假、有点傻,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给读者的震撼是强烈而不容置疑的,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与模范,那种正义感与牺牲精神,至今让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连环画教给我的东西,远远超出老师和父母灌输给的我枯燥理论。”
“文革”结束后,已经是中学生的归琪跟着父母迁到了上海。喜爱读课余闲书的归琪遇到了一个好时机,当时外国翻译小说开始解禁,他每天看到新华书店门口人山人海,排队买书或交换书的盛况令人亢奋,归琪也有通宵排队购买中外名著的壮举。他尤其偏爱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长篇中篇,各种版本都要,现在他家里收藏的陀氏小说就塞满了三个书柜,大陆版本之外还有台版的。
与此同时,连环画也以自身的艺术姿态呼应了思想大解放,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在此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况。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出现井喷,连环画也载歌载舞,积极跟进。这一时期归琪收藏的连环画赫然见证着刘心武们的成果:《班主任》、《伤痕》、《乔厂长上任记》、《芙蓉镇》、《爱情的位置》??如今抹去浮尘稍作翻阅,竟有隔世之感。
归琪告诉我,这一时期获得解放的各地连环画画家手脚发痒,浑身是劲,没日没夜地画,也不讲究,小说拿来就改编一下,画!一本连环画一个月就完成了。中国连环画迎来了又一个高潮。
《暴风骤雨》遭遇“高山流水”
1983年,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归琪进入中星房产公司工作。有了钱,他就在中学时代积攒的第一批藏书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收藏行动。他常常去文庙赶早市,天不亮就怀揣着两只刚出炉的大饼一头钻进书堆,别人不注意的,甚至是老板也不知道其价值的连环画,他一眼就能从乱书堆里找出来,一番讨价还价,斩获。另一条渠道就是与藏友交换,互通有无,这也是扩大搜索圈的有办法。有一次,另一位连环画收藏家在文庙看到一本1955年的初版本《暴风骤雨》,老板开价600元,在90年代初,6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藏家还价至550元,双方谈不拢,一拍两散。此事被归琪知道了,他前去看了一眼“货”,品相极佳,当场付钱。几天后他又去文庙,老板跟他说:“来啦?在你前头看中这本书的人也来了,现在他愿意出到一千,但书已经归你了,你们不妨认识一下吧。”归琪由是与这位藏家结缘,此后经常交流收藏心得。
此后十多年里,这本《暴风骤雨》在旧书市场上极少露面,成了藏友的苦苦追寻目标,有人找到归琪,前后出到3000元、5000元,最后加码至3万。归琪找到那位与此失之交臂的藏友:“你找了它很久,我也一直珍藏着,今天人家出到3万,老实说我有点挡不住了,与其给人家,不如归你所有吧。”归琪献出了自己的珍藏,却不要藏友一分钱。这位藏友叫张奇明,后来经营大可堂文化公司。大可堂在襄阳路一幢老洋房里卖普洱茶,雍容典雅的环境里陈列着许多连环画珍本,也算海上一景吧。张奇明在增加收藏之余,还与出版社联手,使绝版的连环画得以重版再世。
签名售书时的“龙头老大”
几十年的孜孜寻求,归琪收藏的连环画已经超过一万本,满满当当地挤了好几个书柜,不少成套的珍品以及民国本都是市场上可能引发一波争抢的亮点。但归琪与一般藏家不同,他不愿谈升值几多、行情如何的话题,他只愿谈某本某套连环画的创作背景,画家风格,出版曲折,存世情况等“专业话题”,特别爱跟人讲与某画家的交往故事。
归琪与老画家顾炳鑫关系很好。归琪告诉我:“顾炳鑫在解放前是公交公司的售票员,完全是自学成才的画家,平易近人,与他交往没有任何障碍。我陪他去看牙病,读了外国名著后也跟他谈谈读后感,后来就可以看他作画了,他这个人基本功扎实,拉出来的线条比人家用尺画的还直。他的辈分比贺友直都高,在连坛早就有北刘(继卣)南顾(炳鑫)之称。有几次他甚至提出要收我做徒弟,但我觉得自己不会画画,就婉拒了。”
归琪与刘旦宅的结缘也相当有意思。归琪早期收藏的连环画中有不少出自刘旦宅手笔,他非常痴迷刘的构图与线条,认为有大格局和大气象。后来凡有刘旦宅参加的画家签售活动,他必定早早赶到,排在首位。他知道刘旦宅有傲气,参加签售只是出于情面,在签了十几个后就抽身走人。但多次以“龙头老大”形象出现的归琪,给刘旦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归琪还拿出刘旦宅在“文革”前创作的连环画请他签名,让他与旧作意外重逢,发今夕何夕之叹。终于有一次刘旦宅写了一张便条给他,上面写着刘宅的地址。
从此,归琪就可以径直叩开刘的画室求道问学。刘旦宅曾参与全套连环画《红楼梦》的创作,而归琪藏有品相极佳的初版《史湘云》以及从印刷厂里流出来的全套纸型,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激动,刘旦宅就给归琪题了“二石屋”的堂名,此后还送他画稿。
与画家结缘,使归琪收藏到几百本签名本,上海、外地的连环画家都愿意与他交朋友,甚至是忘年交。有些老画家历经磨难后,自己在几十年前出版的作品也找不到了,出版社里也没有留存,归琪就将自己的藏品慷慨相赠,自己没有的,就千方百计去市场里找熟人,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来,满足老画家的心愿。另外,归琪还将一套《阿Q正传108图》赠给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将《流泪的红蜡烛》、《山菊花》送给了这两部电影的主演倪萍,《五朵金花》、《阿诗玛》的主演杨丽坤去世后,电影界准备开个纪念会,组办方找到归琪,希望得到这两部电影的连环画,归琪二话没说,找出来后就马上送过去。冯骥才、崔永元与归琪都是好朋友,先后造访过他的藏室,交流收藏心得。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一书里称归琪“是上海小人书一族中的强人”,还形象地描写:“晚上,归琪席地而睡,因为小人书睡在床上。”
连环画也是国家记忆
因为收藏、喜爱连环画,归琪还给品相稍差、但很有收藏价值的绝版连环画做精装本,绝对是专业水平。这一绝活后来启发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们就着力提升连环画的品级,推出“小精装”满足收藏一族。包装一改变,就轻轻松松多赚了几百万利润。
新民晚报在十多年前,在由戴逸如主持的版面上连载画家原创连环画,引起读者极大兴趣,归琪每期不拉剪下来,编辑装订成册,再请画家题签,在出版社未能出版的情况下成为孤本。
有些连环画在50年代出版,后再没露过面,归琪就献出自己的版本,并担任策划人,促使出版社再版,获利无算,而连环画藏友无不欢呼雀跃。
“文革”中为配合形势,最先获得“解放”的一些画家也根据样板戏创作出版过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就是第一本推出的。据归琪说,此事起于1970年,这“重大工程”还经过毛泽东的圈阅同意,由中央文革小组一竿子到底来抓,江青亲自过问。怕我不信,他就抱出一大堆资料,一本《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十品。“但这个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只牛皮纸袋里的原始资料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由刘旦宅、戴敦邦、张楚良为主要创作人员,再加一位工人画家邓泰和和一位来自空四军的画家李伟信,各人有具体分工,内容由刘、戴二人执笔,邓补景,张画封面,画好几幅后就得空运至北京,让江青审查。江青提的意见还非常具体,敌我在画面中的位置以及角色的表情,都得按照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要求来表现。”
一张当年的文汇报,头版头条就是定稿的连环画《智取威虎山》人物造型,以及关于连环画成功移植样板戏的长篇报道。还有一本本泛黄的、纸质粗糙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每个画家在某次创作会议上的发言,我在里面居然还看到了文汇报驻京记者艾玲的发言,她对本子也有具体意见。她是参与创作,还是衔命而来?得细看内容才能知道。但那个时代的词汇、术语、句式、结构,以及思维逻辑,鲜明地刻录了荒唐岁月的印痕。
《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出版后不久,林彪垮台了,来自空四军的李伟信被抓,然后北京成立了专案组,对参与创作的画家进行长达两年的审查。这些材料也被归琪收藏了,刘旦宅和戴敦邦的检查也是老套路,劈头先把自己骂一通,然后山呼万岁收尾。
这种更像档案的连环画及衍生品有价值吗?“当然有,很有价值!”归琪肯定地说。“这是中国非常时期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产品制造方式的真实全记录,属于国家记忆的性质。这些年来,我一直与连坛的老前辈及志同道合者商量,要筹建一座连环画博物馆,如果这座博物馆建成,我可以将珍品捐出来,特设一个‘文革’连环画陈列室,让今天的青年人知道中国连环画曾经有过的辉煌,曾经影响过多少读者,还有它一步步走来的历程,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读懂这些,才会知道中国连环画与今天的快餐式的动漫产品在本质上有着怎样的区别!”
【请注意:新民周刊所有图文报道皆为周刊社版权所有,任何未经许可的转载或复制都属非法,新民周刊社保留诉讼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