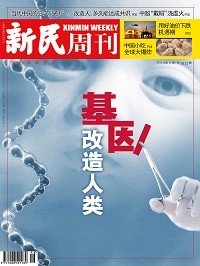让人着魔的《哈扎尔辞典》
撰稿/曹元勇
可以说,打开《哈扎尔辞典》,亦即打开了一个穿越时空、融汇现实世界与神秘之域的超级文本;而对它的阅读,则会成为想象力被彻底激活的过程。
维特根斯坦有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即:“面对不可言说的事物,应当沉默。”如果放到逻辑哲学的范畴里去考察,这个命题毫无疑问是非常严密的。但是,世界上总有一些事物,越是不能言说得确切和明了,就越是让人着了魔似的去谈论它。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奇书《哈扎尔辞典》让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既兴奋又困窘的状态。这位自称是“最后一个拜占庭人”的作家,总共创作了五部洋溢着浓烈现代巴洛克情调的超小说。在每一部作品中,他那些匪夷所思的架构和叙述,既娴熟地使用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花招和元素,又深深地根植于巴尔干诸民族繁复的历史土壤和神秘的民间传奇。这样的作品,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无异于是布下了颇具诱惑力的危险陷阱。拿《哈扎尔辞典》来说,无论是着眼于这部超小说开放的立体结构或无处不在的进口与出口,还是着眼于弥散在作品中的宗教的、神秘主义的思想元素,或是着眼于这部超小说与随着它的问世、没有几年就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神秘的隐喻关系,任何文学的批评都会因为只是聚焦于某个侧面,而与这部作品完整的真实面貌相互游离。这就像作品中所写的哈扎尔族阿捷赫公主的两面镜子:“快镜”在事情发生之前将其照出,“慢镜”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照出;如果你同时去照这两面镜子,必将招来猝死之横祸。
尽管这样,对于热衷想象或爱好在梦幻疆域漫游的读者来说,只要打开了《哈扎尔辞典》,他们最终都会像那些忘记了寻宝目的而只顾享受寻宝过程中的神秘和乐趣的寻宝者一样:或是迷醉于作品里层出不穷的像诗句一样纯粹的警句格言式的语言之美;或是在公元9世纪、17世纪和20世纪的不同时空里往返穿梭,试图解开已经消失的哈扎尔捕梦者教派的秘诀和奥妙;或是沉浸在出自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个教派互相交叉又互相抵牾的各种所谓“史料”,领悟三大宗教对人类始祖元神的神秘解释,执著而又徒劳地试图理清哈扎尔汗国改变宗教信仰的历史真相。可以说,打开《哈扎尔辞典》,亦即打开了一个穿越时空、融汇现实世界与神秘之域的超级文本;而对它的阅读,则会成为想象力被彻底激活的过程。
实际上,《哈扎尔辞典》的强大魔力不只会让你沉迷于这部作品本身,它还会彻底激起你的好奇心和探求欲,让你顺着各种蛛丝马迹,去搜寻一切与这部“辞典”或它的影子相关联的资料。比如:拜占庭东正教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在巴尔干地区、黑海地区冲突和角力的波荡历史,从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定居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的哈扎尔汗国的奇异传说。作为一部伪称由历史文献汇编而成的“哈扎尔百科全书”,《哈扎尔辞典》不是封闭性的,而是永远处于不断生成的敞开状态。因此,有心的读者如果从历史著作中摘编一些与其内容相关的资料,就会对它构成很有趣的、具有文本增延意义的补充。
比如关于哈扎尔汗国。这个在公元7世纪到10世纪曾经声名显赫、一度皈依了犹太教的游牧民族国家,在其消亡后,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可资考证其存在的痕迹。然而,对它的记忆又确实未曾彻底消失,因为“哈扎尔”这个名字在不同民族的地理语言中都有保存。以里海为例,在阿拉伯人的语言中,里海被称为“Bahr al-Khazar”,而在突厥人的语言中则是“Hazer Denizi”。在中世纪的时候,地中海的水手驾船驶往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时,目的地在他们的称呼中则是“Gazaria”,仍然包含着“哈扎尔”的名字。另外,虽然哈扎尔汗国在历史上曾经与拜占庭帝国结过联盟,但关于这个汗国有限的历史记载中有一大部分却是出自阿拉伯历史学家之笔。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历史学家马苏迪在他的《黄金草原》中,对哈扎尔汗国有过大篇幅的记述。在他的笔下,如同在中世纪波斯和中国的史书中,哈扎尔被称为“可萨”。他写道:“当时商定每当可萨国王与伊斯兰教徒们发生战争时,那些在其军队服役的穆斯林则单独驻扎在另外的一个军营中,不攻击他们的教友,但他们向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发动战争。”假如将这样的片段插入《哈扎尔辞典》的犹太教资料部分,或是变成其中的附录或辞条,一定会起到难辨真假、与《哈扎尔辞典》其他部分互相补证的奇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