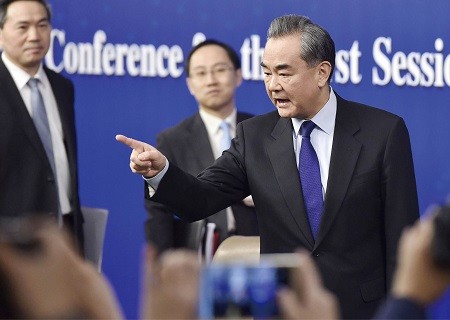一部70年代人的青春成长圣经
阅读提示:青春、性、亲情和友谊,连同背叛、怀疑和放纵,共同构成了一场另类的新时期历史的少年春梦。
撰稿|房 伟
在那个叫做临河城的梦想之地,有一群疯狂的少男少女。他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他们的青春以欢乐的寻找为由,以痛苦的创伤而终,以出走的成长为由,而以回归的挫折为终。他们的抵抗,如同他们的妥协,他们的放纵,如同他们的孤独,都给我们长久的思考和感动。瓦当的《到世界上去》以忠实的笔记录了一个时代最为私密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属于一代人的情感记忆。青春、性、亲情和友谊,连同背叛、怀疑和放纵,共同构成了一场另类的新时期历史的少年春梦。
这是一部以“轻逸”的方式书写历史的70后之书,一部有关70后一代人情感记忆的青春成长圣经。卡尔维诺曾在《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这样为我们解读了“轻逸”:“寂静的山谷中飘落的白雪”。他以文学的情感和想象的“轻”,来瓦解这个世界的沉重。同样,瓦当无意于“大历史”的书写,却无意间以轻逸的笔触,完成了70年代人的历史体验。小说中,有严打、对越自卫反击战、全民经商等大事件,但全然是作为背景,真正构成情节推动力的,则是1980年代以来的气功热、日本电影、港台影视剧、网络游戏等生活细节层面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革命宏大叙事趋于解体,而新的宏大叙事在暧昧中不断整合生成的长时间段。瓦当以其高蹈游走的轻逸狂想,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属于梦想和激情的70年代人的情感记忆。
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也在于小说家纯真的青春激情。瓦当的这部小说,以其华丽的纯文学先锋性与内在的真诚反抗,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作家应有的自尊。塞林格的忧伤、凯鲁亚克的狂放、黑塞对童话的迷恋、村上春树般的优雅细致、渡边淳一的坦荡率真,与太宰治的颓废,都奇怪地扭结在了瓦当诡异而又激情四溢的青春叙事之中。而这些70年代人的青春故事,是由一系列青春人物在小说中的内爆完成的。当凯鲁亚克在小说《在路上》中,漫不经心地写道:“自从狄恩·莫里亚蒂闯入我的世界,你便可以称我的生活是’在路上’”,我们便发现,一个神秘的人物,往往成为一种至死不渝的生活方式的神启式的开端。而《到世界上去》的导火索式人物乃是郑成。郑成是孤独的,他既缺乏友谊,也没有爱情,他也不愿与家人交流。他以绝望的出走,实现了青春对现实的一次脆弱的反抗。而后,假郑成和王大勇的男性爱,林丽美对婚姻的逃避,刘小威和小玲玲、王小勇的爱情纠葛,白面的死亡,都成了青春成长中不断的逃离和反抗。
在瓦当笔下,存在着两个情欲世界,一个是成人的滥情世界,刘小威的父亲,是这个世界的代表。他们对情欲的追逐,源于自身的空虚无聊,而止于无穷无尽的欲望。另一个世界是青春的情欲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纯真和坦诚。这个流溢着情欲的世界,是少年们反抗成人的虚伪和专制的秘密武器。以死亡和性爱的眼花缭乱的游戏,形成了众多叙事的可能性与喧嚣的合唱。瓦当操持着语言的炼金魔法,不断从一个人物的叙事角度,跳跃到另一个人物的内心。他有时煞有介事地以一个故事增殖出另一个故事,又以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有时又恶作剧地用一个故事,消解了另一个故事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他时而迷恋拉伯雷式泥沙俱下的欲望书写,时而无意间锻打出干净朴素的节制抒情。
瓦当是一个好奇的顽童,又是一个多情热烈的潘神,他更是一个语言的巫。他神奇的语言,犹如月光下的飞鸟,滑翔于幽蓝的湖面,闪烁着流动的金属光泽,又好似清水中的刀子,冷冽逼人,又热情犀利。瓦当以少年般的骄傲与清澈,质问无情的岁月和历史,索要我们狂想的青春与永恒的疯狂。到世界上去,我们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