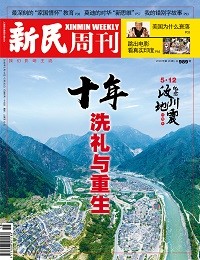那场雪的底下,是北方坚实的大地
阅读提示:小说的虚构和现实之间到底应该是种什么关系?
春节前的一天,我和一位学中国哲学的老同学闲聊。他说最近他开始看点小说,以前看得少,现在觉得小说好像比现实更加真实。他不是在评价社会上的某些事,我们好像很少聊时事,当然,更少聊文学。可能是因为比较起来,我从事的工作与文学的距离要稍近点,他说这话的时候,望着我,笑得不是那么自信。
后来我一直在想小说的虚构与现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说“一直”,不是说老在想,只是因为想不明白,这个问题老搁在那儿。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读完了双雪涛的《飞行家》。
刚读的时候,我就在朋友圈晒了书。倒也不完全是因为虚荣,有一点虚荣吧,还有就是想回应一下袁复生,他曾经是湖南最好的书评版编辑,也是书评人,如今创业转了行。袁复生在朋友圈说两三年前就有人向他推荐了双雪涛的小说,他一直到现在才看。“文字节奏感非常棒,是纯正的好中文的样子”,他说。因为袁复生的推荐,我才买了这本书来读。
我在朋友圈晒了书,点赞留言的人中有八零后作家郑小驴。他问我好不好看,我说我不敢说不好看,他说那是当然。我再不懂我也知道确实是好看,确实“文字节奏感非常棒,是纯正的好中文的样子”。但是我也有我的疑惑,还是那个问题,小说的虚构和现实之间到底应该是种什么关系?
现在我在看《飞行家》这本小说集的时候,我好像想明白了点。我说得可能不够准确,更准确地说是我在看《飞行家》这本小说集的时候,大概明白了我自己阅读小说的偏好,对现实感的喜爱压倒了语言游戏般的虚构,后者,或许可以称之为“魔幻”。
就以《光明堂》一篇为例。当叙述进入到“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块大玻璃后面”,继而开始“我”与“影子”之间虚幻的对白,我开始变得没有耐性。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读者对结尾这部分的理解各有不同,有说三个主角都死了的,有说两个活了一个死了的,各种说法都有,不一而足。谁死谁活的结局我其实并不关心,但是读者出现不同的理解,显然这是因为作者在写这段的时候,采用的手法所致。作者可能有他自己的意图,暗藏着他对全篇故事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有什么寓意(也有朋友用了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既然这段对话是要补足之前并没有交待的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为什么要用这种“魔幻”的写法?
文学评论家可能有他们的解读,他们解读起来可能精妙绝伦。我只是在说我个人的喜好。谁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小说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似乎还是在于它所包裹着的巨大的现实感,它能抵达现实所不能抵达的真实。《光明堂》的前半部分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就在于那场雪的底下,是北方坚实的大地,是曾经有过的生活,和那些人的命运。我希望读到更扎实的小说,对现实有更深入的洞察,而不是一下子就虚了,用技巧来表达某种需要读者来猜的意图。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建立在沉潜在水下巨大的冰山底座的基础,唯其如此,露出的冰山一角,才能倒映出它屹立不倒的理由。而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湖底到底有什么?
双雪涛好像很喜欢这种写法,忽然间魔幻起来,我不知道其他读者是不是和我有同感:当他魔幻起来的时候,就没了现实(或现实感);而当他现实起来的时候,让人完全无法相信一个如此年轻的小说家能抵达如此厚重而尖锐的真实。这本小说集的腰封上写着,“为故事而生的人,最纯粹的小说家”。我不知道这是否在说他如何写作,我只知道他在写作的时候,雪落在北方,并不在乎这些问题。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