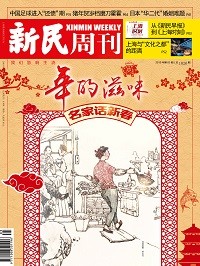人间何幸有草木
撰稿|沈崴崴
若问世上有什么事物,人们爱它,可以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阶层,虽百折而不损,一见忘情,刹那间的喜悦皆发乎天真,那一定是植物了;若问世上有什么事物,它之待人,亦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阶层,赋予同等的青葱润目、芳香沁鼻,那也必定是植物了。当我拿到苏西这本《花见花离》,细细展读,忍不住就想起三个字:不辜负。花不负人,人亦不负花。
她书写了于闽地所见的60多种花草树木,它们穿过漫漶的时间、流离的地理、起伏的生涯,此时相见、彼时离散,花开是见、花落是离。而见与离,本就是循环,是轮回,有见即有离,有离亦将有见,犹如一首回旋曲,一阕回文词。
阿方斯·卡尔曾说过,爱花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生物学家式的,他们制作花的标本以兹研究;一种是收藏家式的,他们只关心稀有品种以示炫耀;一种是普通人的,他们爱花只因为它是花,是美和芬芳。看过了这本书,你会知道,普通人式的爱好也分两种:一种是无谓的,见时固然雀跃,不见时也不特为想念;一种是关情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这本书里,草木不惟是草木,不惟是“抛书人对一枝秋”案头清供时的恬静赏玩,更是生命里成长与悲欢的见证,是陪伴与抚慰、寄托与领悟,这才是所谓“与草木同喜”之喜也。当我看到她写幼年时兴冲冲播下牵牛花的种子等待开花,我也想起我的童年,在平房前的竹篱笆下如何埋下牵牛花籽,如何急不可待每天撬开泥土看它们有没有发芽,如何在花开时轻触柔嫩的花瓣如同抚触婴孩的皮肤,那感觉穿越几十年的时间如何至今仍依稀停留在指尖,同样的记忆带给我别样的欢欣,而世世代代直至将来都有这样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吧,如王小波所言“这种感觉,古今无不同”。而当看到“木香”那一章,我是心惊的,她在荒郊野外遭遇满山盛开的白花木香,这寂寞的澎湃令她驻足不前,目瞪口呆;我亦想起某年某日,在一场台风里,我在厦门的山中看着整座峰谷的相思树一起撼动它们的枝桠,向着天空与大海奋力挥舞,那激越与呼啸带给我巨大的共鸣与震颤,也令我裹足流连,舍不得离开。这无人得见的汹涌与狼藉是海难式的,而沉船后静静的海面、静静的记得,相信我,朋友,“古今无不同”。
其实人间何幸有草木,自诗经的年代,浩瀚的草木牵引着浩瀚的悲喜,留下浩瀚的诗句,科学不能解释为何人能与之共情,正如与流云皓月、迷空瀚海,人的情感有多少细密,草木就有多少繁复;人的思绪有多少幽微,草木就有多少姿容。科学尚不能解释为何人会寄情于斯、移情于斯,而草木又为何亦似当得起所有这些托付,君不见那些上百年的花木,其身姿仪态都似在隐隐吐露所经历的战火、年代与爱恨吗?我爱这本书里的花解人语,人亦解花语,两不相负。
60多种花,60多篇文,从2011年到现在,仍在书写;那语句貌似是散淡的,其实是密集的——密集地在时光里穿梭,古今中外;密集地在情绪里穿梭,哀乐悲欢;密集地在地理中穿梭,天南地北;密集地在生活里穿梭,柴米烟火……这种密集让你惊讶人与植物之亲密竟能丰盛至此,这种密集也常常让我一篇终了需要阖上书页,体味一下心中轻轻泛起的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