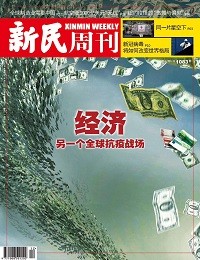揉碎时间,只为还乡
“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一百年前,海明威初到巴黎,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于此,写下了这段话。一百年后,我们的诗人于坚多次游历巴黎后写下《巴黎记》,但他笔下的巴黎与百年前如出一辙。
这就是巴黎的独特之处。
在雨果眼里,巴黎无论如何变迁,它仍是一座岛屿,存在于塞纳河边;在徐志摩心里,巴黎是高于天堂的存在,更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而在冯骥才的口中,巴黎是一个处处张扬爱情和甜蜜的吻的城市,且他们“接吻的语言十分丰富,决不千篇一律”。
诗人于坚则觉得巴黎是一种矿,是巴黎本身创造了巴黎这种东西。“就是摧毁了巴黎本身,这种巴黎矿也不会消失,这种矿物质已经成为超验的,蔓延在人类的欲望中。”
“到巴黎去”,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欲望。
“巴黎是亚文化的天堂,也是道统的根据地,卢浮宫的南方是奥赛,北面是巴黎圣母院和蓬皮杜中心,每一个都是一种文化的道统,卢浮宫是世俗的万神殿,像一个巨大的陶罐,包容着一切。”
《巴黎记》没有按正常的体例进行,它把时间揉碎了,把时空颠覆了,只为诗人能找到一条通途,寻回精神的故乡。
开篇是一首写于2005年的诗,日子却滑到2011年的10月18日,诗人于坚用一道门开启全书的序幕,这一道用了百年的门,“漆色褪去,露出松垮的木纹,缝很宽,塞得进一根长棍面包”,此刻诗人眼里的巴黎是幽暗的,是暮霭沉沉的,像是一个废墟,他将住进一栋废墟里。
转瞬诗人又将日子切到了他初到巴黎的1994年,那年诗人已经40岁了,但是第一次离开故土去往巴黎,在海关,他被声色俱厉地盘问,像是一场逃亡。一路上,他想象着巴黎,那个闪闪发光的地方,想象着自己穿过水泥森林和玻璃幕墙,在天堂般的浴缸里躺着看落日余晖。事实上,巴黎最初的印象竟是“像一场原子弹爆炸”。那个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笔下的巴黎竟如此不堪。
诗人不是失望,而是需要重新梳理对巴黎的认识。
时间再切回到2011年的10月25日,诗人开始以细碎的笔触描述一个人的房间,那是一个典型巴黎人的房间,剃须刀、肥皂盒、眼镜框、磁带、香水瓶……每个房间都有落地窗,窗前都有花盆和杂物。在这里,他想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诗人,曾凭着一种激情和浪漫主义不顾一切投奔巴黎,最终未逃脱庸常而离开,只是也没有再回到自己的故乡。
全书在这种蒙太奇的时空切换中,完成了近一个世纪的巴黎追寻之路。诗人适时以自己擅长的诗歌和近乎黑白的摄影佐之,恰到好处地在纸上还原记忆中的巴黎。
“一些事物的真理走向隐匿,一些事物的真理在敞开,世界运动总是此起彼伏。 ”于坚在《建水记》里这样说。建水记是其古典的乡愿,充满了哀愁和相望。相较之下,那个以幽暗扑面的巴黎成了于坚挥之不去的故土执念。某种程度上,建水完成了他对故乡昆明的还愿,而巴黎则重塑了他对故乡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