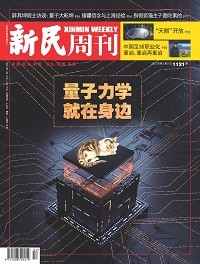傲世天才的传记滑进了小格局
曾经在词学课上听老师说,有的作者专门喜欢写鉴赏,翻来覆去,十六个字:“上阕写景,下阕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哄笑之余,引以为戒,每欲发议论都先暗自掂量,别掉进“情景交融”式的陈腐窠臼里去。其实陈言难去,还是论者眼浅,没材料总是酿不出好酒。偏偏有一类电影,就属于我因为无知而很怕露怯的——比如大卫·芬奇的新片《曼克》。
真人传记类电影,总给我一种拿着谜底倒推谜面的感觉。而当谜底是《公民凯恩》这种被电影课堂奉为圭臬的教科书影片,拆解谜面简直可以类比给江西派的诗作注释,大家提心吊胆,你张我望,就怕一丝错漏,贻笑大方。
思来想去,本来就无知的部分,现补是来不及的,只能透过现象看电影。《曼克》在剥离若干知识背景后,仍然可以被归入天才传。“天才传”素来两大看点,一是抽象才华如何绽放,二是具体人生如何拧巴。《曼克》在这两点上的成绩,后者要高过前者。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本片的时间线令我很不舒服,时断时续得没有道理。观感就像当初听讲《兰陵王·柳》的时候一样莫名其妙:一箭风快,半篙波暖——望人在天北?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怎么就跑了呢。有人说这个时间线是向《公民凯恩》致敬,我说不好,反正感觉不应该是这么个致敬法儿。至于一些明显是致敬的地方,比如台词的直接引用,将《公民凯恩》中描写美丽女性的话语移植为曼克的内心独白等等,顶多是彩蛋,算不得对影片本身有什么帮助。作品跟作者的关系,从来是坐实就丧失风味。属于作品的情致风流,并不能够、也不应该非要在作者的生活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目标。非要说关汉卿是铜豌豆,曹雪芹是贾宝玉,钱钟书是方鸿渐,难免“给个棒槌就当针”的冬烘嫌疑。
抛弃时间线带来的观影别扭,男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还是逐一摊上台面:酗酒,嗜赌,有忠诚的妻子,有精神恋爱的暧昧对象,算是个天性善良的个人主义者。至此拧巴的材料足够了,正需要才华支撑好打丑陋现实响亮耳光之际,影片却断了线。时间线破碎的恶果是只能给观众一个平淡如水的直接描写:曼克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写出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然而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谜底,并不需要透过谜面来猜测。于是,男主的拧巴就如同男主的形象一般瘸了腿。曼克在赫斯特神庙般的宅邸中央,同着众人醉醺醺发表的那篇堂吉诃德演讲,按说是全片的高潮。加里·奥德曼演得真不错,对手查尔斯·丹斯爷爷暗藏峥嵘的风格也很棒,然而就完了。观众到底没搞清曼克为什么拧巴,以及这种拧巴的后果和谜底又有什么关系。当然了,大家可以去查资料——可是看电影总不该随身携带资料簿吧。这是影片本身该做而并没有做好的交待。
不回忆也想不起来,我还看过不少大卫·芬奇。同样是他跟网飞合作,《纸牌屋》纵然天火地火了好几年,我就觉得观感差着一口气,横向比不上同名英剧,纵向比不上《消失的爱人》。个人单枪匹马横挑整个制度,不管是功成骨枯的惨烈还是血肉献祭的屠戮,都算是美国电影的经典题材,但其实并不是芬奇擅长。他更适合诡谲绾结的谜语,在快刀斩乱麻的爽利中,逗露出人心的幽微和黑暗。《曼克》本意是一部孤标傲世天才传,结尾却滑进“儿曹恩怨相尔汝”的小格局里头,虽然是现实,也多少有点浪费。(撰稿 薄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