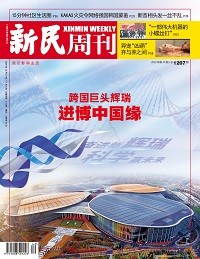我们杀死动物,然后想念它们
1515年,德国画家丢勒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木刻版画《犀牛》,画面中的犀牛好像披着骑士的盔甲,四肢粗壮,布满鳞片,眼睛像牛,耳朵好似猪耳,鼻子上的角既长且薄,向上挺起近45度的角……在创作这幅画之前,丢勒其实并没有见过犀牛,他只是根据目击者送来的一张草图,再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这个犀牛的形象。令丢勒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犀牛的形象大受欢迎,不仅受到时人的追捧,而且还被英格兰、比利时、法国的自然历史书和百兽图录所复制,成为犀牛与“概念的犀牛”的合体,甚至取代了真实的犀牛形象。丢勒笔下的犀牛就像是人类之于动物的“一种传声筒游戏,是长达几个世纪不断验证和修正的名字、形状、误解以及被赋予的意义”。
美国作家埃莱娜·帕萨雷洛的《动物奇形录》是一部旨在探讨人与动物关系的著作。作者并不是直接陈述人与动物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而是借助一些颇富创意性和启发性的非虚构故事,来讲述各种动物的生平与轶事,并将史料、神话、新闻与个人的想象力融为一体,将动物的生命轨迹与人类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相互参照,来探究人类曾经如何看待动物、如何对待动物,生物学上的动物如何与人类想象中的动物交织在一起,从而提醒人类,究竟应该与动物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早在人类刚刚成其为人类时,他们就必须熟悉身边的每一种动物,熟悉狮子的脖子、老虎的牙齿、野牛的脊背,以及马的侧腹的每一寸肌肉……以便他们随时获得食物,且及时逃离险境,这既是生存的需要,又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所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从伊始就呈现出一种既合作、又排斥,既依赖、又敌视的倾向。曾几何时,人类和动物在一个相互平行的轨道上生活着,渐而人类以其特有的智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即便如此,动物依然占据着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宗教的,日常的,还是生物的,神话的。动物“被驯化又被崇拜,被喂养又被宰杀”,它们被人类赋予某种精神性的力量,进而在人类艺术史上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诸如帕萨雷洛笔下的椋鸟之于莫扎特;诸如一战时期一只受伤的信鸽之于法国七十七师步兵团的战士——一只飞出战壕的信鸽,即是一面象征着可能性的旗帜,它让陷入绝境的战士心存希望,鼓励他们不放弃最后的机会。
近世以降,由于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种种事端的连锁反应,一直维系着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传统关系突然被打破了。动物不复是人类的生存伙伴,也不再是人类文化的“信使和承诺”,相反,动物转而成为人类追求巨额利润的工具,或者作为绝育的宠物、供人观赏的动物园里的生物乃至“商业传播的动物形象”而存在。正是在人类疯狂的捕杀下,1627年,最后一头欧洲野牛死于科塔罗丛林;1844年,最后一对大海雀死于大西洋北部的一座岛屿;1936年,最后一只袋狼在一次寒流中死于博马里斯动物园。
随着越来越多的动物的灭绝,人类突然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独,他们终于感受到了被大自然反噬的痛苦,并开始想念动物。人类试图弥补自己的过失,便用他们荒诞的力量从废墟中重建一些不真实的东西,且名之曰“逆灭绝”或“再野生”——不管以后取得怎样的效果,这既代表着人类标记动物生命的新方式,也意味着他们在改善人与动物的关系方面,终于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撰稿|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