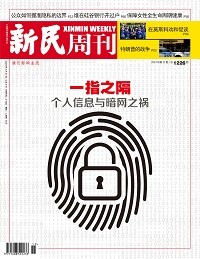当艺术家遭遇文学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文艺总会与酒相关,乃至成为一种文化。饮酒本身即成为一种隐喻:包括让开瓶器螺旋钻头钻入软木塞,在按下金属把手时,期待那瓶中的空气如被雨水拍击的瓦片般颤动,发出“嘭”的一声,桌面上会留下一些碎木屑,但饮者并不在意这些形而下的皮屑。被拴在你的味蕾上的酒,如同一支赋格曲,这时你可以尽可能缓慢一些,让酒的后调轻轻覆过前调,像随海浪而来的沙子缓缓蓄在了贝壳里。四重的物在这杯中交叠:葡萄被酿榨时,混合着甘甜的空气与阳光,混合着耕作者的劳绩与饮者的疲倦。那你该如何描述你的喉咙里蒸腾的酒精?它们是这酒的精魂。与其说它是液体,不如说它是固体,甚至是某生命体:会留下抓擦的生命体。如同一只透明的壁虎在你的喉咙里攀着,如果喝得太快,或者同时喝好几种酒,它们的尾巴就有可能会断在你的胃中,引发胃酸的反攻倒算。酒是你器官的显影液,原本埋在你厚重、阴暗的肉体下的舌头、喉咙、食管与胃,突然被一道光充满:仿佛子夜的居民楼突然亮起了灯盏。生活,作为行动的生活,在酒抵达你的血液时,苏醒了。
高瑀的小说集《醉酒艺术家》,用诙谐的方式,让我们进入一个充满迷幻色彩的酒与艺术的世界。如同他的艺术创作,他的文字也钟意消解看似坚固的历史以及价值体系。作为所谓“卡通一代”的代表,他用“熊猫GG”这个符号,不断地戏拟典故,让它扮演诸如诸葛亮之类的人物,却成为它所扮演的存在的失败复本。完成于2002年的《熊猫先生不是诸葛亮》中,即有一头借箭失败,被射成刺猬的熊猫。
小说集里的十二篇小说,围绕一个自称“醉酒艺术家”的主人公展开,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两者都是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实般摘除,用水冲洗,盐渍过后,供人观看与食用,他们的艺术也源于自身的某种匮乏:这匮乏有时是病理性的,正如饥饿艺术的根源是艺术家罹患厌食症的身体与观众同样厌食的心灵。而如果你展开这本书的书衣,在其背后你就能看到醉酒艺术家的形象:圆脸、小丑妆、肉钩般硕大而僵硬的手正托举着一只奖杯。醉酒艺术家作为一位“反英雄”出场,他在世界各地游走:四川、苏格兰、日本、塔希提,希望从其中寻找一种超越的艺术,但他碰到的,却是自己失败的情欲,如同艾略特笔下的普罗弗洛克般彷徨着。这些故事很少是单层的,主人公就像沉在海底被缓缓拖动的锚,他在游历过程中总能发现一些野史的碎屑与淤泥。有时,这些野史会与主人公的现实平行。在塔希提,高更过着近乎浪子的生活,而主人公却不敢向他倾慕的人诉说自己。在苏格兰,他被一位自称“德鲁伊”的人祝福,事后才发现,那人竟是一个流浪汉、小偷兼疯子。
正是从他的匮乏,高瑀连同其笔下的“醉酒艺术家”逐渐触摸到当代某种本质性的经验:艺术不再是抽象、原创的,它需要关切肉身与此刻,艺术也不再是纯然公共,或需要诉诸情感的存在。它未必是悲剧,而是荒诞剧,于是他的文本便会容纳如此多无厘头故事,以求让历史发生微妙的错位,就像酒让感官错位一样,也因此,高瑀的《醉酒艺术家》自愿成为一本轻快的书,不仅仅透过故事与笔法,亦透过艺术渗入其文字的方式。撰稿|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