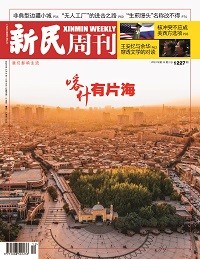中世纪身体的道德隐喻
中世纪总是被一系列刻板印象覆盖:漫长黑暗,悲惨无知,被视为某种过渡、停滞与混沌阶段。即便有人为此着迷,也多是以扭曲过去来满足“新哥特式与恐怖事物的浮夸品味”。英国艺术史教授杰克·哈特内尔的《中世纪的身体》,用器官叙事呈现中世纪生活史细节。身体不只是生存载体,还是调控系统,理解疾病死亡的路径。其强大隐喻功能,辐射了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各维度,是探讨总体性生活的起点。
如既有干苦力的脚,走远路的脚,也有无需劳动的脚。鞋子形制越无功用,越在揭示穿鞋者等级之高。如同魔爪的尖头长鞋,凸显穿鞋者出自享乐阶层。鞋帮做得很低,则为了展示亮眼的袜子。14世纪花里胡哨的“波兰鞋”风尚,被道德家们嘲讽粗俗无比,在15世纪又从尖头转变成平头。鞋和脚的关系,俨然成为道德观察,却形成相反相成的两极。鞋子越长表现对道德感的轻视,赤足则成为羞辱和悔罪手段。
作者发现仪式里身体要素的“两分法”:中世纪统治者既会要求吻脚,来表达尊崇效忠;同时也会进行另一种仪式表演:为穷人、乞丐和贫民洗脚。这种灵感效仿了基督为门徒洗脚的谦逊。赤足,一边是对囚徒的惩罚,另一边又被赋予灵魂的苦修。“毕竟,基督是自己背着十字架赤足走到骷髅地的,还有许多圣洁的典范,长久以来把不穿鞋等同于抛弃物质享受,追求神圣真理。”
这种符号价值的暧昧性,也在有关身体的性特征上呈现出来。在我看来,它体现为显与隐的悖反。一方面,中世纪的宗教传统把与性有关的身体器官,转化为“去性征化”的公共展示,“成为兄弟情谊的象征或神圣崇拜的对象”。另一面却有意隐匿与男性情欲有关的事物,不让大众觉察。
中世纪的医学观念善用隐喻解释两性身体,生命孕育。如男性和女性器官有互为镜像、分属内外的相似性。男性主导的生育观,将女性视为容器,盛放男性种子。有意味的是,男女体液最终都被视为血液的变体,这种加工转化通过加热、调配和压缩实现。“母乳被认为是用母亲的血液在乳房里调制出来的,这种血液也曾经滋养子宫里的胎儿。”
“第二性”观念也并非一个晚近发明。中世纪自然地表述了性别不平等——一种原生与次生,成熟与未成熟,完善与欠缺的两性观。这些源于一种体液说,它曾居于解剖知识的核心地位。“男性才是人类真正的典范”,男性的大量体热奠定了身体魁梧,毛发茂密,可通过大量体液使身体多余能量轻易耗散。而女性身体则被描述为其反面或不足——它寒冷得多,某些程度上类同于孩子身体,不如成熟男性的火热身体。“这种次等的身体因为太过寒冷而无法通过汗液或混合液排出体液,唯一的选项是通过月经清除过多的淤积。”
这种逻辑会自然推导出女性特质:身体娇小,皮肤光滑,也更脆弱。中世纪的思想家将此类身体学说,直接转化为厌女的道德观。女性的体液状态,直接变成心灵分析和道德判断的依据。如根据经血判断其是否贞洁,反复无常;要么拥有好记性,抑或头脑呆滞。这种拙劣的论述工具,与宗教裁判巫术妖魔,同属一个思维世界。“从许多方面来说,中世纪都算得上是令人深深担忧的时代,只凭借解剖学构造,就几乎把一半的人口划分成较低等的人类。”而看似荒谬和恶心的观念,置于历史语境中,恰恰是主体富于逻辑的自我解释学,是另一套身体的想象。撰稿|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