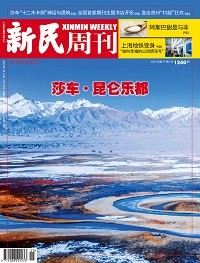也说“审丑”
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丑与荒诞,是为审美的六种类型。把“丑与荒诞”列入审美,还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兴起而形成的理论突变。1853年,罗森克兰出版《丑的美学》,系第一部论述丑的美学著作。书中首度提出丑与美一样,同属美学理论范畴,但在表现丑时,必须使之服从于美的法则。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乏对于美丑的认识,且充满深邃的辩证思维。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到:“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尤其最后一句,表明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某种条件下,比如以丑作为反衬时才凸显为美。刘安在《淮南子》中又深了一层:“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不求丑则有丑矣。”按我的理解,是指美丑在对立中的共存关系,或曰不可分割性。中国画中常见一种画法:以一块丑石作为墨竹的陪衬,则益显峻拔之气。若画成美石不是不可,其筋骨气韵、主次对比、意境营造则呈两相削减、喧宾夺主之势。擅长画竹的郑板桥就说过:“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郑板桥集》)。
这就要说到审丑的第二层含义,即美学意义上的“丑”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陪衬功能上,还在于它往往比流行意义上的“美”,更具深刻的内涵和艺术表现力。比如八大山人或一爪独立或翻着白眼或三翎尾翼的墨鸟,形态近丑而非美,笔触极简而不事琐细,但它的意态、神态和形态所流露出的,是笔墨的深度和笔性的高超。所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只因无处可诉说,那样的“丑鸟”岂是“莺歌燕舞”和匠缚之技所可比拟的?罗丹1891年为已故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塑像,他一口气制作了多尊皆不满意,却一时找不出问题的症结。某日他的学生布尔德尔登门拜访,罗丹征求他对作品的意见,布尔德尔却一下子被精致逼真的手部吸引住了,久久加以凝视且赞叹不已。罗丹这才恍然大悟,遂毫不足惜地用锤子砸去了这只手。因为在罗丹看来,巴尔扎克的精神特质才是最需要表达的,手部过于生动反而冲淡了作品的整体性,也转移了欣赏者的注意力。目下所见整件作品虽显得有点“丑”,但巴尔扎克的“骄傲、自大、狂喜和陶醉”(里尔克语)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成为雕塑史上一件运用“减法”而垂世的杰作。由此可以看出,艺术作品的美与丑,并不取决于表现对象本身,而在于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美学认知层次。
正如前文所说,丑的表现必须以服从美为准则,或曰极则。应该指出,在当代书法、诗歌、抽象艺术等创作领域,那种搞怪耍宝、自以为是的“作品”还是大量存在的。同时,与这样的“丑”相比,很多的俗美、流行美和心灵鸡汤式的鲜美,体现出一种十分浅层的认知向度,极大地混淆、拉低了受众的审美品味。这两种现象,前者可谓“以丑为美”;后者实属“表美实丑”。所以对美的认识深化不可或缺,拿德国学者鲍姆佳的话说:“丑的事物,单就它本身来说,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较美的事物也可以用一种丑的方式去想”(《美学》)。这让我想起赵孟和董其昌的书法,美不美?当然美!但很多爱好者常年临赵字,临着临着就临成了俗美而丑;临董字呢?越临越笔无骨力,浮薄孱弱。临画也如此,有些人取法不出明清,八大、石涛、髡残常挂在嘴边,但笔下的临摹却难取其神,以至徒具皮相,说到底这还是认识和表现的问题,又岂能怪罪以上所列大师诸公?撰稿|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