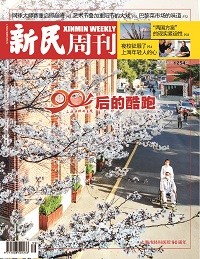用童趣的执念对抗时间
前几年经常看见新闻说,年轻人家里堆满玩具,不是真的喜欢,而是意在补偿小时候没能满足的遗憾云云。牵涉童年的问题,好像总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韦斯·安德森是我所知童趣感最鲜明的一位导演,对他作品的批评就有点像对童年问题的分析,呈现两极化的趋势——爱他的说他天真烂漫,骂他的说他不思进取。短片《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承续这位导演的既往风格,专注于对形式化的高度追求,并且不管不顾地几乎掏空了内容。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习惯上,中国人更加愿意表达对内容的看重,而羞于表彰形式的价值。曹丕说“诗赋欲丽”,尚且没什么争论;到了萧纲说“文章且须放荡”,舆论就颇不以为然了。先贤的教诲说,绮丽不足珍,花哨往往意味着浅薄。就像中秋前后那些包装华丽到“配享太庙”程度的月饼,终归引人侧目。一样东西的形式如果非常惹眼,我们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对内容产生怀疑。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就难以鼓吹。个人风格强烈张扬如张爱玲,也要表明自己对只拥有图案美的作品不感兴趣。但图案美,到底也是美的。也许正是因为美的价值一望即知,简便易得,反而变得轻贱起来。
《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是个挺文学化的作品。影片通过讲述者视角的转变和递进,将情节和场景像套盒一样一层层向深处打开,从《萨拉戈萨手稿》到《高堡奇人》《苏菲的世界》,这一直是小说惯用的手法。影片用了特别稚拙的方法打破“第四堵墙”:让角色对着观众说话,关键道具的设置充满玩具感,连戏剧舞台上常见的“捡场”工作人员也不时出镜。布景如同木偶戏一样转换,呈现出的效果就像看着导演摆弄一座粉妆玉琢的娃娃屋,把角色像屋子里的人偶一样摆到这里、放到那里。被讲述的故事,存在感非常低,甚至人物性格也非常微弱,重要的是表演本身。这正是旧戏所追求的舞台效果:美人唱了,笑了,袖子遮住了口,一出戏的意义就在她的颦笑之中。只不过韦斯·安德森的故事更单纯,人物举手投足间没有深深的人生况味,取而代之的是儿童感十足的无邪和无情。
不是强迫症,但是我挺喜欢韦斯·安德森。他对称的构图和浅景深的设计,迷人的野兽派画作一样的设色,总是带着一种蜡笔画质感的图案美。他凭借孩童一般的执拗,硬生生把形式的表现力拉到和内容平齐甚至超过内容的地步。他导演的作品里我最喜欢《月升王国》,一方面局促狭窄,一方面活力四射,就像一个拧巴的孩子,奇奇怪怪又含情脉脉。新作找回了一些《月升王国》的气质,不同于他近年来有些疲弱的新片《小行星城》和《法兰西特派》,作为一部短片,反而更加丰盈活泼。这也许难免被讥诮是一种韵高才短和故步自封,因为驾驭不了电影的长度,只能回落到小品上来。然而电影毕竟不像假期一样越长越好,长篇和短制,正如西瓜和樱桃风味各异。
罗大佑的歌里唱,由你出生当天起,童稚已每天在远离。想到这一点,再迟钝的成人也难免心生怅惘。对童趣的执念仿佛是一种对时间的对抗。而看这部短片,就像看着孩子趴在地上搭积木,如果能放弃高高在上的成见,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那个尘土飞扬的奇妙小宇宙里,自有它颠扑不破的秩序和美丽。撰稿|薄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