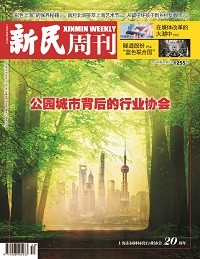不一样的民国学术界
1918年5月,周树人首次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白话与文言,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在决裂的分途义无反顾。此时,二十四岁的桥川时雄以记者的身份,从日本辗转大连来到北京,一边在“新派”与“国故派”势同水火的北大旁听课程,一边潜心于他所钟爱的陶渊明研究。
亦旧亦新的时代,思潮、主义、学派,各擅胜场,桥川时雄并不以新旧为界,记录下一个日本人眼中民国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民国时期的学术界》收录了桥川时雄有关中国学人的报刊文章以及报告书。透过桥川时雄的眼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民国学术界。
1922年桥川以日文翻译出版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次年又翻译出版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为他的译本写过一篇序言。上述二书的着眼点一旧一新,在不同维度上对时代思潮作出回应,选择翻译这两部新近著作可见桥川对学术动向的敏锐捕捉。彼时的桥川在北京的学术界虽属初出茅庐,但颇为活跃。桥川在北京结交了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众多人物,既有辜鸿铭、陈宝琛、柯劭忞、王国维、傅增湘这样的旧学宿儒,也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化大将。文学革命,国故整理,考古发现,教育动态,都是桥川的兴趣所在。桥川细致而率直的观察记录,从他者的角度,勾勒了民国学术界的第一现场。
桥川在中国近乎活动家,然而他视为志业的始终是中国古典的研究,是传统的学问,是《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中反复提到的“旧学”“国学”。桥川在中国最重要的事迹,是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围绕编纂《提要》的工作,桥川对中国学界的观察自然偏重于传统学术。桥川积极物色旧学人物的行为看似逆流,他的记录呈现出与新文化派主流叙述不同的另类视角。
在桥川主持编纂《提要》之前,参编者还只局限于数位前清遗老。当时国学界的局面,用胡适的话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国学季刊》发刊词,1923年)。即便如此,桥川仍然试图以走访、通信等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发掘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南方一批沉潜旧学的老辈学人。在他的组织下,《提要》的参编者从京津地区学者,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的学者,一时间国学耆宿汇聚大半。桥川对南方老辈学人的寻访经过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开篇收录的报告书中。桥川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随着《提要》编纂工作的深入,他从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爱好者日渐成长为一位汉学家。桥川对民国学人的观察记录,也倒映着他自己的学术蜕变。
与桥川倾力联络旧学人物编纂《提要》形成对照的是,他很清醒地知道“旧派已见孤城落日是必然之事”,桥川以其一贯的冷峻尽可能全面地描述着中国学界的斗转星移。主持《提要》的编纂工作最终因日本的战败而移交国民政府教育部,桥川回到日本后作为大学教授继续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仍然保有中国旧学的流风余韵。撰稿|徐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