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建交的“传言人”和“见证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32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仅仅几十个小时后,苏联和中国先后宣布与对方建交,并互派尼古拉·罗申和王稼祥担任驻对方国家首任大使。
这其中,一位名叫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季赫文斯基的苏联外交官不仅在10月1日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开国大典,还有幸成为中苏两国建交的幕后“传言人”和“见证者”,并在此后几十年时间内为中苏、中俄友好关系做出许多贡献。直到不久前,季赫文斯基生前完整版的回忆录《重返天安门》才问世,里面如数家珍般回顾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令今天的我们面对七十年前的往事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唯一的官方代表

许多时候,档案记载与后人的习惯印象是有出入的。开国大典进行时,贵宾云集的天安门城楼上,外国人只占极少数,像历史纪录片《中国的重生》里确实出现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等名人的身影,可他们只是作为苏联民文化代表团成员出席,真正的外国官方代表仅有一位,那就是季赫文斯基。微妙的是,他名义上还是苏联派驻中华民国政府的北平(当时刚刚改称北京)总领事而已,因为当时中苏双方并未正式建交。就在庆典结束后数小时,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派助手来到苏联总领馆,给季赫文斯基送来一封急信,内容是要求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
在《重返天安门》里,季赫文斯基详述了这一重大历史细节:“我迅速将其译成俄文,然后与译电员一起将电报发给莫斯科,发完后还小酌了一杯酒,之后我便与妻子前去参加人民政府的招待会。第二天早晨,值班的管理主任来敲我的卧室门。我对他说:‘听着,让我再睡一会儿!’他说:‘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刚才收听莫斯科的广播,因为杂音太大,我什么也没听清,但清清楚楚听到您的名字!’原来,因为时差的原因,我拍发的电报恰好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他当即下令在中央媒体上进行公布。就这样,苏联于10月2日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式与苏联建交,季赫文斯基无意中成为中苏建交的“传言人”。
中苏建交后,直接面临的技术课题是谁来担任对方国家的首任大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苏联政府决定选择在中国呆了六年多并一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季赫文斯基对这位老上级很熟悉,后者是从苏联红军半路出家的外交家,1939年完成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系的进修后就派到重庆,担任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武官助理,1941年任代理武官,1942-1948年升职并担任武官,1944年才回国参加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东普鲁士的战斗。罗申汉语流利,且熟悉中国情况,于是在1945年7月被紧急调回中国,1948年升任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1949年1月,国民党预感南京不保,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罗申奉命率馆员随国民党搬到广州,后来才只身回到莫斯科,这件事显然给即将全新开始的中苏关系带来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回忆。
身为当事人,季赫文斯基也没想到“当家的”(即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提名罗申“回炉”,他当初的想法是莫斯科将派遣与国民党没一点瓜葛的资深外交官。面对莫斯科发来的指示,季赫文斯基带着满脑子的疑惑,立即拜见周恩来,就新驻华大使人选征询中方的意见。几十年后,季赫文斯基清晰地记得:“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一会,他本人去了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过了15分钟,他回来告诉我说,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提出的大使人选。”就这样,罗申从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变成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
兴奋异常的季赫文斯基马上向国内汇报,苏联政府于10月4日宣布罗申从莫斯科启程,他一路紧赶慢赶,变换好几种交通工具,先是坐飞机到赤塔,后换乘火车来到靠近中国的苏联外贝加尔边疆区,7日上午10时,罗申抵达苏中边境小站奥特波尔(今外贝加尔斯克),几小时后开过中国口岸满洲里,8日傍晚6时到达哈尔滨,9日深夜零时从哈尔滨出发前往沈阳,当天下午5时从沈阳继续前行。10日下午4时18分,专列经天津抵达北京前门车站,罗申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欢迎接待的外国大使。此时,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等候多时,准备给这位大使致以最高规格接待。
纪录片《中国的重生》完整展现了欢迎场面:罗申下车后,军乐队奏响中苏两国国歌,罗申和周恩来先后致词,随后周恩来陪同罗申步出车站,季赫文斯基紧跟在后面,他们受到车站广场上三千多名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按照国际惯例,大使到达,一般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代表到机场或车站出面迎接即可,但罗申却由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亲自迎接,难怪苏联外交部一位副司长曾对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戈宝权说,中方“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等于迎接外国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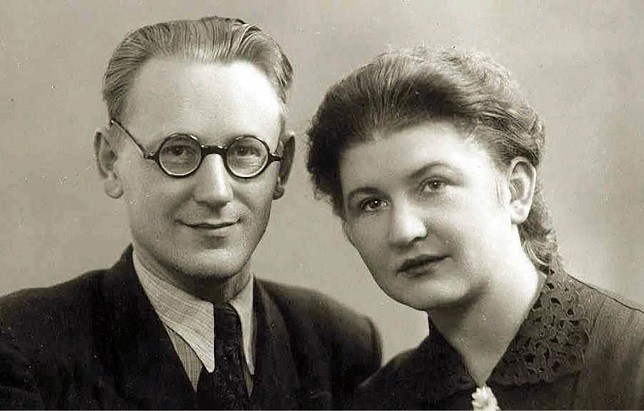
“全新的命运”
可贵的是,季赫文斯基对中国的描述并非停留在官方层面,而是涵盖新旧时代交替的时间段,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1945年9月,日本投降。翌年5月初,曾跟随国民政府呆在重庆八年之久的苏联大使馆回到南京,但苏联驻华外交官面临的新任务是密切关注中国国内时局发展,当时国民党磨刀霍霍,企图消灭共产党,而内战的爆燃点就集中在与苏联接壤的中国北方。鉴于形势需要,1946年1月,莫斯科决定在北平设立使馆代表处,7月升为总领事馆,位于市中心的东交民巷,用的正好是自1861年以来俄国使团住过的老宅。早已在罗申手下脱颖而出的季赫文斯基,当仁不让地成为苏联在华北的外交负责人。
解放战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得到人民支持的共产党军队以东北根据地为起点,迅速席卷南下,特别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瓦解已指日可待了。“1948年底,华北的解放军就兵临北平城下,一度切断北平与天津的交通线达四十多天,城里人心惶惶。”季赫文斯基回忆,守城的国民党军到处张贴反共标语,发誓死战到底,可这种口号却掩盖不了大肆掠夺百姓的“集体暴行”,“当时俄国人在北平办有两家乳品厂,一家属于俄国东正教会,另一家属于苏联国有财产,但国民党兵抢了他们的鲜奶和喂奶牛的草料,我不得不出面与他们争论,但毫无结果。很快,国民党军人和官吏开始大量逃离北平,他们还把整条林荫道上的树木伐光,以便抢建飞机场,供更多的飞机着陆”。
这种混乱局面延续到1949年初冬解放军进城,新的人民政权开始筹建。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况且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给予中国人民有力的支持,因此苏联外交人员受到优待,尤其能接触到解放区最新和最真实的信息。季赫文斯基去迎接来京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坐的是火车,而从长辛店到前门火车站的一路上,有不少故事让他动容。在长辛店机车厂,他们得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工人们就从工厂里转移走工具、车辆零件甚至整个车床,然后分别藏好,一直保存到人民政府需要的时候。“津浦铁路上性能最好的一台蒸汽机车头就曾被埋在地下十多年。几十辆乃至数百辆汽车就这样从企业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位参加过护厂斗争的老工人告诉苏联客人,“当解放军向北平(国民党时期的称呼)挺进,国民党极尽所能地焚烧并摧毁一切的时候,许多车辆被我们用这种方式抢救下来。”工人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工作积极性和能量,帮助人民政府把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起来,老工人说:“这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帮助它!”
解放军进城后,铁路水塔无水可用,水泵停转,蒸汽机车无法加水。但几个小时后,水塔就开始运转,铁路枢纽全力满足解放军的需要。所有人都明白,如果能够提高知识水平,就能为属于自己的国家做更大贡献。为此,工厂、百货商店甚至个体作坊都开设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政治和技术夜校,大家充满热情地学习知识和文化,学生中还有一些五六十岁的市民,但他们并没有掉队,而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从前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掌握的一切东西。季赫文斯基体会到,北京到处是新中国第一代的高涨热情,常能听到年轻人在工厂和作坊里高唱激昂的革命歌曲,他告诉苏联著名摄影记者米科沙:“仅仅在一年前,你能见到的人全都是一副阴沉而疲惫的面孔,整个北平的情绪是灰色的。”
和普通人一样,季赫文斯基非常喜欢游览参观美丽的建筑,尤其当这种“静默的语言”同解放的社会一道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季赫文斯基曾陪同苏联代表团登上市中心附近的景山(旧称煤山),整个北京城的景色可谓尽收眼底,正前方是紫禁城,可以看见昔日皇家宫殿的黄色瓦房盖、高达15米的坚固城墙、灌满水的护城河和镶嵌块块石板的惯常。“以前,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封建帝王的宫殿看起来让人感觉阴森森的。”苏联人细腻地捕捉了紫禁城角楼、城墙和护城河的细节,这里曾是财富和精致建筑艺术的象征,可是在国内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者占领期间曾经遭受过洗劫,现在却是中国人民高度文明的纪念碑,那些精致无比的大理石和木雕作品令人叹为观止。季赫文斯基曾向同胞们介绍,紫禁城南面绿荫掩映之下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不久前还是在华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象征,“它由一道高墙与城市其他部分隔开,实际上那里不属于中国,而是享有法外治权的地方,其历史源起于义和团起义,当时人民忍无可忍,满腔怒火喷向帝国主义压迫者,在起义被镇压后,帝国主义决心在中国心脏处埋下钢钉,企图永远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
顺带提一下,新的中苏关系也给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带来“全新的命运”。10月20日,被滞留在广州的原苏联驻国统区外交人员历经飞机航班取消、轮船抛锚等变故,终于来到北京,加入罗申领导的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弗拉基米尔·瓦西科夫当着季赫文斯基的面,郑重向罗申大使报告: “请允许我汇报!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已经成功完成了苏联政府下达的任务,返回常驻地北京。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在新中国成立头两个月里,苏联就派出援华专家三百多名,几个月后就增至数千名,他们大都住在与大使馆仅一街之隔的国际饭店,每周六和周日那里都会举办盛大的舞会,邀请苏联外交官及夫人参加,专家们也是大使馆的常客,大家一起比赛象棋、打排球。排球场与英国驻华使馆仅一墙之隔,一不留神,球就飞到对方院里,按理说只能向对方礼宾官索要,但苏联人经常“奋不顾身”地翻墙拣球,公然“藐视”大英帝国的“领土完整”。苏联使馆人丁兴旺,多亏了当时管理食堂的苏联侨民罗曼诺夫斯基,他是个精明干练的商人,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罗申善于交际,来北京不久,他就跟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的维克托神父交上朋友,传道团有自己的养牛场、养蜂场、菜地和果园,使馆的奶制品以及其他食材就购自那里。闲暇时,家属们经常光顾附近一家名为普希金的商店,与其说是购物,不如说是想跟俄罗斯售货员拉拉家常。
季赫文斯基强调,新的苏中关系完美地拉开帷幕,那是一种真诚的、令人振奋的、世代皆兄弟的友谊。

真诚的友华派
聚焦到季赫文斯基本人,他的故事同样令人称奇。1918年9月1日,季赫文斯基出生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父亲是个医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全家人曾想过出走芬兰,但对家乡的眷恋使他们留下来。上世纪30年代中期,季赫文斯基从大彼特里舒列的第41中学(九年制)毕业,后考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1938年从该校五年级被共青团选派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后为外交部)工作,直到1957年6月。据同事回忆,季赫文斯基拥有亲近而又富有建设性的谈判者形象,懂得与人建立友好关系,每每谈及苏联与别国复杂的关系时,季赫文斯基总是说:“我寄希望于那些务实和理智的人,而这些人在各个国家还是很多的。”
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季赫文斯基的地位不容小觑。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来莫斯科访问,见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苏联高级领导人,全部会谈的翻译正是季赫文斯基。正是这次出色表现,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注意到这个小伙子,让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去中国迪化(今乌鲁木齐)的苏联总领馆当副领事,处理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善解人意的莫洛托夫考虑到季赫文斯基的前程,两年后特许他赶回莫斯科,以走读生的身份从东方学院中文系毕业。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季赫文斯基承担了繁重的外事任务,接待大批同盟国使团,较重要的是1943年陪同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利访问斯大林格勒前线,还参加过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苏联代表团秘书处的工作。1943年,季赫文斯基重操旧业,经新疆来到重庆,当上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二秘。1946-1949年任苏联在华北的外交代表,负责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事务。1949-1950年,季赫文斯基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罗申到任前还兼任了几天的临时代办)。1968-1974年,他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苏联委员。
季赫文斯基不仅知华,而且是真诚的友华派。1949年底,毛主席首次出访莫斯科,还参加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庆祝,季赫文斯基亲自陪同毛主席抵达中苏边境,中国代表团要在那里换乘苏联列车。“我走进他的包厢问:‘我可以为您拍照吗?’毛主席回答道:‘请!’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照片。毫无疑问,毛是个杰出人物,真正的领袖。他出身平民,靠实践获得真知灼见。正如中国人常说的,他土生土长,自学成长。”在92岁高龄时,季赫文斯基向俄罗斯《消息报》透露那段属于个人的往事:“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做得非常明智,他们坚持基本制度,但同时调动了个人积极性。中国人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前进。我认为,这个体制非常灵活。”
中国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99年10月1日,季赫文斯基再次受邀来华,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活动。2008年9月28日,时任中国总理访俄期间,在宾馆会见俄罗斯各界友好人士,时任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俄科学院院士季赫文斯基应邀参加会见。他在发言中强调,中国正在继承并弘扬发源于周恩来总理时代的民间外交传统,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势头非常好,一大例证是俄中友好协会积极参与的双方国家年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两国建交六十周年和中俄友好协会成立六十周年,两国分别在对方国家举办语言年,季赫文斯基衷心祝愿中俄友好组织今后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会见后不久,季赫文斯基应邀来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故地重游了他阔别了数年之久的北京。
可惜的是,2018年2月24日,季赫文斯基在莫斯科溘然辞世,享年百岁。但历史已然证明,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中俄确实互为伟大邻邦,彼此合作,并肩前行,被赋予更广泛内涵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