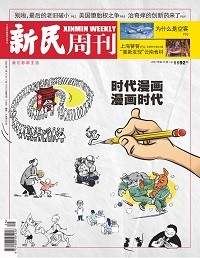让更多人喜欢越剧
专访茅威涛、郭小男
茅威涛与郭小男,这么多年来既是恩爱夫妻,更是黄金搭档。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小男提出“重塑茅威涛”这一大胆设想,使得茅威涛,乃至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下子从《五女拜寿》、《西厢记》、《陆游与唐婉》这些早已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中走了出来,杀出一条血路,为越剧在新世纪的传承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展示,无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独家艺见:最近,你们二位合作了新戏《江南好人》,将越剧与布莱希特相结合。显而易见,郭导是想通过实验达到一种突围,从而给越剧乃至戏曲带来更多可能性。但是每种艺术样式的存在会有它习惯生存的土壤,不断的颠覆和革新会不会使它的本质支离破碎?这出戏里,你坚持的属于越剧的部分是什么?
郭小男:茅威涛等于越剧,我想颠覆也没那么大本事。
茅威涛:郭导就一才俊,哲人。但本人是一个会把导演逼到墙角的演员,哈哈。所以大家往往可以在排练场上看到的,就是两个“唯美主义者”对掐,最后实现辩证统一。
独家艺见:郭导对未来越剧的定义是什么?或者说您认为未来越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郭小男:适应时代,坚守与变化并举。最大程度地被审美者接受。
独家艺见:有些观点认为越剧就应该坚持儿女情长,在其他领域内的拓展都无法将艺术性和可看性结合得很好。在郭导看来,排演上一世纪的布莱希特,能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可看性的兼顾么?
郭小男:让思考、愉悦、摩登结合,观众各取所需。不仅是越剧,所有的艺术无不如此。
茅威涛:的确,我一直提倡,舞台艺术最高的境界,是带给观众:一、欣赏的愉悦,二、思考的愉悦。
独家艺见:作为导演,您觉得《江南好人》最令您满意的、突破性最大的、最与众不同的是什么?
郭小男:最满意的是用了半年的心血,让小百花完成这样一次转变。这一转变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它有了从古典到现代转变的技术可能性,从而可以面对未来的越剧了。
独家艺见:目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您二位的美学观点是对1942年以来以叙事本体主义为核心的新越剧改革运动的突破,因此可将之称为“新古典主义”。在纪念越剧改革70周年的今天,现状并不乐观,然而浙江小百花这些年来的勇往直前,带动了一大批青年观众对于越剧的喜爱。但同时,不少老观众的不理解,甚至谩骂,也始终伴随茅威涛的左右。
茅威涛:很多年前我来上海演出,一个观众天天在后台门口骂我。人家问他你既然那么讨厌,可以选择不看啊!他的回答很绝:“骂归骂,看还是要看的。”我想,我欢迎严肃的艺术评论,“猫咪”(粉丝)亦如是。但对于“黑”,泰然处之,大不济,也可以“拉黑”嘛,哈哈。
郭小男:戏剧的转型依靠众多姊妹艺术的帮衬,这本身就是丰富和学习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嫁接的过程中不出现矛盾,找到平衡点,让剧场接受。而创作,就是在担心观众能否接受和不担心之中找到平衡。
茅威涛:正像郭导提出的——“旧中有新,新中有根”。
实际上中国戏曲确确实实面临着对今天观众能否更大限度地去突围的课题,中国有300多个戏曲剧种,但是今天可能还存活的、在演出的不到100个,而且地方剧种都是源于地方的文化和方言产生,从本地方走出这个地域,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那是寥寥无几。可能越剧是一个特例,因为越剧是在上海开始繁盛起来,上海是一个新文化的大都市。
我想,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放弃老观众,我只是想有更多今天从来不知道越剧的、没有走进过剧场的观众,他们能够喜欢越剧,喜欢我们现代的戏剧。最近在大学开讲座时,有同学问我信仰是什么,我回答,越剧是我的宗教,舞台是我的佛门。
【请注意:新民周刊所有图文报道皆为周刊社版权所有,任何未经许可的转载或复制都属非法,新民周刊社保留诉讼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