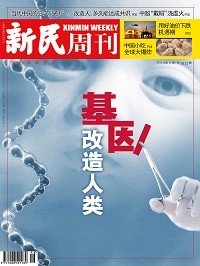谁是越剧的角儿
纪念越剧改革70年
戏曲角儿与院团的关系,的确是相当微妙的,既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
主持人|王悦阳(记者)
嘉宾|李莉(上海越剧院院长)
钱惠丽(上海越剧院副院长)
方亚芬(上海越剧院一团团长)
黄德君(上海越剧院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盛舒扬(上海越剧院二团青年演员)
齐春雷(上海越剧院一团青年演员)
李旭丹(上海越剧院二团青年演员)
朱洋(上海越剧院一团青年演员)
作为纪念越剧改革70周年的重头戏——“上海的声音”系列活动在前不久成功举办了,虽然今天戏曲并不景气,活动依然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出人与出戏
主持人:从越剧改革70年的历史来看,人才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戏曲人才的培养有其自身的规律,所以在越剧改革70周年之际,我们联合了上海市文联与戏剧家协会,想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这对当下和今后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李莉:青年演员的培养和传承,是我们院特别重视的。我想,上海越剧院在全国的最大优势是群体性。上海13个越剧流派的保持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比较严谨地在传承,而其他兄弟院团独挑大梁、比较拔尖的人多,群体性人才少。上海越剧院是属于群体性的,目前钱惠丽、单仰萍、方亚芬等人是一群,相应的下面的青年群体在经过培养后也是一批,目前她们在全国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比如盛舒扬、杨婷娜等等这些人。我们从自己院里举办的“小蝶杯”开始,随后是“越苑青春风”,历时将近一年;再到影响巨大的“越女争锋”,借助了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平台,又做了深度打造,历时半年。可以说,越剧院在这方面是相当努力的。
我们从2010年的演出开始,青年演员占了70%,这样一来明星演员不乐意了,有的艺术家甚至一年只演了6场戏。所以我们2012年就又调整了,把比例改为4:6,青年演员占60%。实际上对于院方来讲,明星演员场次虽然少,但是经济效益肯定高过青年演员,因此是有损失的。比如2012年我们就排了全明星版的《孟丽君》,把10个一级演员投上去了,当时我们的投资是将近40万,14场,经济效益已经过百万,而对青年演员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剧院之所以定下4:6的规定,是为了让青年尽快适应舞台,摸爬滚打,锻炼出来。
主持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越剧院长期坚持“共同繁荣”的局面,这本身对剧种、对剧院而言,有着一定的好处,无论缺了谁,都可以照常运转。然而,事物发展总是两方面的,在“一锅粥”的情况下,也难免会碰到僧多粥少的尴尬。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旦难以培养领军人才,那就无法占领艺术高地,李院长对此有何看法?
李莉:目前院里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原创剧目缺乏,我们的计划是一年排两部新戏。但我院有两个团,人才又多,轮到角儿排一部新戏可能要等10年。所以我们有个硬性的规定,首先,你想上新剧目,要得到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只有文化发展基金会立项之后,剧院才让你上演。这样就能省出很多钱来排两个戏。但排两个戏,对于剧院来说还是僧多粥少。比如群戏,对于明星来说,他们更喜欢只有两三个人突出,群戏不合适;对青年来说,传承当然重要,但群戏对于他们体验新的角色塑造来讲,就很弱化。
实际上,我们给青年演员排戏的机会还是很多的,这两年新的原创剧目都用在青年演员身上了,而换来的很有可能是意见一大堆。但我一直认为,剧院将来是需要接班的,那就需要青年。中生代演员即使能撑大局,再撑个三五年而已,如果青年还是上不来,那有什么用呢?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青年群体中找到拔尖人才?因为尽管有优秀的群体在这儿,但总要有那么几个有影响力的人存在。然而,这里面又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剧院里是希望推角儿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有影响力的角儿的话,对于剧院今后走向市场是有好处的。但这个角儿的要求是必须站在台上能让人眼前一亮,而我们现在的青年演员或者是扮相很好,或者是唱得很好,但总体上还不到那个范儿。作为领导,当然有扶持和培养的责任,但是实际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困难的选择。我曾经试过,连续两年到三年,就推两到三个人,给她们每年排一部新戏。但团里第一个就过不去,每年给这几个人排新戏,那其他人干什么去,不是要有意见了吗?实际上,作为一个剧团,想要打造拔尖人才的话,势必要面临分崩离析的状况。有的人经过专家的分析可能有潜力,但是经过几年的磨练,可能他不一定真有这个才能,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必须要有整个团队一致的看法,一致的要求和一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所以难度比较大。
艺术与艺德
主持人:戏曲角儿与院团的关系,的确是相当微妙的,既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成功的例子不少,同时令人遗憾、一拍两散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总的来讲,艺术家是需要组织去关心、爱护的,可同时,艺术家也要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彼此互相促进,才能提高剧种的艺术性和生命力。
李莉:有一次戏曲中心开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就提了个建议,建议戏曲中心在整体高度的平台上,组织一些专家,来看看那些青年的潜力,给青年团队组织一些集训——我是指艺术上的集训,艺德的集训。我深有体会,现在的演员,当在被扶持的时候,是积极配合的,可一旦扶持到位了,就不管了。对此,上海京剧院的孙重亮院长就总结道:“当演员还没有到达艺术黄金期时,他们是艺德的黄金期;当他们到了艺术黄金期时,艺德黄金期就消失了。”
确实是这样,当演员成名后,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剧院服务,做贡献,赢得了多少票房,而不去想我们大家为把他扶到这个位置,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比如要开新闻发布会了,请他参加一下,他会说我很忙。我们最紧张的是说明书——排名、写介绍,后来有了经验教训之后我决定排三道线:先是团长审阅签字,之后副院长,再正院长签字。类似这样给剧院领导带来压力和耗费精力的事是相当多的。总体来说,我们的确应该为青年演员提供各种条件,把他们推上去,但是对于青年演员本人来讲,如何提高艺德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有哪一方面忽视了,我们就很难培养出全面的优秀的演员。有的演员为什么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上不去,就是差了一口气,差的就是人格修为,心胸狭小,对人物的塑造不可能深刻地去理解。
主持人:在您看来,目前在培养青年优秀人才的问题上,还有着哪些较难克服的因素?
李莉:很多人指责,上海越剧院的演员怎么不练功。对此,我们的确有难处,我们只能对演员说你们要坚持练。这个问题可能要怪领导不抓或不重视,但也是因为越剧院真的没有练功的地方。目前一大一小两个排练厅,两个团平常排戏都要协调。第二是因为没有时间练功。杭州有些剧院是有宿舍的,办公楼、排练厅、宿舍都在一起,很容易管理。但我们的演员有的住在市郊,工资也不是很高,很多都是打的过来,来回两个小时,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把一个月的工资用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集中练功,不得已,我们就提出了以排代练的方法。对于青年演员来讲,他们能做到多少,就在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了。
我分析了京昆这两年做得比较好的原因,每年央视都在为他们举办京昆比赛,这个给他们提供了很大动力,剧院也给他们提供地方排练,传承有绪。但对我们越剧演员来讲,困难重重,首先,入上海户籍就很难,我们院有的人考了5次都没有通过。在人才引进这方面,上海越剧院就不具备任何优势了。
坚守与困惑
主持人:李莉院长刚才讲的内容非常务实。关于青年演员的培养,我想请各位青年演员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谈一谈,你们来到院里以后,有哪些方面你们认为院里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又有哪些方面剧院仍需改进的呢?
盛舒扬:进院这些年来,我觉得我的成长比较迅速,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前一阶段经历了新编历史剧《李商隐》的排练,我就深刻觉得青年演员要体验或者学习到导演制的排戏,是一大课题。我们在排练时常常不知道这个舞台动作、舞台调度是出于什么原因,所以,就算我们演得再精致,但人物的内心还是空洞的。我们可能体验不到那么多,因为那是经过老师、导演精心设计的,并非我们自己的感悟。但是我们作为80后、90后,看到剧本,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只有通过消化分析,才能真正提高。
如何才能让演员被观众记住,在我看来就是要塑造人物,而并非是唱腔,并非是身段,因为这两个是每个演员都必须具备的,或许我们现在这两点还有不足,但我们会继续在历练中去寻求。而真正能够让我们成熟的,是塑造人物的能力。回想以前老师在创造出一个流派时,是根据一个人物创造出一种声腔,我们会学习这种声腔,对于它的起源,我们并不了解。我想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
其次希望得到领导帮助的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宝地,我们希望多观摩到一些好的演出,无论是戏曲、戏剧,国内、国外的,用观摩来提高我们的审美。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自己的剧种、流派,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都还不够,达不到好的水平。然而,现在很多好的演出票价都不便宜,我们的收入还达不到每场演出都能够自己掏钱去买票,如果院方、戏曲中心等能为青年演员提供票务上的方便,我们一定也会积极去观摩演出的。
主持人:虽然越剧改革已经走过了70年,但诚如袁雪芬晚年所提到的那样——原来越剧的很多优势,比如音、舞、美的完整性,现在对比于其他地方剧种,都早已荡然无存了。这话很有道理,现在戏曲、戏剧舞台雷同化趋势很严重。所有的音、舞、美都是以导演为中心,然后整合一套班子出来。高度雷同化的制作模式,削弱了剧种本身的艺术性,甚至在市场化的大潮中迷失自己。
还有一个很大的趋势是剧种特色的淡化,几乎都往话剧化的道路倾斜,话剧加唱原本是贬义词,如今却成了戏曲舞台的一大特色。比如这次越剧中生代演员新编剧目的汇演,明显白口多于唱腔,而好听的、朗朗上口、能为观众熟悉喜爱的唱腔更是少之又少。但事实上,唱腔才是剧种的特色啊!还有水袖的弱化,也失去了戏曲原应具有的功夫与美感。当然,这个问题也出现在新编京剧和新编昆曲中,几乎所有剧种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齐春雷:我觉得,今天所谈论的话题,其实是几代越剧人都曾经面对过的,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回想有一年,李院长让我们排了6台男女合演的戏,其中我参与了4台。排的时候感觉是任务,一定要完成,一共就花了两个月时间,又要排练又要记唱腔台词,给人一种填鸭式的感觉。但后来我感觉还是有提高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接受的过程。目前排练中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几乎没有导演制和审核制,青年演员完全靠录像学戏。
至于李院长提出的排练、选角他们很为难的问题,我们也能体谅。因为原先老先生他们的剧目能够成为保留剧目,不是今天排出了这个戏,明年就不再改,不是这样的,而是一辈子都在改,只要这个剧本是有底子的,就不断在改。经过不断的改动之后,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我自己也想得很清楚,我现在的艺术水平还不够高,新创剧目就不会扎实,所以,我就把经典的、有名的老戏拿出来再挖一挖,排一排。这样,就算我这一代男演员将来没有很辉煌的男女合演的作品,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存在过,后辈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如果再有下一代,他们还有一个参照物,如果男女合演的状态能在下一代达到辉煌,我也是很高兴的。
我想,我们这一代应该背负起的就是责任,责任一直在被考验,被敲打,因为随时随地都有欲望。越剧有很多经典的戏,比如《红楼梦》、《西厢记》、《祥林嫂》、《梁祝》,70年以来的耕耘留下了这样四部经典剧目,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啃老,如果别人还是只知道这四台戏,那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也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只是学习和传承,没有发展。
钱惠丽:越剧起源于浙江,兴盛于上海,但很多人认为现在越剧又回到浙江了,上海现在不是重镇了,浙江投入的力度的确很大。然而,反观我们这次纪念活动,哪个院团能排出这样辐射江浙沪的强大阵容?而我们做成了。全国又有哪个剧团能一次性演成这四台经典大戏,而且全部自己完成?
所以这次演出结束后大家开研讨会,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当时提了两点建议:全国越剧院团每年能不能像京剧十大院团那样开一次院团长论坛,反映大家的创作、意见、需求,同时加强交流合作;第二个就是,每几年在上海举行一次越剧博览会,把大家在这几年中积累的新创剧目的探索和经验,分类型地集中进行半个月或一个月的展演。因为每个院团每年也都是在演出的,零打碎敲不成气候,但把它们集中展示后容易做成一个事件,这件事需要有人做。这样的汇演,每个人都较着劲,实际上是一种良性竞争。
齐春雷:我们比不得老前辈,我们展示的机会很少。我们的台柱子在台上要有光彩的话,不在台上站久了,是绝对出不来的。
李莉:对的,这个我知道。上次我蛮伤心的有件事,一位中生代名演员化好妆站在台后,紧张得不得了,手都冰凉,她和我说,我好久没唱戏了。我看她腿都在发软,因为太久没唱戏了,所以缺少了一种舞台上的自信。第二件事就是一团新排的《新拜月记》,我去后台,主演徐标新穿了一身新衣服,在我面前转了一圈,问我“灵吗?”他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这是第一次从头到脚为他做新戏服。以前都是演老的戏,所以他都是穿老戏服。再比如说到我们现在的顶梁台柱单仰萍,上次座谈时也是眼泪汪汪的,她说她在越剧界这么多年,现在年近五十了,只有一台以她为中心的原创大戏。而这方面赵志刚做得不错,原因是他活动能力比较强。
说起这些我心里也不大好受,但是难度也是很大的。现在排一部戏,动辄百万,如果说像《新拜月记》,全部动用院里的力量的话,可能成本还不会太高,但只要一动用外力,就不得了。这么多年来,我们越剧院的投资从来没有超过过100万的,严格控制在100万以内,人家都叫我管家婆。但如果请一个导演一下子要花掉一大半,那我还排什么戏呀?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确实没办法。
要求与希望
主持人:人才是剧种发展的关键与保证,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尤其是近年来通过“越女争锋”的比赛,为青年演员赢得了不少各个年龄层的粉丝,相比较传统的越剧戏迷,他们不仅在文化修养上有了提高,并懂得与时俱进,组织粉丝团,通过网络、媒体为自己的偶像进行宣传,大大提高了越剧青年演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李旭丹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作为优秀人才引进,来到上海越剧院这么多年,你有着怎样的感触?
李旭丹:作为人才引进,我来到上海快五年了,刚进团的前两年,院里对我的提拔很大,而这两年相对来看给青年演员的演出机会就比较少。但我也有个比较好的机会,能借到南京市越剧团,排了一部原创大戏《丁香》。在22岁的年龄,单挑一部大戏,而且女主角是两小时几乎完全不下场的,这对我的锻炼很大。
就像刚才盛舒扬提到的,我们有时有导演来指导,有时则完全靠录像,这样一来对人物的体会就不够,只是机械性地模仿,内心的学习和感悟很少,这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排一出,丢一出。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剧场,没有定点演出的单位,很难使我们不断充实自己。现在演出市场萎缩,演员锻炼的机会也少,不像以前老演员能有很多高密度的演出,而我们这样的状况,成长就特别慢。
黄德君:李旭丹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赵志刚是怎么出来的大家知道么?就是有一次主演的嗓子不行,这时候赵志刚出来救场,他为什么能救呢?就是因为积累。我是看着他进来的,很用功很刻苦,所以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同样的例子还有方亚芬,她刚进院的时候,演出机会很少,袁雪芬老院长没有第一时间接纳她,而是开出了一串名单,让她去找张洵澎、梁谷音、李炳淑等京昆艺术家,去学习,去借鉴,去思考。后来方亚芬的脱颖而出,离不开这长时期的艺术积累。
主持人:朱洋作为新生代越剧演员,前不久喜获白玉兰新人配角奖。作为一位90后,从事古老的越剧艺术,你有着怎样的体会?
朱洋:我是2008年来到上海,加上实习也有四年了,我觉得我来到越剧院蛮受到领导关爱的。先是进院来了个“七仙女专场”,后来又有了“五朵新蕊”汇演,我去年还得到了白玉兰的新人配角奖,我觉得我很荣幸。
青年演员发展存在的问题就像前面三位刚才说的,跟“录老师”来学习,而没有走内心的东西。2011年上半年排了现代戏《家》,我感受挺多的,从读剧本开始,导演就跟我们分析人物内心、人物关系。通过导演说戏的方式,我觉得虽然我是个配角,但当导演在和主角说戏时,我听着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排练对于自身的提高有很大帮助,让人感觉很幸福,结束以后都不想离开了。
现在一般演出商提了要这个戏,我们就要赶着在几天内把它排出来。要像排艺术品一样,就不太可能了。像袁老师的《祥林嫂》在厨房间的那一段,原著里只有一句话,就是“祥林嫂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编剧就能写一出折子戏,还这么经典,说明他们一直在揣摩。我真心觉得,他们这些老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方亚芬:机会永远给有准备的人。我就对我的学生们说:“你们真正能够出成绩的,是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在排练场,那是做给别人看的,真正想要做到肚子里面有东西,八小时以外去努力。就算是走进排练场,你也会比别人踏实,因为我今天做过功课了。没做过功课你跑进排练场,心里是空的。大家刚才说到演人物要走内心的东西,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积累,要文化底蕴、社会阅历还有舞台实践,多方面加起来才能把人物体现在舞台上。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得了奖,我心里很忐忑,我是不是真的达到这个水平?但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得到了梅花奖榜首,我觉得心安理得,我有这个实力,接过奖杯我非常踏实。以前觉得得奖很侥幸。现在的年轻演员想一步到位,对,职称大家都想评,但是你要想想,我是不是称职?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就算达到了,还是要不断提高。
另外,老师在身边的耳濡目染很重要。我的老师袁雪芬虽然不亲自教我,常常说“自己回去看看”,但我在她身边那么多年,直接获得的启发与感染是很大的。好的老师,好的导演,都不是手把手教你的,角色还是要靠自己去琢磨,去体会的。一个悟字十分重要,老前辈们的悟性就是我们的榜样。
主持人:在越剧改革70周年之际,将纪念活动的主题定为“坚守与突破”,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剧种的发展除了人才的培养,我们还需要理论先行。70年来,很多实践老前辈们已经做了,但是没有很好地得到总结。回顾当年袁雪芬大师的锐意进取与大胆革新,我很希望今天的越剧能像京剧、昆曲那样,第一个是要有玩意儿,除了声腔上丰富之外,表演上要有人物,不能只是炒冷饭的重复,在表演上要有技巧,有内涵,这样才有生命力;第二个是要有高浓度的文化介入,就像当年袁雪芬搞改革,很多大学生、编剧、作曲都自发加入,而向话剧、电影、京昆的大量学习,充分消化,也为越剧能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高浓度的文化介入是促进越剧发展的良方。
【请注意:新民周刊所有图文报道皆为周刊社版权所有,任何未经许可的转载或复制都属非法,新民周刊社保留诉讼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