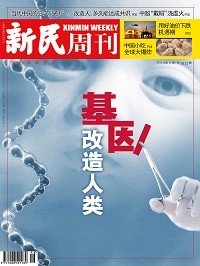漫长的治愈
撰稿|徐敏霞
纪实作品也好,虚构作品也好,我比较在意作者会选取什么细节来体现自己的立场。读《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每每总有放下书本细细回味之处。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应该不是孤例,也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张新颖过去曾提到过“自我愈合”一说,这个过程沈从文用了四十年。
“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创作者和普通人相比,因为敏感,更容易遭受日常生活的折磨,沈从文虽然频频依靠印象记忆里的美好来获得“更新的起始”,但这类烦恼总是反复发作、根除不了。他既需要吸取生活中的宁静和诗意,又对琐碎的侵犯感到不满。在事业顺利的时候,这些小事不一定会给人多大的困扰;而在对自己的社会价值不那么确信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扎扎实实的苦恼。
弃绝外求于政治,从理想落实到具体的事,是一种自救的方法,是对现实的突围。而落后于大家又使他感到痛苦,他试图自杀,之后便也知道,对于眼下的生活,去死同样不值得。新朋旧友乃至家人,沈从文回避了他们善意的期待,既不刚烈地对抗,也不亢奋地合作,而是投身到一项过时的、不被需要的新事业中,这在他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
从时代语境看,沈从文对“为国家做点事情”的理解总不在点子上,但这反而成全了他在“群”里保持住“单独”的生命。社会巨变,众生癫狂,周围人都能顺时应变,他却不肯如此,或者说模仿不来,因而感到孤独;但人要始终趋时并不那么容易,劝他重新拾笔写作的朋友,也有成了右派的,这使他一度担心自己,然而却没有,他连与“我们这代人”一同倒霉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恐怕没有比此时更能确认自己已经被“群”所抛弃的了,他宁可为不能继续以写作安身而痛苦,也不要为趋炎附势挑战立命底线而纠结,与自己搏斗好过与茫然搏斗,于是索性将“不上台盘”的人做到底吧。
沈从文五十八岁后,深受疾病的折磨,感受到身体内部的衰老,以至于一年一年随时觉得自己会报废。虽然此后多年社会仍处于不断的动荡与变化中,故人的背叛时有发生,心情的激荡在所难免,但与随时可能的死亡相比,任何人为的破坏和阻挠都表现得很虚无,这是健康人无法体会的。专注于喜欢的工作不啻为一种精神疗法,将能对付过去的生活琐屑和“有情”的幸福世界隔开。在心中完全排除了他人对自己改行的看法,天地变宽,情绪上也摆脱了压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让工作和生命相互支撑着往前走。至此自我愈合的过程已完满,之后有没有“出土”,有没有获得老天的平反,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至于晚年的美国之行,在傅汉思等旧识看来是“等了三十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与写小说的沈从文重逢),但沈从文本人没有那么恋旧,他更感兴趣的是新事物(冰淇淋、美国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作家本人的灵魂境界和作品获得的社会评价之间存在时差。当海外的朋友对沈从文的认识还停留在三十年前他的文学世界的时候,他的心境已经早早跨过了这一页(跨得很痛苦,但跨过了便也就轻松),大家期望看到的沈从文和沈从文本人已经是两个人。由海外传递到国内的沈从文热,称不上是作家晚年的一次逆袭,更构不成对作家本人迟到的安慰;反倒是,这个宝贝没有在粉碎一切的各种运动中成为“古人”,他的活着,治愈了读者。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