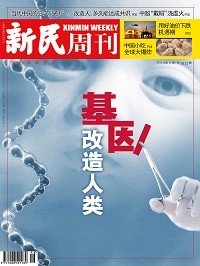时间旅行到底行不行?
阅读提示:为什么伴随着宇宙现实的揭秘和曝光,人们反而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焦虑?探索宇宙的欲望越是强烈,收获越是丰厚,随之产生的末日危机越是不可遏止。这些外星球“恐怖主义者”其实是我们内心的敌人,是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在这个星球犯下的错——冷战与局部战争、恐怖主义、环境恶化——买单。
记者|何映宇
在现实生活中,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难以逃脱的魔咒,可是,在科幻电影,穿越时空却大行其道,死神看来要歇业了,这一切的源头,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起人们对时空穿越的无限遐想。爱因斯坦在其相对论中明确提出:“当一个物体达到光速,那么时间就会变慢,这一现象称为‘时间膨胀’,而当这个物体的速度超过光速,那么时间就会倒流。”
这让科幻迷们脑洞大开。日心说发表之前,所有人都认为天圆地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心说之后,宇宙的概念完全不同了,登月、星球大战、外星人入侵的故事乃应运而生蔚为大观;而相对论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时间,未必是恒定流逝的,它可能弯曲,可能变得缓慢,也可以逆转倒流,即我们可能返老还童,可能和你的高祖或者第十代玄孙在一起。
这一切,以前完全不可想象。原来,理论,可以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脑洞。
时间的难题
反思时间的第一人却并不是爱因斯坦,最先对客观化时间产生怀疑的是著名的基督徒奥古斯丁,对,就是写《上帝之城》和《忏悔录》的那位。他发现,既然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时间也一定是上帝创造的,也就是说,时间,是在上帝哪天拍脑瓜想出来之后才有的事,而在上帝发明之前,没有时间,但是有上帝。就是这么回事。
既然时间不是客观化的,那就是主观化的喽?于是奥古斯丁有了一句名言:“时间在我们心中。”
奥古斯丁虽然是基督教的一代宗师,但是他所发现的这个时间问题可能超出了当时普通人的理解程度,所以过了整整1400年才找到他的知音。这个人就是大哲学家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不谈上帝,他对时间的兴趣来自时间的虚无。时间到底在哪里?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它的表现形式是日升日落和时针滴答,但是,日夜、钟表和时间是一回事吗?如果没有“我”,时间还存在吗?或者,时间还有意义吗?
后面还有柏格森写《时间与自由意志》、海德格尔写《存在与时间》,都是在哲学的范畴内讨论时间,也就是玩术语玩概念,侃晕一个是一个,海德格尔名气再大,读懂这本砖头一样的存在主义大作的有几个?到爱因斯坦就不同了,人家是科学家,没有哲学家夸夸其谈不靠谱的印象,而且爱因斯坦有理论有数据,摆事实讲道理,那说服力杠杠的。虽然他的原作比海德格尔还要难懂,但一经媒体通俗化简单化的曝光解读传播还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穿越剧写手们的春天来到了!
爱因斯坦另一大假想也成为各大科幻迷津津乐道的理论资源,那就是虫洞。
虫洞其实也不是爱因斯坦首先提出的概念,191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弗莱姆首次提出了虫洞,1935年,爱因斯坦及纳森·罗森在研究引力场方程时假设透过虫洞可以做瞬时的空间转移或者做时间旅行。还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幻小说领域,1895年,H.G.韦尔斯在《时间机器》中就写到了时光机,真是想象力超群的奇人,但是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还得说是爱因斯坦。
1949年,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发现了广义相对论允许的新的时空,这首次表明物理学定律的确允许人们在时间里旅行。哥德尔在和爱因斯坦于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度过晚年时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相对论,从而熟知了爱因斯坦的这一理论。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爱因斯坦的这个时空里,整个宇宙都在旋转,远处的物体绕着小陀螺或者陀螺仪的指向旋转。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一种悖论,即一个宇航员,他还没出发就已经回来了!这一问题一度让爱因斯坦非常沮丧。
这一让爱因斯坦沮丧的发现却让科幻迷们兴奋,因为再快一点,就可以回到过去了,可以去改变你的人生、挽回你爱的人、可以让死去的人复活……可以做太多的事。时空旅游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太多人想吃后悔药。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专门辟了一章谈虫洞与时间旅行,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位年轻小姐名怀特,
她能行走得比光还快。
她以相对性的方式,
在当天刚刚出发,
却已在前晚到达。
这诗实在是够烂,我们不去管它,我们来看这首诗暴露出来的问题:前晚到达,前晚,是在当天之前,还是当天之后?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当天从A地出发,到达B地,不论你以什么样的速度,到达B地应该在A地出发之后,可是,如果你以超光速运动,其结果却出现了,到达B地发生在A地出发之前,这怎么可能?
但是缩短旅行的时间则是可行,最快的方式就是走捷径,比如,虫洞。地球和α-半人马座相隔20万亿英里,而虫洞只有几百万英里,那就大大缩短了星际旅行的时间,何乐而不为?
那么虫洞到底是怎么样的?在1935年爱因斯坦和纳珍·罗森写的那篇论文中他们说广义相对论允许他们称为“桥”(即虫洞),这种“桥”不能维持得足够久,使得空间飞船来得及穿越:虫洞会缩紧,而飞船会撞到奇点上去。
祖父悖论与平行空间
那么有人就提出来了,能不能把它撑撑大,让飞船通过?
也许吧,谁知道呢。1966年播映的科幻剧集《时间隧道》头一次将人类制造时间隧道的幻想科技呈现在影视作品中,美国政府所研发的这项神奇技术一次次地将主角送向不同时代完成任务,那种黑白相间的螺旋式空间令人们领略到了时空隧道的神奇与疯狂。后来,这种有点炫的隧道就成了虫洞标配。在2009年电影版《星际迷航》中,黑洞成为两个平行宇宙的连接点,史波克与尼诺在被黑洞吞噬的同时,穿越了时间与空间,不过他们出了点小差错,史波克与尼诺进入黑洞前后相差了一秒钟,结果由于黑洞中心时间迅速变慢,导致他们出现在第二时空相差了25年。既然虫洞谁也没见过,科幻导演就说了算了。有的比较普通,电影《比尔和特德历险记》中的是电话亭、《神秘博士》中是警亭,都不免有点随意,想想《热浴盆时光机》中出现的温泉浴盆型时光机与《超时空泡泡机》中的洗衣机型时光机,那才叫趣味盎然。而最奇怪的虫洞则是《有关时间旅行的热门问题》中,时间隧道居然是一间不起眼的卫生间。
不管是不是卫生间,如果飞船通过了,你回到了过去,那你能做什么?实际情况是你什么都不能做。最常问到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到过去把你的祖父杀死,你是不是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就是经典的科幻动作片《终结者》系列所探讨的问题,这也被称之为“祖父悖论”。
《回到未来》的男主人公马丁回到过去后,竟然被正值豆蔻年华的母亲看上,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如果他不能让父母相爱并结婚,他根本就不会诞生。为避免消失的命运,他想方设法撮合父母相爱。
而在《终结者》系列中,公元2029年,经过核毁灭的地球已由电脑“天网”统治,人类几乎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人类在领袖约翰康纳的领导下与天网英勇作战,并扭转了局面。“天网”为了改变这一切,制造了时光逆转装置,派遣终结者人型机械人T-800回到1984年,去杀死约翰的母亲莎拉·康纳,以阻止约翰的诞生。第一部阿诺德·史瓦辛格是大反派,第二部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拯救者,反正就是有坏蛋妄想改变历史以达成统治未来的阴谋,被正义者一一化解的故事。
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好运那会怎么样?未来的幸存者再回到过去把机器人赶走,或者根本就不允许发明机器人和电脑?当然了,未来的机器人怎么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也会派机器人来继续组织,这样,《终结者》就是拍个100部,故事也讲不完啊。
诺兰的《星际穿越》就考虑到了这层问题,所以飞行员库珀(马修·麦康纳饰演)回来看他的女儿,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这样的话,他虽然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是一个巧妙的处理。这也是科学家们思考的另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有多个宇宙存在,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一个?那么,也有很多种历史,很多个你?这些历史和你我他在平行宇宙里各自发展着,如果你回到过去,改变了历史,那你就进入另一个宇宙,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回不去的。
我们内心的敌人
有点搞脑子,但在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中,时间旅行确实是最让人们着迷的桥段之一。
1985-1990年美国拍摄的《回到未来》三部曲是早期穿越电影中的代表作,影片的热映表明它戳中了美国人民的G点:未来。不是奔向未来,就是未来人来到现在,带来的是各种未来闻所未闻的高科技。几乎所有此类的美国电影都将重心放在对未来的想象上。可是对照一下中国人的穿越G点,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宫》《步步惊心》是清宫戏,周星驰《上海滩赌圣》讲的是有特异功能的周星驰回到1930年代,靠他的特异功能在赌桌上大显神通的故事,穿越是噱头,其实还是一个年代戏。
美国,不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国家,可是中国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感到自豪。大唐盛世,蒙元帝国,疆域辽阔,万国来朝,何等风光,到了近代,风水轮流转,轮到欧美靠着洋枪洋炮坚船利炮来作威作福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缓过气来,这是巨大的失落。所以,当美国好莱坞在大量生产奔向未来的科幻巨制时,中国人总喜欢怀旧与穿越到古代。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大量西方科幻片中,所渲染的,是末日危机,中国人没有末日观念,这和基督教的影响有关,相对论不仅没有让科幻作家变得快乐起来,反而变本加厉,这是杞人忧天吗?
你看乔治·克鲁尼2015年的最新作品《明日世界》,主人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即将被末日毁灭的地球。他们穿越到未来,义无反顾地解决了世界末日危机,拯救了全世界,OMG,没有克鲁尼这样的英雄,有一千个地球也完蛋了啊。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藤子·F.不二雄(其实是两个人)笔下那个穿越而来的哆啦A梦出场时,是以一个“乌鸦嘴”的形象出现的。在《机器猫》第一卷第一集“来自未来世界的机器人”中,大雄躺在榻榻米上,悠哉游哉吃东西,这时,一个不祥的声音突然从屋子里冒了出来,大声说着一些丧气话:“大雄,你会在三十分钟后上吊”,“在四十分钟后受烤刑”……很不幸,这些预言无一例外全被哆啦A梦说中了,后来一一应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开头所制造的笑料,以对未来的悲剧性想象为依托,这种多少有些悲观的情绪几乎在所有的科幻类作品中都弥漫着。在这些作品中,未来是一个冰冷的世界,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地球的繁荣,反而引来杀身之祸。施瓦辛格特别擅长在未来战争中和机器人来一番精彩的肉搏,以展示他过人的肌肉。而当乔治·卢卡斯将这套危机意识投射到大银幕上,宇宙中多了多少腥风血雨?甚至幼齿的铁臂阿童木和鼻子像鸡蛋一样的茶水博士也要组成了一个超级组合,为拯救地球而痛下杀手。
一般来说,科幻作品的英雄史观是很表面化的,观众们就爱看奥特曼日复一日地和傻瓜怪兽来一场装腔作势的“殊死”搏斗,最后的结局不外乎正义战胜邪恶这样的陈词滥调。不过也有特例,《星战前传3:西斯大帝的复仇》就将天行者安纳金推入了精神之恶那黑暗的深渊。
卢卡斯提出了这样一个论题:从来不存在永远的善。
虽然斯皮尔伯格的《外星人E·T》以一个和颜悦色、楚楚可怜的形象示人,但在相当多的科幻片中,外星人是一副侵略者的嘴脸。在库布利克的《2001:太空漫游》中,外星人是那种高大、外形像昆虫一样的形象。在《异形》中,我们看到了可怕的外太空生命体,它们显然没有那么友好。
为什么伴随着宇宙现实的揭秘和曝光,人们反而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焦虑?探索宇宙的欲望越是强烈,收获越是丰厚,随之产生的末日危机越是不可遏止。对于宇宙的恐惧是与人类宗教信仰的缺失成正比的,而工业文明正在制造了一种悖论:我们在改善着我们的生活,同时,这种生活又在毁灭我们。就像爱因斯坦,它的理论探索了宇宙,可是,我们知道,他著名的公式E=mc2,正是原子弹制造的基础,是科幻核危机世界末日的根源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外星球“恐怖主义者”其实是我们内心的敌人,是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在这个星球犯下的错——冷战与局部战争、恐怖主义、环境恶化——买单。回不回得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则是关注当下,认识我们自身。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