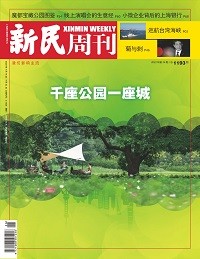日本“慰安妇”:军国主义烂污泥沼的祭品
阅读提示:所有这些饱受磨难的灵魂静静伫立,默对斜阳。她们的经历既是政治的,也是历史的;既是个人的,也是女性的。
记者|孔冰欣 特约记者|赵 松 颜文璐(日本《东方新报》)
当“慰安妇”这三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时隔经年再度大规模袭来,不禁要问,所有人真正理解所谓“慰、安”背后,被侮辱、损害、扭曲的公道与人性吗?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诱骗、逼迫等手段强征随军性奴隶,目的是“安抚士兵、鼓舞士气”。而“慰安妇”之名,是日军强加给这些随军性奴隶的“美称”,是最卑鄙可耻的遮羞布。说到底,那些弱势女流,只是日军发泄兽欲的无辜对象。
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来自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女子挺身队”——和“神风敢死队”相似,“女子挺身队”也是军国主义怪胎的产物,是侵略战争机器上畸形的零件。她们或许可以自我催眠,“这是光荣,这是奉献;这是履行帝国的意志,这是奔赴前线服务皇军”。事实上呢,“炮灰”终归是“炮灰”。
而最讽刺、最具悲剧意味的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出于对进驻美军的恐慌畏惧,尤其是出于对日本妇女或遭暴行凌辱的忧虑,政府决定参照战时“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此事代价不菲,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却飞快批准了预算——“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洁和血统的延续,十分划算。”其后,日本内务省通告全国,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遂“应运而生”。政府冠冕堂皇地声称“协会维护民族纯洁、百年大计,乃阻挡狂澜的防波堤、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明眼人早一望即知:这是“国家卖春机关”。
起初,连妓女都不情愿这么快就要“转化思维”、服侍“敌人”,于是日本政府干脆撕下伪装,为凑数公然征集良家妇女。其时日本国内民生凋敝,很多女性迫于生存压力,只得无奈应聘所谓“涉外俱乐部女事务员”的“职位”。梦魇就此开始,据记载:“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有些是稚嫩的女孩,对异性还没什么认识呢,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的轮番蹂躏,很可怜啊。一个曾在银行工作过的姑娘就是这样精神崩溃自杀的,后来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
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当底层女性苦苦挣扎的时候,日本皇族、公卿贵胄、豪门财阀却把自家娇养的掌上明珠们尽量保护得滴水不漏;另一方面,有些战时狺狺狂吠的右翼投机分子,又在战后“积极投身RAA事业”,利用本国妇女的身体大发横财……用普罗民众的“慰安”换来“上流社会”的“清白”与苟且,踩着同胞手足的血泪与尸骸上位,军国主义的荼毒让本已丧心病狂的衣冠禽兽愈发泯灭人性。
尔后,出于对性病泛滥以及自身形象问题的顾虑,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日本“慰安妇”们就这样被扫地出门,并且拿不到任何补偿;而多半染上“脏病”、衣食无着的她们,可行性最高的谋生手段,依然是从事皮肉生意。
日本“慰安妇”在人数上可能是最多的
那么,既为战争“挑起国”又为“战败国”,既为战争“加害者”又为“受害者”的日本,其社会本身究竟如何看待“慰安妇”问题?带着种种疑问,《新民周刊》特约日本《东方新报》,采访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日关系专家高原明生。
高原明生表示,“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不只有中国人、朝鲜人等,还有日本人。而且,日本“慰安妇”在人数上可能是最多的。但是,战后日本政府并未将日本“慰安妇”作为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来对待,也极少有受害者站出来发声。高原明生分析,日本“慰安妇”中有很多人是被骗和被强迫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自愿的——被强迫还是自愿,这在日本成为“慰安妇”问题的主要争论点之一。日本《大辞泉》对“慰安妇”的解释,可一窥此争论之端倪:“慰安妇”是指在卖春设施、慰安所里以战场上的军人为对象进行卖春的女性。这样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慰安妇”制度的残酷性。
大概1965年前后,一些关心日本和朝鲜关系的人注意到战时“慰安妇”的存在,但是那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韩国社会的变革,韩国国内开始将“慰安妇”当作社会问题看待。1990年1月,韩国学者尹贞玉在媒体上发表了有关“慰安妇”的调查报告,日韩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逐渐被人们认识,“慰安妇”问题终于在韩国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年5月,卢泰愚总统访问日本,韩国人民要求日本谢罪和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年12月,韩国的受害者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日本政府展开对“慰安妇”的调查。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制募集、移送、管理“慰安妇”这一事实,并表明道歉与反省。
在日本学术界,有很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主流还是持批判态度的。高原明生指出:“我看到的日本学术研究中,没有人是否认存在‘慰安妇’这一事实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战争带来的巨大悲剧,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而在日本社会,一般民众对“慰安妇”问题的认知似乎限于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纠纷”。高原明生称,没有看到关于日本民众对“慰安妇”问题认知程度的调查,很难说日本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慰安妇”问题。但是,普通日本民众获得与“慰安妇”有关的信息主要是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而媒体通常只在“慰安妇”问题成为日本与邻国“外交纠纷”的时候才会报道,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想见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并未将“慰安妇”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慰安妇’问题是一个涉及‘性’的话题,在面向年轻人的教育方面,比较难处理。”
高原明生恳切表明,“慰安妇”问题是一个极易激起民族情绪的问题,所有人应严肃审慎待之,相关言行要经过深思熟虑。采访中,他多次强调日本发动战争是错误的,“用力量来强制他人是不对的,而战争是力量和力量的冲突,所以我们应该杜绝战争再次发生,这是最大的教训。“‘慰安妇’问题是战争带来的诸多悲剧之一,女性和孩子这样的弱势群体在战争中牺牲最大,要避免悲剧重演。”
安倍政府从闪烁其词到大放厥词
诚如专家所言,“应该杜绝战争再次发生”,“要避免悲剧重演”;然而,今时今日的安倍政权,所言所行却近乎南辕北辙。
实际上,日本国内对待“慰安妇”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1995年,号称以“河野谈话”发表为契机,认识到“慰安妇”问题严重性、从反省视角出发的半官方半民间组织“亚洲妇女基金”设立。其宗旨是把从日本国民处募集到的资金和政府财政作为基础,结合医疗资源,为“慰安妇”受害者提供补偿和帮助。截至2005年,“亚洲妇女基金”对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等285名“慰安妇”受害者进行医疗与资金支援,国民集资总额约5.65亿日元,政府对“慰安妇”医疗帮助的支出约7.5亿日元。不过,“亚洲妇女基金”并未提及对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的赔偿与支援。“亚洲妇女基金”运作期间,还受到各国的抵制,因为此计划被认为是日本政府有意回避了国家赔偿。
2015年12月28日,日韩外交部部长在首尔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由日本政府出资10亿日元设立“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基金,两国政府将合作开展恢复“慰安妇”受害者名誉、抚平受害者内心创伤等各种项目。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在协议签订后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安倍向“慰安妇”受害者表示道歉和反省。但因为韩国国内持续抗议《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加之韩国政权更迭,这一协议没能得到贯彻,为此日本政府撤回驻韩大使以示不满,日韩关系也因此跌至谷底。
而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含糊、反复乃至否认,正是衡量其历史观的一面“照妖镜”:2013年5月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表示,日本政府强调不会修改承认日本军队性奴役的“河野谈话”,并坦诚说明历史问题。同年10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面对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有关“慰安妇”的提问时表示,“不应把‘慰安妇’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至2014年6月9日,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直指河野“在‘慰安妇’问题上没有坚持应有的信念,给后代留下了很大的祸根”。同年10月21日,菅义伟“有样学样”,在国会问询中宣称河野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有很大问题,我们否认。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2016年1月18日,安倍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重申,日本政府在已经掌握的资料中没有发现任何直接表明军队和官府强征“慰安妇”的记载。
右翼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安倍政权,从闪烁其词“不应把‘慰安妇’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到大放厥词“没有发现任何直接表明军队和官府强征‘慰安妇’的记载”,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如果“慰安妇”问题都不算政治问题,那什么问题才算政治问题?!如果包括日本本国妇女在内的生灵涂炭都不算“直接证据”,那什么证据才算如山铁证?!
女性在“军国主义+父权文化”下失声
从整个人类的高度去审视侵华战争,乃至二战全局,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慰安妇”、抑或是奥斯维辛,都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历史、日本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德国人的历史,而是全人类的历史,是深深扎入人类文明心脏的刺。对于“慰安妇”的讲述,需要超越民族范式、国家范式,因为它是世界的浩劫。真正的和解,不是各方达成了某种利益上的共识,而是各方建立起“以真相换取宽容”这样的价值共识。
一齐坠入日本军国主义烂污泥沼,成为无间幽冥之血肉祭品的,是中国、朝鲜半岛、日本本土等等不计其数的失落羔羊。针对“慰安妇”的性犯罪,在民族羞耻的意义之外,更是赤裸裸针对女性的暴力。这种暴力在战争中以极为恐怖的样貌彰显,在和平时期则以隐秘而漫长的耻辱创痛,将受害者的一生钉在了苦难的十字架上。
在各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修辞当中,“祖国”常被比作“母亲”,象征着神圣和孕育。而在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瞄准女性的性暴力成为了战争中心照不宣的“自选动作”。这种暴力的根源,是父权文化刺激下故意释放的野蛮欲望——对他族最大的羞辱和打击是践踏对方的母亲、妻女,“强暴他族女性”与“践踏他族领土”在事实上运行的是同一逻辑。因此,战争中的性暴力不止给女性带来耻感,也给受侵国族的男性甚至全体社会带来耻感。“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这种耻感是极富性别意味的,民族权力关系当中渗透着性别主义的色彩。
日军情报部某军官递交陆军本部的一封文件完全佐证了上述观点——“当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恢复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二战前后,穷兵黩武、极权独裁的日本军国主义与威势膨胀、面目狰狞的父权语境黏合互融得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最该感到可悲、最该感到绝望的牺牲者,恰恰是其本国的“慰安妇”——再回首平静地审视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军国主义的突出特征除却对外侵略扩张,还包括了什么?是对内镇压反战运动,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人民被要求向国家无私奉献,私权、人权、言论自由受到压抑;人民日常生活常受军事上的动员与干涉;政府吹嘘掠夺来的“利益”,激发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以确保民意对战争的支持……
所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父权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日本“慰安妇”问题上,具体表现为直接迫使作为个体的女性丧失了发言的权利。她们的身体被大写的“集体”所操控,从而处于“无声”的状态,为所谓民族、国家,甚或“人类未来”代言,唯独不为自己代言。战时,属于“主动攻击国”一方的日本“慰安妇”,要响应动员号召,用肉身激励、犒赏本国的军人;战后,属于“被动承受国”一方的日本“慰安妇”,又要“解救国难”,用肉身自荐枕席,平息可能降临的极怒惩罚;她们总是在做贡献,她们又总是随时随地可以被“过滤”掉——她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牲畜草木啊!
日本电影《望乡》里,在南洋死于困苦与心碎的东瀛娼女们,坟墓统统背对“祖国”;《人证》里,女服装设计师为维系名誉与地位,不惜谋杀了自己昔年与驻日黑人士兵生下的混血儿,却无力回天,万念俱灰下跳崖自尽;再联想到中国“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所有这些饱受磨难的灵魂静静伫立,默对斜阳。她们的经历既是政治的,也是历史的;既是个人的,也是女性的。
“慰安妇”问题不是简化的“国仇家恨”,亦非普世的“苦涩鸡汤”。我们值得尝试的,是进一步审视和反思,并借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希望。
祈祷,蓝色星球无战事。
(鸣谢《东方新报》孙冉老师对本文的帮助)
链接:高原明生
东京大学法学与政治研究科教授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副院长
1981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任立教大学教授,2005年开始在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系政治科学研究科担任教授。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专门调查员、英国开发问题研究所理事、哈佛大学特别研究员、亚洲政经学会理事长,新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日本方面秘书长),北大特别研究员,Mercator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等。近期著作有《中国近现代史系列5——开发主义的时代1972-2014》《东京大学私塾 现代中国讲座》等。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