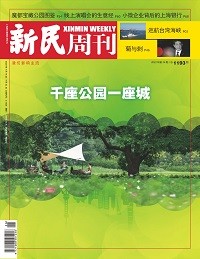忆当年,他们一直在寻找安放书桌的地方
记者|孔冰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有些民族的基因密码是被死死锁定的,比如读书,以及为什么读书。所以,对很多恋恋不舍、念念不忘的观众来说,《无问西东》片尾7分钟的彩蛋,是远比电影本身更加如诗如歌的震撼余音。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那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府,瞬间将国人的思绪拉向了历史的纵深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南开——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首遭战争摧折;接着,国立北大、清华,亦难逃劫运。三校遂先约会于湖南长沙临大,继而被迫流徙云南。1938年,昆明建起了一个临时联合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8年之后,南渡之人,各自北返,“神京复,还燕碣”,西南联大几与抗战相始终,确属一代盛事,百世难遇。
除却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坚持办学的高校另有不少。那些音容笑貌宛在眼前的先辈们,聚在一块,共同耕耘,互相切磋,重建学术乐园。外在环境虽然险恶,但教师埋头著书、勤快解惑,学生好像永远有填不满的求知欲望,师生交流绵密,知识火花热闹迸放,如响斯应,此所谓“弦歌不辍”。既是浩劫,也是风云际会,更是因缘凑合。
中华之大,他们一直在寻找安放书桌的地方。
南渡记
西南联大极盛时,计有教授170余位,学生2000多人;一批学界名人汇聚一地,顶尖学生群集一处,是抵御外侮、反抗强权的象征,是人才培养基地、知识分子的庇护所,是民主堡垒。多年后,三校师生仍以联大为傲,自有其缘由。
顾名思义,“联合大学”是“混编”而非“化合”,故南开之活络、北大之自由、清华之严谨,依然各自保留其底色。所谓“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虽是一部校史,却是三个学府精神所寄。
而若论联大基本精神,则必曰“自由”,包括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其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比如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学生同样享受到了“出版自由”,可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形成了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自觉地抵制了国民政府试图强加的思想控制。此外,举凡“身临其境”联大自由民主学风的人,无不念兹在兹,倍感亲切:“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另一“融汇东西文化优长”之处,是他们虽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说,他们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从这一“拒绝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联大知识分子群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
正因西南联大具有“道德楷模、精神领袖”的力量,故其能够成为隐潜意义上的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千百年后,“也许联大在昆明的有形校园早已灰飞烟灭;无形但重要的是,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绘出的知识地图,每能代代相传,层层扩大,一如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铭之词‘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之序:吕芳上《战争、西南联大与历史遗产》)
对于后人而言,故纸堆里的叙述终究不如鲜活的影像来得贴近。有鉴于此,观众的确应当致谢《无问西东》的拍摄团队。据悉,他们在14个月里看了百万字的文献和17万张照片,诚意满满,还原、加工了诸多真实而感人的历史细节。
比如外号“寡言君子”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他鼓励学生勤恳学习,并不希望他们喊口号、谈政治。学生不听他的,被抓了,他去保释,劝解;再被抓,他再去谈判,去保释。学生组织的激进活动,他不禁止,不参与,不干涉。
西南联大成立后,校务委员共三人,除了梅贻琦,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不过,实际“主政”的,还是资历、年纪排末位的“小梅”——就因为他主见甚少。当时流传一首打油诗,专来戏谑梅氏口头禅: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然而,名士毕竟是名士,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回忆日本轰炸:“……(梅)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比如和电影里的吴岭澜一样,其时清华转系者实不在少数。张世英起初学的是经济,三年过去,觉得自己更适合哲学,后终成小逻辑的一代宗师。而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李长之从生物系转到了哲学系,吴组缃从经济系转到中文系,林庚则从学物理改为学中文——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比如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华,轮流到北大、清华做演讲。清华那一场,徐志摩充当翻译,“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而和志摩“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成、徽因,则是西南联大“铁皮校舍”的设计人——没钱没材料,所以没办法。因为“没办法”,反倒成就了联大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停课赏雨”的佳话;推开窗户,还可以看见马约翰老师带着学生们跑圈运动——马约翰一出现,何兆武就“倒霉”了,在“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的“恫吓”下,他乖乖用交体育报告的方式补回成绩。
比如“超级必修课”跑警报。电影里的吴岭澜拎着鸽子,现实中的金岳霖抱着鸡;地质学先驱袁复礼的“标配”是恐龙骨架;被刘文典称为“国粹”的陈寅恪,方言口音浓重;闻一多的美髯太醒目,上课时师生齐抽烟;杨武之(杨振宁父亲)在防空洞里,与学生讨论数学问题;而和沈光耀一般喜欢到锅炉房煮糖莲子的,是汪曾祺回忆里的广东人郑同学;至于双胞胎兄弟郭大林、郭小林,角色设定或借鉴《未央歌》天真开朗的童孝贤……“天南海北人,五湖四海音”,正是西南联大的如实写照。
最摧断肝肠的,无疑是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诲。他毕业于清华,考取了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吾辈今后自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短长,方能雪耻复仇也!”抗战爆发一个月后,沈崇诲率诺克机七架,奉命轰炸日本船舰。任务完成返航归途,至白龙港上空时,忽发现大批敌舰,此时的他已无炸弹可供投掷,飞机内部机械又发生故障,难以返回基地。最后,他决定奋力一搏,瞄准一艘日舰,将马力调到最大,由两千米高空极速而下,与敌舰同归于尽。
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是沈崇诲的同龄人,同样就读于南开中学,同样加入中国空军,同样在抗战时阵亡。1937年8月14日,张锡祜驾驶马丁机3006号赶赴南京对日作战,但飞机突遭雷雨天,在临川上空失事,张锡祜不幸遇难。闻知儿子死讯,张伯苓并未哭泣,愕然沉默后,连道“死得好”。若非抗日背景,若非家国情怀,一个父亲怎会说出如此“不近人情”的话?!
西迁录
既有北地高校之南渡,便有上海高校之西迁。
1937年8月12日,诗人冯至到江湾招考同济大学附中新生(大学预备班),早晨他从吴淞乘小火车,傍晚回校时小火车就被日本人停了。一时间,诗人无车可乘,无路可走,夫人姚可崑(同济高职的德文教师)则在等待中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下,冯至租一小舢板,乘着烟雾在日军横行的军舰中穿行。夜里十点多,他恍如隔世般潜回在市区暂住的小屋,方用罢一碗面条,隆隆炮声自天而降。水浪如利剑般在诗象里冲天而起,同济吴淞校园在硝烟中化为尘土。
为保存文脉,同济大学决意迁往内地,先后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同济人数路并进的总里程加在一起,超过了两万二千里,可谓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老一辈回忆,“同济大学是日军重点追炸的对象”;“八年抗战救国,估计没一所大学走的路比同济更远,受的磨难比同济更深”;“同济搬到哪儿,日军就撵到哪儿,是否生怕同济与德国有关的军工、造船和医学等专业会造成‘麻烦’?”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事济天下;同济大学,确实是日本人的“大麻烦”。“八一三事变”后,同济救治的军民不知凡几,待全面抗战爆发,同济医学院教授张静吾特赴南京,建议以军医署名义命令向内地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以加强军医力量,保障伤兵救治。军医署后来组织了12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往苏州。而在张静吾组建第五重伤医院的同时,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81名师生员工奔赴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
医疗救人,军工救国。自1937年内迁至1945年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国家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当时我国的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兵工署、21兵工厂、22兵工厂、50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枪弹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事高层技术和研发的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故彼时有“十军工,九同济”之说。而机械系的一些教授,同时兼任兵工署工程师,在上课之余,秘密研制武器。如机械精密仪器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蔡其恕,主要从事战时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中国现代光学工业奠基人彭明经,主要从事炮瞄装置的研发工作。(朱大章:《“十军工,九同济”一说始于抗战》)
李庄时期,趣闻颇多。当地百姓发现,同济医学院“只见尸体进,不见尸体出”,满腹疑惑。一日泥瓦匠修屋顶,透过缝隙瞥到师生拿着刀子对台上的尸体“划来划去”,一旁还放着个滚水的锅子,顿时魂飞魄散:“下江人(同济来自长江下游)吃人啦!”消息传开,李庄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为消除误会,同济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向居民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在这以后,即便医学院学生拎着“骷髅头”去茶馆,当地人也见怪不怪了。
那几年的李庄,堪称精英荟萃,不仅安顿了同济师生,还容纳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体制人类学所和社会科学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和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而关乎同济的大事,有两桩不得不提:一是校医唐哲亲自救活数十例麻脚瘟病患,医学院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邓瑞麟经过动物实验等查出病因,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二是生物系教授童第周邀请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来访,李氏表示无以置信——童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实验胚胎学家,他的学术成就,竟是在“沙漠一般一无所有”的实验条件下完成的!
1944年冬,日本为挽败势,制定了旨在打通滇缅公路的“一号作战计划”,铁蹄踏入贵州独山。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驱逐敌寇、收复失地。此讯传到李庄,同济师生群情激昂,年仅32岁的留德博士杨宝林教授率先加入了报名队伍。短短几天,同济报名从军的同学达到600多人,约占在校学生数的三分之一,创全国纪录。经体检,共有364名学生加入抗日军队,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更有几个近视的学生,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只为如愿。当年,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直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另一沪上老牌名校复旦大学,抗战时迁至重庆北碚夏坝。北碚期间,复旦聚集了众多著名专家前来教书,如陈望道、顾颉刚、孙寒冰、周谷城等,“老舍和梁实秋都是客座教授”。为了使学校附近的贫民能有求学的机会,复旦师生还举办了民众夜校,此等情操,分外难能可贵。而先后迁至重庆小龙坎、九龙坡、溉澜溪等地艰难办学的上海交通大学、迁至贵阳的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等其余高校,皆怀抱济世安民之宏愿,以朗朗读书声对抗侵略者。
萨义德说过,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知识分子无法做“局外人”,无法不向往国家富强、未来光明,无法不为这样的目标被迫着发出心灵的吼声。将国族的民主、科学、自由、进步当作毕生的追求、永恒的理想,才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础。
张世英曾在接受媒体人采访时,回忆躲避轰炸、在防空洞里打桥牌的情形。他仰着头,望向远方,忽然陷入另一种世界。俄顷,他说:“那时候,可真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呢,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是社会前景与个人前途皆美;是中华之大,总可寻找到安放书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