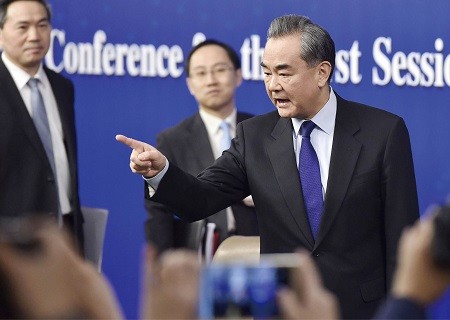超时空旅行只是 “白日梦”吗?
阅读提示:也许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在宇宙中不那么茕茕独立,也许我们只是想看看被改变的历史能否书写不一样的篇章,也许没有也许——坦白讲,“也许”最高级的超时空艺术,并不源于工整方圆,反因无序的错乱铸就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孔冰欣
2017年,大卫·林奇的Cult巨制新版《双峰》(Twin Peaks: The Return)播出,此时,距离前作中那句著名的台词“25年后再见”,真的已经过去了25年。
2018年,由David Duchovny和Gillian Anderson领衔主演的传世经典《X档案》时隔十余载重启第十一季,“I Want to Believe”的海报犹在,“The Truth Is Out There”的好奇与追索犹在。
不知道下一个千禧年降临之前,人类是否能够挣脱时空的束缚,挣脱肉身的束缚,实现真正意义上穷究宇宙的夙愿。对超自然现象和外星智慧的兴趣,对科学技术发展失去控制的惶惑,对道德滑坡、世风每况愈下的批判,对“阴谋论”思维方式的若即若离,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带有民粹色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霸权的忧虑,以及对天灾人祸和“世纪末”挥之不去的恐惧,共同交织出一幅具有太多不确定性的未来科幻图景。
这种复杂的情感,反映在欧美科幻类题材的影视作品里,便呈现出多重文本堆叠、涵义一言难尽的银幕奇观。更有甚者,除了思考地外生命的可能性与生存危机的紧迫性,还大量引入哲学、宗教与神学的意象、母题及暗示,表达了游离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游离在单薄躯壳与浩渺苍穹之间的心灵震颤。
那么,准备好了么?请跟我来,一起踏上这次星球迷航的超时空旅行罢。
空间探索:星河烂漫无垠兮
今年在《头号玩家》里狠狠玩了一把的斯皮尔伯格,天生不老童心,极具想象力,对外星题材也是津津乐道。
1977年纽约首映的《第三类接触》,明确了与星际来客“接触”的可行;1982年上映的《E.T.》,更是温柔得淌出了琥珀般的鎏金蜜意。与冷战时期对峙、冷峻的气氛大相径庭,这两部电影一反常态地着重描写了人类探索未知的心理,而非外星人的狡诈凶残。虽然,“安详”与“爱”的主旨往往容易陷入乌托邦的不切实际,但反观今日全球格局,这份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终将失守,还是令人唏嘘的。很难说,以后在电影里“迎接”外星人的,到底是鲜花与音乐,还是子弹与炮火——事实上,大导演本人亦在《世界之战》(2005)里表现出某种模糊的立场,外星生命不再是和平的使者,反以侵略的面貌肆虐地球,涂炭生灵。
类似《世界之战》这般地球人单挑外星人,相对更加突出“二元对立论”的电影,诸如《异种》系列(1995-2007)、《独立日》(1996)、《星河战队》(1997)、《天兆》(2002)、《第九区》(2009)、《阿凡达》(2009)等等,或因耸人听闻的噱头,或因光怪陆离的视听,或因反讽浓厚的比喻而引起观者的注意,但缺乏伟大的科幻电影所具备的、最核心的那种伸向灵魂的探触,因此只能被付诸一笔带过的篇幅。
不得不多提几笔的,是《星际迷航》(Star Trek)。
该科幻影视系列由美国派拉蒙制作,衍生出6部电视剧、1部动画片、13部电影的庞大分支;当然,还包括不计其数的同人作品。“星际迷航”的想法最初由编剧吉恩·罗登贝瑞(Gene Roddenberry)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经过近50年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完善,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幻影视系列之一。它描述了一个乐观的未来世界,人类同众多外星种族一道战胜疾病、种族差异、贫穷、偏执与战争,建立起一个星际联邦。随后一代又一代的舰长们又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探索银河系,寻找“新大陆”、发现新文明,勇敢地前往前人未至之境。天马行空的不拘一格、精密的世界观以及无微不至的人文主义关怀,使《星际迷航》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品之一。以今日的眼光再看几十年前的初代特效,确有“很傻很天真”的忍俊不禁。但是,《星际迷航》将勇闯无人区的勇气,勇气支配下着眼未来的三观,着眼未来三观指导下的豁达包容,用一个个近乎童话般的星球传奇故事完美中和,难怪让那么多的宅男/直男尽折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双峰》开启了一次别开生面、惊心动魄的另类序章。安静的小镇,美艳的女孩,年轻的探员,外来的力量,深渊的凝视……大卫·林奇照例用他那又妖异、又伤感、又调皮的招牌镜头,对准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死湖倒影,与潜伏在人性深处的暗黑与光明。有趣的是,在《双峰》中虽非主角,但表现不俗的David Duchovny,后出演《X档案》而大红大紫。在《X档案》里,原先《双峰》只是浅尝辄止(或者说因志不在此而点到为止)的命题,被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外星势力,异形生物,生化技术与政府阴谋,从未被呈现得如此生动而引人入胜。创作组利用新的美学范式,再现了超越日常生活和正常思维认知的恐怖、幻想及极端体验,并以此指涉当代人面临的困境和危险,表达了那些无法用传统话语和概念框架来作出圆满解释的,当代人所特有的焦虑。《X档案》“混搭”了理性和非理性、科学和宗教信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还成功地将现代性对真理的追求这一严肃的使命与后现代的调侃和讽刺相结合,试图给出针对当代社会机制与文化症结的“X答案”,因此让持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观点的观众皆获得了满足。
至于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异形》系列(1979年至今),实则是蕴含古希腊悲剧内核的“物种起源”、“现代启示录”和“创世记”。人类自以为是的星球殖民,带回了不可一世的外星孽种。地球人、仿生人、外星“泰坦族”、异形,环环相扣的叙事链条上,牵系着弑父的“沦丧”与“反抗”,及对“永垂不朽”的嘲弄。仿生人大卫在《异形:契约》(2017)里一边投掷“黑水毒弹”,一边吟诵雪莱《Ozymandias》的画面,足够点题:“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功业盖世,料天神大能者无可及)又怎样?最终,“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而今一切荡然无存。偌大的废墟,残骸四周只有那苍茫荒凉的戈壁)……
要说史诗,库布里克的神作《2001太空漫游》(1968)无人出其右。当黑石现身;当名垂影史的“星门九分钟”让四维空间的智慧动物顿生“一眼万年”的震撼;当完成了经历各种生命形态的旅程,“星孩”诞生;当大气磅礴的古典音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响起……没有其他的形容词了,就四个字:无与伦比。

而如果我们撇除掉对哲学层面思索的要求,便会发现,《火星任务》(2000)、《地心引力》(2013)、《星际穿越》(2014)、《火星救援》(2015)等硬科幻元素显著的影片,已经交出了关于探索宇宙、移民外星、“适者生存”的合格(甚至优良)成绩单。特别是《星际穿越》与《火星救援》,起初宣传的卖点之一就是“科学、专业”,诺兰的创作团队曾声称,《星际穿越》“基于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基普·索恩(Kip Stephen Thorne)的理论虫洞和时间旅行研究,经过合理演化之后,加入人物和相关情节改编而成”——索恩早在1997年便萌发了把“虫洞”拍摄成一部电影的想法,直接影响了当年推出的《超时空接触》(该片由朱迪·福斯特主演,《星际穿越》的男一号马修·麦康纳与她有对手戏)。此外,《星际穿越》中出现了三种飞船——徘徊者号、登陆号和耐力号,团队为此研究了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并参观了太空技术公司。其中,耐力号环形母舰由12个隔舱组成,转速为每分钟5次,以通过向心力产生1G的重力。通过气闸系统和弯曲连续的楼层连接,12个隔舱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四个发动机隔舱,四个永久性隔舱,以及包括生活区、驾驶舱、低温室与医学实验室和四个将被放在新行星表面的登陆舱。
飞船是工具,实现“登陆外星”后,如何生活自理才真正棘手。幸好,我们的马特·达蒙不负众望,从自我疗伤到自我“施肥”种土豆,就没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据悉,《火星救援》获得了NASA的全力支持,剧本有50页的内容全是有关NASA的细节,力求影院里的宇航员形象和行动符合实情。该片花絮还有:最开始的火星任务,正是NASA将来打算实施的;2015年9月28日,也就是影片在美国上映的四天前,NASA宣布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证据;原著小说作者Andy Weir是一名专业码农,他甚至编写了软件来精确计算从地球到火星的航行时间……“用积极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直面惨淡的人生”,《火星救援》非常符合美国院线的主流价值观,也是行文至此最“一本正经(又并不胡说八道)”的科幻电影。而根据好莱坞对“火星”题材的偏好,以及一大堆科学类纪录片絮絮叨叨的分析,未来,人类移民火星的“创意”,说不定还真成了。
时间探索:今昔大战穿越情
斯蒂芬·威廉·霍金,不久前离开了我们。
1963年,时年仅21岁的他患上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卢伽雷氏症),全身瘫痪,不能言语,手部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霍金并没有就此认命。1979至2009年,他任卢卡斯数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该书被译成40余种文字,出版逾1000余万册,但内容极其艰深,被戏称为“读不来的畅销书”(Unread Bestseller)。有学者曾指此书之所以引发坊间热议,盖因其尝试解答过去只有神学才能触及的题材:时间有没有开端,空间有没有边界。2001年,霍金的又一部著作《果壳中的宇宙》出版发行,该书堪称《时间简史》的姊妹篇,以相对简化的手法及大量图解,再次诉说宇宙的起点,介绍了广义相对论、量子论、黑洞、时间旅行、超引力等前沿概念,并探讨了预言未来的能力和星际旅行的可能性。
这位不乏(黑色)幽默感的科学家,曾放言: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人类不应主动寻找他们;地球或在几百年内毁灭,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他相信高维空间——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M理论,即超弦理论的一种,认为宇宙是十一维的,由振动的平面构成(而在爱因斯坦那里,宇宙就四维:三维空间,一维时间)。他也相信“时光机”——借助太空中的虫洞或速度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时间的挪移未必不可行。但是,霍金同时警告,千万不要搭时光机回溯历史,“只有疯狂的科学家,才会想要回到过去‘颠倒因果’。”
到了“祖母悖论”上场的时候了。假设穿越的你杀了自己的祖母,那么你是不可能出生的;既然你不可能出生,又怎么回到过去杀死祖母呢?编剧们为了扫除这个障碍,绞尽脑汁,不惜一再搬出“宿命论”与“环形结构”自圆其说。《十二猴子》(1995)、《时间机器》(2002)、《恐怖游轮》(2009)、《环形使者》(2012)尽管逻辑自洽的烧脑程度各有不同,结局也难用确凿无疑的“好/坏”下定义,但或多或少都向“宿命论”与“环形结构”的灵感借了光——要么,你不知不觉变成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因触犯众神被罚永无止境推巨石上山顶的科林斯国王)式的人物,作茧自缚;要么,你兑现了“将损害尽量减至最低”的闭环,死也瞑目。
同为莫比乌斯带循环谜题所扰,“一日囚”类型的《土拨鼠之日》(1993)与《忌日快乐》(2017)主线其实极度雷同——重新认识世界,与生活达成和解;后者犹如前者的性转版。这两部“以小见大”的片子告诉人们,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无法逃避,不若好好把握每一天,哪怕它不停地重复着。而一旦在“正确”的节点做了“正确”的事,“正确”的选择,搁浅的人生终将续航,驶向前方的蓝海。《源代码》(2011)的脑洞比《土拨鼠之日》《忌日快乐》更大,杰克·吉伦哈尔饰演的男主连“一日”都撑不了,只能被“困”在轮回往复的“特定8分钟”,直到破解现实里的死亡迷局。故事的最后,自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英雄抱得美人归。一般情况下,在此类电影中,编剧费劲折腾主人公之后,乐得留下一个美好的“尾巴”,作为对“时间囚徒胜利越狱”的犒赏,顺便安慰了期待“好人好事有好报”的善良观众。
将“逗比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的,当数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导演的《回到未来》三部曲(1985-1990)。从意外穿到1950年代,到引入平行宇宙,再到混战西部牛仔世界,跳跃时间轻松刺激,未来从不一成不变。喜剧意味十足的情节,因为“我的命运我做主”的主旨鼓舞了大银幕外的观众们。影迷对《回到未来》着实情真意切,以至于2015年10月21日(电影第二部中,少年Marty和博士Brown乘坐“时光车”从1985年到达未来的“降落日”)当天,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刷爆了社交网络的热点。
而纵观《时光倒流七十年》(1980)、《隔世情缘》(2001)、《本杰明·巴顿奇事》(2008)、《时间旅行者的妻子》(2009)等片,即使冠以“时间旅行”的外壳,也遮不住“罗曼蒂克”光彩焕发,辐射出强烈信号。在这些电影里,细究古与今,老与少,“正向与逆行”都是没有意义的,唯一有意义的,是真爱本身。爱是错身而过的惆怅叹息,是“非你不可,无你不欢”的情有独钟,是“芳华恰盛,执子之手”的一生一会,是“千百次相遇,千百次钟意”的地老天荒。爱,是撼动时间的能量,定格时间的魔法——爱,是最不可思议的“时光机”。
需要指出的是,纯然由原始的(野蛮的)“爱”所驱动,而做出的改变时间、不计后果的行为,非常遗憾,往往会弄巧成拙,遵循着墨菲定律(根本内容:凡可能出错的,有很大概率要出错),甚至带来灭顶之灾。看似能够挽回光阴、如愿以偿,秒杀“祖母悖论”的“平行宇宙”,是关于“时间探索”的迷人畅想,面前却横亘着“蝴蝶效应”这头拦路虎。
多元宇宙是一个理论上的无限个或有限个可能的宇宙的集合,包含一切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所有的空间、时间、物质、能量以及描述它们的物理定律和物理常数。多元宇宙所包含的各个宇宙即被称为平行宇宙。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科学家在观察量子的时候,发现每次观察的量子状态都不相同,鉴于宇宙空间的所有物质都由量子组成,所以这些科学家推测既然每个量子都有不同的状态,那么宇宙也有可能并不只是“唯一”,而是由多个类似的宇宙组成。有学者在描述平行宇宙时用了这样的比喻:它们可能处于同一空间体系,但时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在一条铁路线上疾驰的先后两列火车;亦有可能处于同一时间体系,但空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时行驶在立交桥上下两层通道中的小汽车。
“蝴蝶效应”呢,顾名思义,“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万事或皆有定数,万事或混沌莫测,是以,《黑洞频率》(2000)的“合家欢”太美式主旋律、太不真实;德国的《罗拉快跑》(1998)更像样些,至少揭示了“一处不同,即现岔道”的不稳定性。而《蝴蝶效应》系列(2004-2009)索性彻底撕下了希望温情的面纱,当主人公发现无论如何穿越,如何补救,如何衍生出新的平行宇宙,都无法阻止新的悲剧,简直万念俱灰——第一部的导演剪辑版里,男主穿回出生那一刻自杀,以期亲友跳出苦海,其惨烈决绝,未免令观众在感动之余,不禁反思:这“爱”的代价,委实过分高昂了。
就人类目前掌握的科技手段而言,超时空旅行仍然停留在“白日做梦”与“纸上谈兵”的阶段。也许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在宇宙中不那么茕茕独立,也许我们只是想看看被改变的历史能否书写不一样的篇章,也许没有也许——坦白讲,“也许”最高级的超时空艺术,并不源于工整方圆,反因无序的错乱铸就刻骨铭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