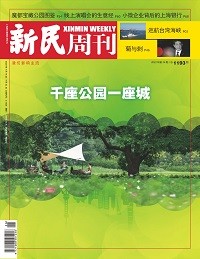古城长安文物修复师们的 “终极法则”
站在灯影绰约的城墙,登高望远,恍若听闻远处,三千万人吼叫秦腔;穿梭高耸而立的安定门,脚踩黄土,八百里秦川,千军万马驰骋而过。西安,这个在《史记》中被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古都,经历了周、秦、汉、唐建都于此,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庞大如大明宫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微小到一个瓦当、一件陶器,千百年光影缱绻,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
“千古绝唱”绵延至今,绝非凭空而来,而是仰仗着一个“智慧与手艺”并存的群体——文物修复师,从发掘出土到日夜打磨,呈至世人面前,倘若没点“少林武功”的真本事,拿捏起来总稍显钝拙。如肚中再墨水匮乏,又学着四川安岳峰门寺摩崖造像“反面教材”患了“美盲之症”,修复文物,便无所谓“敬不敬畏”,而成了商业化的亵渎了。
择一事,终一生,是古城长安文物修复师们的“终极法则”,作为全国2000名修复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正追赶着时代的车轮,以巧手、巧思,以本真、纯粹,重返历史画卷,无限接近与探索文物最初的面貌。

最原始的手工匠人
即便过了草长莺飞的季节,骊山脚下这片面积56.25平方千米的土地,也从来不缺游人,但凡慕名来西安,必定慕名来秦陵,距离市区37公里开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院,每天迎接数万人目睹这一帝陵奇观,而这里,有一个群体同样备受瞩目。
清晨7点半,兵马俑一号坑顶棚缓缓打开,坐标西南角的方位,上百平方米的区域聚集着17个修复匠人,他们埋头清理灰尘、研究拼对残片,一天的工作,从这里开始,那些沉睡在地下两千多年的近万尊兵马俑,也从这里“重获新生”。
“许多人认为,兵马俑出土时都是完好无损,这是错觉。”此话出自王东峰,秦始皇陵博物院兵马俑1号坑修复组组长,他自2002年开始从事修复工作,至今已整整16年。十六个春秋的日日夜夜,他与整个团队共修复完成了超过100件兵马俑。
而这100件兵马俑的修复,并非借助高科技的外力,大多是老实本分地靠着“一双手”来完成。这双手的功劳从第一步“文物发掘”便“功不可没”——用精巧的手术刀去除陶片泥土、用柔软的毛刷扫去残余灰尘,与大多数人想象的兴师动众的铲子不同,这是一双专业之手:动作轻柔,力道适中,熟谙门道。
每一尊秦俑“重见天日”,恰恰预示着漫长修复工作的开始。从数不清的样貌上无甚区别的残片堆中,把秦俑碎片一一分辨、编号、规整;“一个残片多的陶俑通常需要三到五个月才能修复成功。”王东峰说,大部分陶俑碎片都在七八十块,碎得最厉害的一个,多达180余块。清理、拼接、粘黏、加固、做色,看似稀松平常的“五步”走,对一名称职的修复师来说,却是极高的挑战,必须既是精通历史、绘画、文字的“大家”,又是钻研化学、物理、材料材质的“匠人”。

棘手之题,在1999年“百戏俑”的修复中得到解决——在秦陵后院的一幢办公楼内,寻着灯光径直走到底,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常年温度保持在26.4℃,湿度维持在37%,是秦俑“精品之精品”的冬季复原庇护所。
知天命之年的刘江卫,停下了伏案指导,扶了扶眼镜框,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1994年,25岁的资深修复师刘江卫进入1号坑参与发掘任务,从修复石铠甲到百戏俑,从用“化学去锈法”复活青铜水禽,到外援各州市博物馆,无数个第一次,成就了刘江卫“资深”的称谓。
修文物,也修心
从业24年,刘江卫没少开辟“蹚道儿”,带过的新人,逐渐成长为“中流砥柱”。如今的刘江卫,作为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专家、是公认的“名医”,帮全国各地进行陶质文物修复,以及相关技术指导、培训。经他修复的上千件汉代陶俑、陶马等珍贵文物,如今已经成为了青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今他手上正在修复的一批文物,来自河南焦作出土的陶仓楼。
业内人都知道,陶质彩绘文物共有19种病害,兵马俑就占到了18种,随意拿起桌上一张文物病变图,起翘、空鼓、龟裂、脱落、裂隙、硬结物、泥土附着物、生物病害等……图纸底部长长一溜标识,表面看起来相当“学术化”,但这个修复方案编制规范、病害分类与图示、修复档案记录规范,在刘江卫的钻研归纳下,已经成为了国家文物局认可的行业标准。
刘江卫的徒弟车彤俯首在工作台前,专注地用小手术刀、去离子水和脱脂棉签,一遍一遍地清理陶片表面的“病害”。而在此之前,绘制1:2的病变图和线图作为参照,就花费了她四天之久。刘江卫说,这个标准虽被业内认可,但因其费精力、费人力、更费脑力的特性,国内真正使用的人十分有限。都说文物修复是一件苦中作乐的事情,但,高标准苛求的“苦”,愿意尝的人,仍是少数。
即便少数,也不能抹灭它的价值,刘江卫明确的三大原则:最小干预、有效干预、可逆性,实实在在解决了文物修复的顽疾和漏洞。通过画出粘贴线和粘贴缝,大器物锚杆销钉的位置,方便后期二次修复;为了保有彩绘原貌,探索出30%抗皱剂和3%加固剂的最大化彩绘保护法;粘接时,使用德国进口的环氧树脂,从秦俑的足到头,分层进行粘接,旨在线条流畅,精神抖擞,反复可逆。
“文物修复,修复的不仅是物件,还有心理”,在刘江卫看来,秦俑如真人般大小,或身披铠甲,手持兵器;或腰束革带,腿扎裹鞋,看似千篇一律,其实每一个都有其“行为特征”,即便出自同一个工匠或小组之手,细小的偏差也依然存在。
正因为偏差细小,用高科技反而不如人眼识别来得真切,就算用上目前较为先进的三维扫描、虚拟修复,恐怕也无法真正扭转“全手工”为主的修复路径。去科技化、附着“匠人”特性的行业标准,令多数人开始反思文物修复的初衷。或许,机器或软件,无法掌控秦俑的“喜怒哀乐”,而人的手温,却可以。
绝不重建的“千宫之宫”
在西安市中心北部,一座面积3.7平方公里的大型文化遗址,则没有兵马俑般那么幸运,可以“重见天日”,上千座宫殿、数万计的文物经过岁月流转,或沉埋于地下,或风蚀于地表,留给后人的,是一处处断壁残垣。
艳红色的折扇、缎面的舞衣、清素的妆容,丹凤门后御道广场的百姓大舞台,从来都是西安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看上去像公园的地方,曾经耸立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
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皇宫,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2个克里姆林宫、15个白金汉宫。自唐高宗起,有17位大唐君主在此处理朝政,历时长达200余年。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湮没已久的秘密,也铭刻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忆。
47岁的李春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的发掘领队,从1996年“含元殿”的发掘开始,就坚守在大明宫,见证了它的拆迁、发掘、出土以及“不以重建为目的”的复原保护。22年过去了,性格本就沉稳的他,变得更具学者风范,温润柔和、一丝不苟,对于工作又几近苛求。穿过大明宫的红色木质长廊,进入考古探索中心最里面那间透明玻璃大厅,便是李春林和他的团队修复文物的场所。长长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大明宫出土的文物——陶器、瓷器、瓦当、花砖。出土于大明宫御厨房的这组瓷器,几小时前刚刚修复完毕,乍看,与广州美院油画大师谢楚余作品《陶》中的瓷器倒有几分相像,只不过,口子上多了碗形的器盖,根据封泥印戳文字判断,这组瓷器由浙江、宜昌、云南等地进贡,用于保存海产品、腌制鱼、茶饼之用。
修复完结的瓷器,青色质地原件与白色石膏的修复补片交错相间,补片“不上色”导致的色调反差,让人恍惚有了历史与现实的穿越感。“这就是修复起来的成品,我们不主张过多地后期加工,这是我们恪守的原则。”在李春林看来,文物修复的准则是宁愿在外貌上“失分”,也不愿靠着现代人的臆想,违背文物本来的风貌,而这一“去伪存真”的修复标准,小到生活器物、大到宫殿遗址,在大明宫的整个修复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伸与体现。
漫步在大明宫,没有想象中复建的宏伟宫殿、没有重塑的亭台楼阁,更没有依照历史“比葫芦画瓢”的现代建筑群,有的是多种遗址保护方式的探讨结合,如果你曾在史书中被这座屹立了220年之久的大明宫深深吸引,那么,随心走至任一处,都会发现,一砖一瓦渗透着对遗址保护的敬畏之心。
丹凤门遗址保护大厅,用轻钢材质搭建起的城门造型,宛若一个巨大的罩子,将遗址罩在里面,供游人参观;1996年发掘完毕的主殿含元殿,则采用对原来的夯土先裹层保护壳,再以青砖包砌的方法,1比1修复保护了殿基、墩台、龙尾道;而相比之下,宣政殿只是种了些树木,进行意象性的展示;紫宸殿也是树木和钢架搭建起的外式轮廓,给游人一个展示的空间。
这是遵从遗址原始面貌的创新文物修复方式,虽说广受好评,但对于李春林来说,仍有一些“未圆满”的遗憾。“我们可以通过对称性原则修复宫殿,却无法百分百还原(唐朝)地面以上架构的状况。”的确,古人建造宫殿,受制于物资匮乏、技术限制,连建筑地基也要投入成千上万人夯打而成,而今,如若用纯夯土,除了受制于昂贵的人力,还将面临极端天气、难以露天展示的挑战。
于是,考古队找到相近的三合土复原大殿及两旁连廊墙面,又尽量用特别的陶土复制铺砌龙尾道的花砖质感,纵然仿照它的规格、质地、色感重新打造,但用肉眼分辨,仍能在“真假”之间做出区分。
“古代制砖的陶土要经过筛选淘洗等复杂工序,这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而现代人早已没有这种耐心了。”以故宫金砖为例,不仅需要复杂提炼,还要加一些糯米汁,此外还要经渗炭磨光处理,才能保证烧制出又黑又亮的效果。李春林感叹,过去生产力虽低下,但在做工的细致程度上,现代人却难以比拟,如果大明宫有复原的可能,在工序上也应该遵从历史版本。
然而,大明宫遗址三分之二尚未发掘,即便想要“真实还原”,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考古队试图用立体实物展示手法来弥补这种遗憾。在大明宫东侧区域,依照考古成果和文献图纸复原了1:15的微缩景观,实景还原了全盛时期的整个唐大明宫宫殿群——站在高台之上,大明宫尽收眼底,南起丹凤门,北至玄武门,宫门,城门、官署省,庭院,大殿,大大小小房屋总共1151间。“千宫之宫”的美誉,借由修复师的“巧手巧思”,正从这里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是遗址,也是公园
如果你认为,大明宫的修复面貌就止于此,便是“不解其中风情”了。某时尚App上标记“大明宫”的游记超过600篇,大多普通游客会失望于未见雄伟宫殿群,扼腕叹息,大呼不值;相反,文物爱好者们则另有一番体悟——作家孟晖曾在《大明盛唐魂》一文中写道:“我无意间看到了这一片唐代遗迹最后一刻未受惊扰的样子,连绵的绿地与树木,在普通人看来,也许没有那么大的观赏价值,但令我肃然起敬。”
的确,大明宫遗址以“懂我之人无需多言”的修复姿态,有别于传统,它不拘泥于欣赏性的重建,更不单纯侧重原始的保护,却又与城市居民相融甚洽。以遗址展示、遗址保护、城市公园集于一身的“保护与利用”并存的修复模式,放眼全国,堪称首例。
从含元殿的修复路径看,80年代成立专门文物修复保护所;90年代二期保护启动,对两楼两阁进行系统修复;2000年,全面推行“不重建”的创新性修复举措。2000年以后,受国际遗址保护理念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和遗址保护激烈对冲,开始着手解决“如何让两者协调同步”的棘手问题。
当时,大明宫之上并非一片空地,而是大片棚户区和城中村交错的区域。大明宫保护办文物局局长吴春告诉《新民周刊》:民国时,大量黄河流域难民沿着陇海铁路逃难,直抵西安,见大明宫一带荒凉少人,便在此落脚生存。许多年过去了,由于遗址区内受制于“保护为上”,百姓不得大搞基础建设,一直过着没有自来水、网络、天然气的原始生活,与遗址外的世界明显脱节;而真正的遗址,也混迹于居民区中间,同样无法展露其应有的价值。在矛盾冲突下,西安市政府拿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在城市中心对这块将近3.7平方千米的大型遗址进行整体保护拆迁,并将上千户百姓妥善安置在了周边的崭新小区,连拆带建三年完成。
因拆迁而搬走的居民,并没有就此隔绝于这片神圣的遗址之外,他们仍然能够来这里继续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人生。每逢凉爽节气,到公园里晨练、散步、遛弯,少数爱好者还组成了舞蹈队、练剑队、歌唱队,定时定点聚集排练。
最令人感动的是,重建过程中,设计师专门保留了若干棚户区居民在自家门前种的树,如今它们在前朝广场原地生长,伴随着大明宫的朝阳与日落,摇曳起舞。一座城市的辉煌记忆,不该以牺牲普通人的生活为代价,文物修复也不该局限于修复本身,平衡好现代人与文物的关系,承认一切人都是文明的参与者,才是对历史最崇高的敬意。
而这个敬意,在大明宫文物修复的多样性上,愈发完美展现。在3.7平方千米的区域,36处遗存预留考古发掘区,等待着新的探索,在未来漫长的探索之前,他们大多以种植绿色植被的方式保护了下来。“大部分遗址裸露在地表,种植植被,可以抵抗外在侵蚀、雨水沉降对遗址的破坏。”

时间倒回到11年前,2007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园,这座盘踞龙首的大遗址备受世界瞩目,11年过去了,随着北城文化张力辐射,在遗址区形成了集遗址、考古、文物、书法、陶瓷、石碑为一体的博物馆矩阵,同样也是创新修复方式的体现。大明宫唐都新碑林馆长印建幸说:“今年,我们准备深入挖掘大明宫历史文化资源,并以唐代梅妃形象为主题,做出专属于大明宫的梅妃文化。”
如今,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大明宫考古探索中心、大明宫遗址博物馆、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四大国有博物馆并驾齐驱,八座博物馆星罗棋布,向世人讲述着保护大遗址、探秘考古学、传世文物精品、记录工业文明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