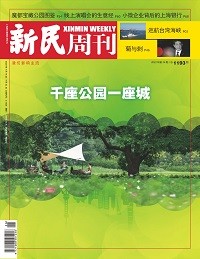石窟保护只能修复吗?
提起中国的石窟,你可能会第一时间反应到“四大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但你也许不知道,在新疆还有一个巨大的“龟兹石窟群”——阿艾石窟、苏巴什石窟、森木赛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台台儿石窟……伴随着群山连绵起伏。其中又以阿克苏市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保存最为完好,现存壁画多达1万平方米,因此又有“中国佛教文化摇篮”之称。
若再加以深究,克孜尔石窟还对中国著名的石窟有着重大的影响——这里从公元3世纪就开始建造的中心柱式“龟兹型窟”,显著影响了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乃至云冈中早期石窟的形制。
当“敦煌学”日渐深入人心,国际上对于“龟兹学”的研究也已如火如荼。究竟,这些龟兹石窟群里,还有多少文化宝藏有待挖掘?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瑰宝
早在1985年,新疆就已成立了专事石窟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龟兹研究院”。龟兹原是中国古代西域大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如今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所在地。
“克孜尔石窟”就坐落于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8公里处的渭干河河谷北岸,因为砂石呈赤红色而得名“克孜尔”(红色之意)。1961年,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又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上的一处重要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形制上看,克孜尔石窟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和多种洞窟组合形式,若干洞窟的组合即代表一座独立的寺庙。公元4世纪开始建造的“大像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者——这种开凿大像窟并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同类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了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地区。
而从遗存的超过1万平方米的壁画来看,克孜尔石窟又保存了丰富的3-8世纪中叶佛教故事画——壁画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释迦牟尼故事画为主。尤以“菱格画”这种特别的形式来表现本生和因缘故事100余种、佛传故事60多种。其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甚至超过了印度,见证了3-8世纪龟兹作为天山南麓佛教中心的盛况。
与敦煌、云冈等石窟相比,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还融合了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印度本土风格的秣菟罗艺术,显示出明显的西来影响印记。可以说,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群,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产物——无论从文化人类学,美术学还是历史学的角度,现存龟兹石窟的每一处历史遗迹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大丝绸之路历史人文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然而,自公元9世纪衰落以来,经历过1000多年的风吹日晒、大小地震、宗教战争和外来侵略,克孜尔石窟遭到的破坏也是非常巨大的。
2011年,当上海印刷集团商务数码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团队真正站到克孜尔石窟面前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的石窟群——部分石窟已经因为地震坍塌,石窟内的壁画有的被侵略者整片割走,有些被刮下壁画上镶嵌的金箔,佛头或毁于宗教倾轧,或已遭偷盗者毒手远渡重洋……
而上海商务数码团队此行,不只是领略龟兹石窟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带着一项前所未有的突破性任务——上海商务数码与龟兹研究院合作,对石窟壁画进行数字化的保护。
所谓数字化的保护,并不是仅仅拍摄数码影像,留下数字资料供后世研究,而是更加高精尖——他们要通过先进的三维扫描、平面采集和三维建模、3D打印等技术,对石窟进行立体化的数字复制和还原。
扫描、打印,乃至3D打印,这些在如今看来都是稀松平常的技术了,但是要对一个个形制独特、壁画色彩极其丰富的石窟“下手”,这还是全世界头一遭。
2011年,这个开拓性的创举,选择了第一个目标:克孜尔石窟第17窟。之所以选择17窟,一方面因为它的窟体与壁画保留相对比较完整,另一方面,窟区中又具有典型的龟兹艺术样式,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与人文欣赏价值。
17窟的主室平面方形,宽3.56米,进深3.61米,高3.62米,其后还有一个甬道,与主室两端相连,意寓“轮回”。甬道仅宽0.8米,高1.9米。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要架设起各种机器,对石窟造型及其中的壁画进行尽可能的高精度数据采集。
“第一步是三维扫描,首先掌握洞窟的结构,对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后续的采集方案。”团队骨干李嵩告诉《新民周刊》,“然后进行平面采集,洞窟的采集难度很大,因为几乎所有的立面都是弯曲不平的,拿洞窟的顶部造型来说,就有‘券顶’、‘穹顶’、‘覆斗顶’等等,不规则的形状,采集方法和难度也不同,为了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还要遮蔽透入石窟的太阳光线,再打上自己的标准光源。”

“因为天气和温度的影响,每年基本上只有5-10月可以在山里工作。”李嵩告诉记者,“近一点的石窟可能20分钟就能走到,远的就需要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能工作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花上七八个小时在石窟里,希望可以尽快完成更多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因为再不抓紧保护的话,后人可能就看不到这些宝贵的石窟了。”
从博物馆里走进洞窟
17窟的复制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2012年,在山西大同举办的国际壁画双年展上,商务数码带着他们和龟兹研究院合作保护石窟项目的第一个成果参展,一鸣惊人。
在青浦的中华印刷博物馆里,记者见到了这个当年参展震惊业界的“克孜尔17窟”——如果不是因为先推开的是现代办公楼的大门,你会以为自己就站在新疆克孜尔的石窟群里——打着手电,像往常探访山中石窟那样推开17窟的小门,主室与甬道赫然就在眼前。主室正中是一个空着的佛龛,佛像早已不知去向,两旁与券顶都有精美的壁画——你可以看到历经千年岁月洗礼留存下来的沧桑色彩,也可以窥见文物侵略者留下的满目疮痍——壁画上大块的无色面积,曾经是璀璨的金箔。
目睹这个数字还原的17窟之后,才理解什么是李嵩所说“超过95%的还原度”:壁画上有多处裂纹,有些裂纹深到仿佛会有碎石掉落,但伸手一摸,你会发现其实壁画完全是平面的,只是视觉上做到了十足的立体。有意思的是,团队将一些国外游客信手写下的涂鸦也一并复制还原了下来。
而在17窟的旁边,就是商务数码还原的第二个石窟:新1窟。新1窟开凿于公元7世纪,1973年才被克孜尔千佛洞文管所清理发现——此前一直被掩埋在山体中。一场大雨致使山体垮塌露出了新1窟,洞窟的主室虽然已经基本坍塌,后室却遗存完好,不仅有一幅巨大的飞天壁画,还保存有卧佛塑像,“塑绘”结合,表现佛陀涅槃情景。泥塑造像明显具有印度芨多时期“薄衣透体”的特点,为龟兹石窟所仅存;顶部飞天造型苍劲雄厚,又融汇了犍陀罗艺术之遗风。留意观看,你会发现17窟的右甬道外侧侧面,有一幅壁画下方写着:得到了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支持——此壁画正是失而复得,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授权复制归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掀起了西域探险热潮,来自英、法、俄等国的探险队,先后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探险活动,这些探险队或多或少都从这里带走了壁画。其中又以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揭取的壁画最多。因此,目前海外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大部分都保存在德国,其次是俄罗斯。
龟兹研究院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流失在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人员先后赴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和韩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调查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2012年,龟兹研究院和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2016年,龟兹研究院又启动了和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合作。
经过20年长期艰苦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最多的这两家博物馆的支持下,研究院现已收集到海外8个国家20余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的462幅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高清图片。今年7月18日,由新疆龟兹研究院主办,木木美术馆承办,上海印刷集团商务数码公司协办的“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展”,在北京798艺术中心启动。
影像展上不仅展出了由商务数码1:1仿真复原的克孜尔14窟、38窟,还有137幅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高清摄影图片。
“这个影像展还将去往全国十地进行巡展。《海外克孜尔洞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集》也快要出版了。”《新民周刊》记者从上海商务数码了解到,“影像集里收集了大量流失海外的壁画作品,经过龟兹研究院的反复核对和测量,大部分壁画都已经找到了其所出洞窟与被切割的位置。”

尽管仿真还原的“克孜尔14窟”正在北京展出,但是身处上海,记者依然通过虚拟手段“走进”了这座洞窟——这就是商务数码的第二步创举:用VR数字影像复原洞窟。
在参观1:1实景还原的“克孜尔新1窟”时,记者见到了用3D打印技术还原的两尊佛像——佛头已遭破坏,两尊佛身,也是克孜尔石窟群所仅存。为了尽可能逼真地还原佛像,2013年商务数码耗资100多万元采购了当时最先进的民用彩色3D打印机——不仅机器贵,耗材也以克来计费——每尊佛像均由高科技纳米粉末一层一层打印堆叠而成,每一层的厚度仅仅0.01毫米,两尊佛像的材料费就要数十万元。

巨大的还原成本必然会限制克孜尔石窟未来的大规模保护和还原,VR由此被提上议程——在普通办公室里划定一个正方形的小区域,戴上专用的VR眼镜之后,记者仿佛就站在了克孜尔石窟群面前。左右手各持一个手柄,记者走进了“克孜尔14窟”,左手的手柄可以充当手电筒的作用,照亮洞窟区域,欣赏精美壁画;右手的手柄则可以触发壁画的相应位置,点击按钮之后,壁画旁边就会垂下一方卷帘,帘上是对壁画故事的介绍。就这样,VR的出现让1:1还原的成本都省了,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克孜尔石窟。
从一开始的摸索探讨,到如今的日渐成熟,李嵩和同事们一道也已经为洞窟的数字化采集研发了一个完整流程和不少辅助设备,从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现在已经变成一体化的操作系统——从照明、调试到采集,从地面一直到6米高,在电脑的控制下,一切都可以一气呵成。因为出色的成果和创新的技术,2017年,李嵩作为团队中的代表还被授予“上海工匠”称号,1987年出生的他,在平均年龄46岁的上海工匠中显得非常年轻。
时至今日,商务数码已经完成了9个洞窟的数据采集。在同时接受记者采访的亲历者看来,这是传统大企业跟上时代技术发展的必经之路:“新时代的出版印刷不仅仅为文化发展起到辅助作用,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新兴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