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一辈子的《红楼梦》
特约记者|张 英
在201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王蒙的新书《王蒙陪读〈红楼梦〉》亮相。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是王蒙“评点红楼梦”的第四个版本。此次新的“陪读”版,采用一百二十回足本“程甲本”为底本,集合了王蒙多年读《红楼梦》的感悟。
评论家李敬泽说,“王蒙点评《红楼梦》最合适。200多年来,要论文人懂世事、明白人情,除了曹雪芹就是王蒙。由王蒙来陪读《红楼梦》,让我们了解中国的人情、世事,中国人的心。他陪读、批注《红楼梦》,就是厉害,不用别人去打,自己先打起来了,自己左右手互搏,一口气出四版,每版都不一样,得对着读,才能看出每一版新加了什么,为什么要加这些,很有意思。”
中午饭吃到一半,“扔掉”刘心武等朋友,王蒙就离席了——得去泳池喽。86岁的高龄,依然精力充沛,条理清楚,幽默机智,做事风风火火,神采飞扬。时光流逝,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今年第一期《上海文学》杂志,在小说头条发表了王蒙的《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两则短篇;他还新写了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生死恋》——这三篇的主题都是爱情。此外,他在各种报刊上继续发表文章,表达对世界和社会的看法。
文学创作以外的时间,是“传经布道”。除了完成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工作,去年王蒙跑了十几个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宁波、青岛等地,做了十几次有关传统文化和读书类的演讲。也旅行国外多地,如古巴、巴西、智利,坐邮轮游览了意大利与希腊。
平时在家,他每天坚持游泳、走路,在微信头像上晒健身成果,笑称自己是“耄耋腹肌男”;看新闻、影视,还玩微博、刷微信,偶尔也看看视频,在喜马拉雅开起了讲读孔孟老庄的音频节目,对新生事物不仅有好奇心,年轻人流行的时髦爱好一样不差。

《红楼梦》常读常新
张英:这个版本的《王蒙陪读〈红楼梦〉》,与之前你点评的三个版本有什么不同?
王蒙:这是我出的“王蒙点评《红楼梦》”的第四个版本。在聂震宁先生的策划下,我1995年就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评点《红楼梦》,后来又在上海文艺、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其它版本。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王蒙陪读〈红楼梦〉》,采用一百二十回足本“程甲本”为底本,由红学家冯统一先生点校。我这一版的点评,集合了多年评点《红楼梦》的心得、体会。每一版,我都会新增一部分内容,这次也不例外。
我读了一辈子《红楼梦》,还是痴迷其中,仍然常读常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你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都能找到参照,找到解释,找到依托,也找到心心相印的共振。
《红楼梦》是小说,但对于我来说是真实、原生、近乎全息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你可能并不熟悉,作者的的描写、情节、故事、伟大、精细、深沉、华美、天才能取信于你,让你完全相信它的生动、深刻、立体、活泼、动感,可触可摸,可赞可叹,可惜可哀,可评可说。
这二十五年来,四个版本的“点评《红楼梦》”系列,它们不是重复、补充的关系,而是共存的关系。每一个版本点评的侧重点不同,这一次评点的感觉与之前的都不一样,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越深,对《红楼梦》的理解也就越读越深,越读越有乐趣。原来的点评内容基本上没动,这次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张英:这一版的《红楼梦》,是86岁的王蒙的点评,如果说是“常读常新”,新在何处呢?
王蒙:我举个例子,贾宝玉为什么那么痛恨科举考试和功名利禄?厌恶读书上进、做官,讨厌修齐治平,而且一听这个就发火。他的反应太过了,一个人赞成一件事儿可以表现得很热烈,不赞成的事情一声不吭就完了,也没必要鸡飞狗跳的。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贾宝玉那种一谈起功名利禄流露出的伤害感,那种绝望感、痛苦感,不管是十二钗里谁劝他,他都是发疯一样,咬牙切齿地仇恨。那不是一个孩子爱不爱念书所造成的,只能问他的上一代,前世,去找原因。
贾宝玉的激烈反应,表现了一种被伤害的感情,而这种被伤害的感情,是当年女娲补天时留下的。一提读书、做官、为朝廷效力,其实是扎到了贾宝玉最疼的地方。女娲补天时,有36501块石头,但只需要36500块。那这“多余”的石头就非常悲哀,惭愧,孤独失落。其它石头都补天了,成了天地间重要的角色,唯独它运气不好,被抛弃、被遗忘,失去了使命,也没有存在的意义。
封建帝国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读书人,想有一官半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必须进入社会管理体制,成为朝廷系统的一员。贾宝玉前生是“补不了天”的石头,所以痛恨补天的向往,不愿意追逐名利当官求职,这是他性格形成的先天原因。
一僧一道给了他机会下凡尘,到贾府体会人生的荣华富贵,才子佳人,爱情亲情,晚景凄凉、衣食不保最后又变成石头,回到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石头上记载了一生的经历和故事,就是《石头记》。
《红楼梦》是小说,又是哲学和玄学,写法奇特。小说也好,戏剧也好,都靠悬念,渴望知道后事如何,“原来如此”。《红楼梦》不在乎这个,一上来就先把结局告诉你:我写的这些,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张英:对你而言,几十年读《红楼梦》,乐趣在哪里?
王蒙:我把《红楼梦》当作一部活书来读,当作活人来评,当作真实事件来分析,当作经验学问来思索。从《红楼梦》中发现了人生,发现了爱情、政治、人际关系、天理人欲的诸多秘密。
每次读《红楼梦》,就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新体会、新解释。
以自己人生的经验去理解《红楼梦》的经验,验证、补充启迪自己的经验,你的人生便无比地丰富了,鲜活了。
这些年,我不光评点《红楼梦》,我还到处演讲读《红楼梦》,上电视台开课讲《红楼梦》,我甚至公开说,为《红楼梦》布道,做推广者,死而后已。
你对什么有兴趣?社会政治?三教九流?宫廷豪门?佛道巫神?男女私情?同性异性?风俗文化?吃喝玩乐?诗词歌赋?蝇营狗苟?孝悌忠信?虚无飘渺?那就谈《红楼梦》吧,里头什么都有。
比如里头的魔幻故事,非常好看。第一层是女娲,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第二层写天宫,说贾宝玉原来是神瑛侍者,林黛玉原来是绛珠仙草。天旱了,神瑛侍者每天给绛珠仙草浇水。神瑛侍者到了人间以后,绛珠仙草要报恩,跟着下凡用自己的眼泪来回报贾宝玉,眼泪就是神瑛侍者给它浇的水。第三层是警幻仙子,专门给贾宝玉讲男女之情的,讲情天恨海的种种故事。
另外,《红楼梦》的特点是留下了太多的空白,一道道填空题,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前赴后继,几百年里不同时代的人,用记忆力、联想力、想象力,直至侦探推理的能力,去解读《红楼梦》。
清朝就有人读《红楼梦》得精神病,整天惦记林黛玉,整天惦记晴雯、芳官等等,家里人就把《红楼梦》烧了,他在那儿抢天呼地的:为什么烧了我的林黛玉?为什么烧了我的晴雯?不吃不喝,最后就死了。1977年,一对青年男女感情不顺,看了越剧《红楼梦》,很难过,最后双双殉情。

(王蒙曾经做客山东卫视《新杏坛》,谈传统文化与家国梦。)
《红楼梦》为什么伟大
张英:普通读者爱《红楼梦》,主要是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你看重什么呢?
王蒙:《红楼梦》不光是讲爱情,它更多表达了人生的本体,宇宙的本体。
从物质层面来说,宇宙也好,人生也好,都是由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所构成的。中国传统说法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红楼梦》没有具体写金木水火土,它写到了阴阳,写到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写到了世界的消长变化,写到了世界的永久性。
它写人的生老病死、聚散离合、吉凶祸福、兴衰荣辱、善恶曲直、是非功过,写尽了人性的角落。作者没有道德价值判断,没有歌颂与谴责。
中国文学的传统是“教化”,文学作品里体现的是二元对立,君子和小人,忠臣与奸臣,黑白分明。《红楼梦》不是,它更多的是冷静的描述,容许你有多种的价值判断。我们读的是小说,但我们感受到的人生命运的沧桑,甚至超过了实际生活。
张英:《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吗?
王蒙:当然,那么多赫赫有名的文人墨客,连毛主席这样的政治家都喜欢《红楼梦》,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喜欢看小说,原因就两条,一是文学性,一是人生性。文学性包括作者才华、作品风格等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有人生性,也都具有文学性,文学性离不开人生。
但有一类作品,能让你感觉到它描述的是活生生的人生,是充满血泪又充满美好事物的人生,以至于你会忘记了它是一部小说,忘记了它是一个作家写出来的,而就像面对真实的生活一样。
《红楼梦》就是这样伟大的小说。它好像是自然主义,零零碎碎、鸡毛蒜皮、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但它把汉语汉字汉文学的可能性用尽了,把我们的文化写完了,所以有人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它能够给人一种人生的悲凉感、荒谬感和罪恶感。开始,作者先宣布书里的人物已经死亡、消失,再讲述石头上所载故事,从头到尾不断提醒读者,现实世界是虚无的,是转瞬即逝的,一切美貌都会消失,一切青春都会淹没,一切富贵都会无影无踪。所以鲁迅先生说《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小说的文体也很有意思,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像一粒种子,发芽,长出枝杈,长出叶子,开出花来。各种矛盾、问题、任务,每一种关系,都有无穷的可能性。一夜没见,又开出一朵花来,又一夜没见,又长出一个枝杈来,自然天成,这样的书非常少。
《红楼梦》中的描写方法与现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是相通的,例如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 《红楼梦》中可以称为“仙幻现实主义”。除此之外,在书中也可以解读出悲喜剧、结构主义、空间与时间、符号与寄托等多层意义。
《红楼梦》在颓废、屈辱、罪恶的感觉之外,又有温暖的爱恋,亲和。不管讲多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小说的核心还是一个“情”字,难分难舍,比生死还要强烈。贾宝玉体验了那么多爱和愁,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他,那么高纯度的情感体验,就是只活二十几岁也是值得的。人生有种种焦虑和悲哀,但是你到世界上走这一趟,值。
从艺术性上讲,《红楼梦》超越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道德教化为剪裁标准的观念。在《红楼梦》里,善和恶、美和丑,兽性和人性乃至佛性,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它什么都写尽了,没有回避任何东西。到现在为止,这样的小说,中国文学作品里,只有《红楼梦》。
张英: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里,为什么唯独《红楼梦》研究成为了最火最热的显学?从普通人到学者,全民都为之痴迷?
王蒙:文学的力量在于把生命的状态揭示出来,揭示人生的本质,《红楼梦》什么都有,耐得起解读。
对《红楼梦》的解读和议论,已经超出了《红楼梦》的文学范围。各种社会、人生、哲学、科学、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宗教,甚至政治的解读,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流派,用这些方法、流派分析《红楼梦》都有收获,都行。
比如现实主义,《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而贾宝玉要求个性解放,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分析完全讲得通;魔幻现实主义在《红楼梦》里也有,又是和尚、道士、太虚幻境、青埂峰无稽崖、神瑛侍者、绛珠仙子,又是出生的时候嘴里含着玉,这儿一个钗,那儿一个麒麟。
《红楼梦》的信息太丰富,留下的空白又太多,它诱使读者千方百计去探究,推理扑朔迷离,结论花样百出。
比如,“索隐学派”把《红楼梦》当密电码来分析,其一些说法我不敢苟同,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里的符号太丰富了,导致对《红楼梦》的考据与索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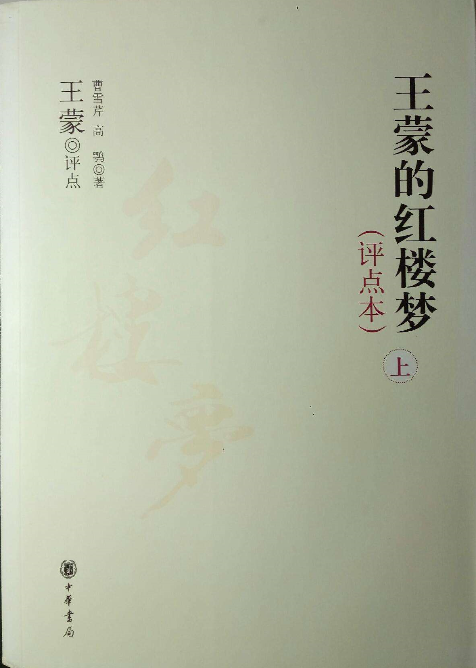
(不同版本的“王蒙评点《红楼梦》”,应该也能给读者带来“常读常新”之感。)
我最喜欢《红楼梦》程乙本
张英:你曾经建议出版社把《红楼梦》改名为《石头记》,为什么?
王蒙:不同的时代,《红楼梦》有不同的名字。我认为最好的书名是《石头记》,这方面我曾与作家宗璞讨论,我们两个的意见一致。我建议,今后出版社再印此书(指供大众阅读的长篇小说,不是指专门的某某版本),干脆用《石头记》做书名。
与《石头记》相比,《红楼梦》还是露了一点,俗了一点。《石头记》,直击宇宙,连通宝玉,登高望远,又具体而微,与小说的核心道具,宝玉脖子上挂着的那块“通灵宝玉”息息相关。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令人欷嘘感叹,多少滋味,尽在不言中。
张英:众多《红楼梦》的不同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
王蒙:我最喜欢的还是最普通的版本,程乙的。因为它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了,其它的版本没有。一般读书人看得有兴趣了,哪怕他看过《红楼梦》三遍五遍,想要往深里研究,行,那就得去看不太一样的版本了。
我一本看的是程乙本,一本看的是庚辰本,一本看的是列藏本,还有列宁格勒的那个版本。但我读下来,看不出区别——列藏本没有后40回,只有前80回,就这一点区别。一般的读者,谁在乎是哪个版本呢?
张英:你怎么看待,那些指责后四十回是他人代笔、续写的理由?
王蒙:我觉得书是没有办法续的,不但没办法给别人续,自己续也没办法。把你以前写的小说再续写一章,不要说十章二十章,你再续写一节试一试,没得写,不可能的,尤其《红楼梦》这本书,更是没办法写。
到现在为止,批评、指责后四十回的种种理论,还没有能够完全说服我。我想来想去,高鹗的续作还是最佳的,尽管是带来遗憾的续作。如果现在弄一个博士,牛津大学或北京大学毕业的来续作,那更可怕。
我没有考据学的工夫,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学问,我宁愿相信曹雪芹,他是有一些断稿残篇,而高鹗呢,作了一种高级编辑的工作,这个比较能够让人相信。如果说这就是高鹗续作,而且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这是我的常识所不能接受的。
现在供研究的材料非常少,各种说法非常多,并且越来越多。研究者你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材料,你找不着更切实的材料。文本没有,档案没有,前人著述没有,没得可挖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张英:我看您意思是对这些研究隔岸观火啊,不表态。
王蒙:对于这些,我只能在旁边看热闹,当个吃瓜群众。对《红楼梦》我只限于大众版的版本研究,只审美和鉴赏。然后对各种研究者的发现,各种结论,表示理解。
张英:为什么《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后,在西方受到的是冷遇?
王蒙:我认为还是翻译的问题。《红楼梦》的内容太丰富了,有文化差异有阅读门槛,不是那么容易被转换的。《红楼梦》有各种文字的译本,翻译后的《红楼梦》,没有了原汁原味。
有一次我到新西兰,《红楼梦》的一个译者,送我一本他翻译的版本,我一看王夫人全部是lady Wang,贾母完全是lady Shi ,贾政说 “ladies and gentlemen”,味道就全变了。文化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不可通约性。
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游记》,东南亚比较容易接受《三国演义》,认为《三国演义》能够启发明智。
为什么没有人文院士
张英:你是政协委员,前些年曾经提议建立文化事业领域的荣誉体系和褒奖体系,这个提案有结果吗?
王蒙:这是我在文化部的时候,就提了的。荣誉称号的体系指的是,比如“人民艺术家”或者“人文院士”,像苏联过去还有“功勋艺术家”、“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体系,现在朝鲜还有这样的体系,相当于科学家里头的院士。褒奖体系指,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奖励这些文化上有独特贡献的人。比如说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是由天皇颁发的,大江健三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被补发了芥川奖,不过大江健表示“我得奖和你没关系,我拒绝接受”。
英国有一个皇家学会的评价体系,法国有一个法兰西院士各国情况不一样,但基本上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类似的评价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张英:为什么非常困难?文艺界多年提出设立“人文院士”,表彰中国文艺界的杰出贡献者,但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王蒙:据我所知,设立这个体系,要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又要征求一些相关部门的意见。全国总工会很自然地提出:我们劳动英雄、劳动模范这个体系没有,只给文化人发奖不可以;全国妇联提出,我们现在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些都搞得不正规,我们需要有妇女的褒奖体系。这么一来,文化褒奖体系猴年马月才能够实行啊。
另外,没有这个评价体系,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的人文学术研究和贡献缺少信心。我们人文不应该急功近利,而应该跟着学术、学识走。学术、学识是稳定的,你不要今天把一个人捧到高得不得了,过几年又认为错了。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中国人首先做价值判断,而非认知判断。什么意思呢?不去探究本身到底什么情况,先说是好还是坏,是拥护还是反对,就是先站队先表态。我们不太注重真伪,但是我们注重好坏,善恶,爱憎分明。可爱憎分明,有一个前提,就是辨析真伪啊。
现在学术上的腐败,也非常严重。
张英:中国社科院几年前设立了学部委员,地位据说相当于中科院的院士。
王蒙:它必须是工作关系和编制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现在是不管社科院系统外的,所以不具备全国性和代表性。因为如果一牵扯到外面的,就又麻烦了,比如北京大学的学术很叫座,你为什么没有选进来?它的评价体系和评选结果,也不一定最理想。
什么时候我们把人文学术和现实操作拉开一点距离,可能就会做得更好一点。
鲁迅讲过,中国人的特点是这样,远远看见一个匾额,几个人没有看清楚上头题的什么字,但已经开始争了。这个人说题得好,那个人说题得坏,争得头破血流。至今依然有这个问题,做事情,不去把标准、规矩弄好,让评选成为好事,最后往往变成“目的和动机都是好的,结果坏事了”。

(2015年9月29日,王蒙(中)凭借《这边风景》首获矛盾文学奖。)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热
张英:对传统文化复兴热,你很冷静,却忧心忡忡于这种趋势,为什么?
王蒙:感觉等于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进步给取消了。《三字经》和《弟子规》里有一些非现代的东西,只讲尊敬长上,把你培养成特别听话的人,但是它不讲青少年有什么权利,不讲长上对青少年的基本需要和诉求,应该有所尊重。
我最反对它这个“勤有功、戏无益”,就是不可以玩的,你只有勤劳才行,如果玩了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了,这剥夺了青少年的乐趣和创造性。再比如说,《弟子规》里头甚至讲到,如果长上对你不满意,即使是打了你、骂了你,你只能够服从不能够反抗,这些东西太前现代了,二十四孝的倒退就更不用说。
鲁迅当年痛心疾首,什么为了孝顺母亲把儿子活埋,什么儿子用自己的肉去喂蚊子,免得咬父母,这种荒唐残酷的观点,现在居然被宣扬,一直到要求小学生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张英:现在恐怕不只是学生了,还体现在经济生活里,企业管理里。更荒诞的是,竟连情感咨询和教育领域,也在讲究“三从四德”。
王蒙:这个其实很简单,据说很多企业家发现了《弟子规》之后,如获至宝,然后要求全体员工先把《弟子规》背下来,以此作为一种管理的手段。它没有威权,只有管理,就是一个青年人,或者一个孩子,你必须老老实实,听大人话,听上级领导的话,接受管理,听从指挥和命令。强调这个,从管理人的角度来看,儒家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
张英:因此,也要警惕传统文化里的糟粕垃圾。
王蒙:这是传统文化的力量。还有人提出来要把“孝”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
所以我有机会就讲邓小平的那三句话: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
张英:你还提到,不要轻易改动全国统一高考。
王蒙:全国统一高考可能有大家觉得不公平的地方,但如果让每个学校单独招生,或许要出现更多的不公平。不能到最后变成也许拼的不是成绩,是拼爹妈,拼背景,那就太糟糕了。
所以,不要改动全国统一高考,除非有更公平、更合理的办法。

(2018年8月24日,王蒙亮相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加“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中外对话会。)
每天走8600步
张英:你身体太好了,像您这样精力旺盛的老作家,不多。不过美国的厄普代克、史蒂芬·金到八九十还在写长篇小说。
王蒙:徐怀中最近完成了长篇小说《牵风记》。他比我大,90岁的人了。最近,冯骥才有一篇不太长的小说,写天津义和团的事。他比我小8岁,76岁,也算年龄比较大了,但他是篮球运动员出身。
张英:说说你的退休生活吧。
王蒙:我现在每天游泳,走路,注意比过去稍微少喝点酒。
体重130斤,身体还算行。走路小步快走,迈大步我没有那个力道,平均每天是8600步。今年我有意识地减少,给自己规定的标准是一天7000步。我必须每天中午以前走5000步,因为没有这5000步的底子,你一天到不了7000步。但是如果碰上来客人了你要送送啊,或者是上商店买东西,那就超过7000步了。像我昨天、前天都过了9000步了。当然,雾霾太严重的时候,我不敢出去走,一看一天只有几百步。
张英:我看您生活很放松,现在出门旅游还坐邮轮啊。
王蒙:坐邮轮慢慢旅行,二十来天的样子,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坐邮轮是这样,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对象,有时候它可以连走20多个小时,因为邮轮上玩的花样太多了。
那些年龄大的欧洲人,每年坐一次,在邮轮上定一个房间——就是想熟悉这个房间,变成自己家一样。有时候根本不下船,就看看海,看看鸟。
他们把晚年安排得很好,钱就该用来干这个,不然要钱干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