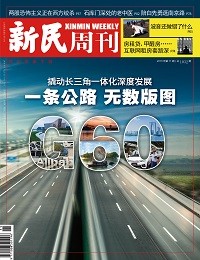白先勇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阳春三月,天气晴和,陪伴82岁的白先勇走在南京路的街头,这场景既新鲜又陌生。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从七重天到新世界,还有茂昌眼镜、亨达利钟表,“小时候都来过,没想到它们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在王开照相馆,幼年的他曾拍过一张照片,“当时在王开拍照片,老吃价(稀罕)额,因为王开是顶顶好额照相馆!”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却始终未变,他依旧还记得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当时安装了第一部自动扶梯,“家人抱着我去坐,感觉好新鲜!”
如今,往事又浮现眼前,南京路依旧霓虹闪烁,熙熙攘攘,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的白先勇,眼底有一丝留恋与欢喜,“上海还是那么美,那么有情调。”站在曾经熟悉的故土,身穿灰色风衣的他,双手插在大衣口袋中,翩然独立,拍下了一张照片。“阿是有点老克勒?”他笑着调侃道。
白先勇与上海有缘,无论是幼年时的短暂居住时期,对南京路、淮海路、百乐门等处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最终用尹雪艳、金大班等人物,写入了自己的小说代表作《台北人》中;还是少不更事的时候,因缘际会听到一段梅兰芳、俞振飞演出的《游园惊梦》,最终有了自己之后几十年的小说、戏剧与昆曲间的不解之缘;还有时隔39年后再度来到上海的所见所闻……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戏剧再精彩曲折,又怎及人生际遇的万分之一?直到今天,耄耋之年的他,依旧对上海有着深深的眷恋,喜欢住在老锦江,也爱去儿时生活之地走一走看一看,还有不少上海文化界的好朋友,更爱吃精致入味的上海菜……只要有机会来上海,他一定不错过,在这里,有值得享受的友情,更有值得怀恋的往昔。“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上海对我的影响,我对上海的感情,都是很不一样的!”

上海情缘
《新民周刊》:白老师,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的语言能力特别强,几十年来,不仅一口道地的桂林乡音难改,还会流利的广东话,在美国则完全用英文教授外国学生《中国小说史》……可没想到您一口上海话也说得如此流利,听来老派且亲切。
白先勇:洋泾浜,洋泾浜!哈哈哈!其实我只是会几句,毕竟小时候在上海生活过一个阶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的一生,在很多地方漂泊过,所以到了哪里就学哪里的话。直至今日,人家问起我的家乡究竟是哪里,我也说不清,但我知道,我的家乡,我的根,是中国文化。
《新民周刊》:在我印象里,您童年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却在今后的写作与生活中,留下了很深刻的烙印。特别是对上海的摩登、现代与光怪陆离的现实,之后都一一写进了《台北人》中。
白先勇:的确。我们全家来到上海是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过来。那是我第一次来上海,简直看傻眼了!我们家在上海很多地方住过,最早在虹口的多伦路,我的父亲母亲与兄弟姐妹们都住在那里。后来我得了肺病,与家人隔离,住在虹桥的一幢房子里,内心非常脆弱与落寞。记得那时候,虹桥还是一片农田,非常偏远。39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大陆,还曾去过那里,依旧比较荒凉。可今天,虹桥已经是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地方了。今夕何夕,叫人感慨系之。1987年,我第一次重回上海,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窗外望去是黑压压的一片,几乎没什么灯光,和我印象里的上海,似乎并不一样。可当时我就有预感,总有一天,上海这座长江流域的“龙头”一定会起飞,到时候一定会不得了!到了今天,果然!
《新民周刊》:提起您在上海的足迹,可能最有名的就是汾阳路上的那幢漂亮的小洋房了,直到今天,它还被亲切地称为“白公馆”。
白先勇:这个说来有趣了!当时那条路不叫汾阳路,叫毕勋路,我在离它不远的南洋模范小学读书。说是“白公馆”,其实我父母一天都没在那里住过!哈哈!那是我住的地方,我父母一直住虹口的。后来我了解到,它做过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部,之后又给了上海越剧院。我的印象里,花园里有个很大的喷水池,上面还有个很漂亮的雕塑。87年我回去看的时候水池还在,雕塑没了。再后来池塘也没有了。不知道现在那里怎样了……
《新民周刊》:往事依依,令人唏嘘。据我所知,您还在“白公馆”请客过呢!
白先勇:太巧了!第一次请客就请到了自己家里。那是我离开上海的前几天,复旦大学的陆士清教授告诉我,上海昆剧团在演全本《长生殿》,问我要不要看。我一听,立刻跳了起来!没想到时隔那么多年,还有昆曲可以听!我第一次看昆曲,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八年后首次复出,在美琪大戏院,与俞振飞先生演昆曲《游园惊梦》。那次真是轰动极了,美琪以前是从不演戏曲的,只放电影和演舞蹈、话剧,但那次梅先生复出,全上海为之疯狂,一张戏票黑市炒到一根小金条。你想想,还了得么?我家正好有两张票,我母亲就带我去看了。奇了怪了,那时候根本听不懂看不懂,但是《游园》的“皂罗袍”曲调一起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就一下子把我的心揪住了,至今为止,我始终觉得,“皂罗袍”就是我的“心曲”,呵呵!所以你想想,那么多年后还能听到梦寐以求的“水磨调”,我该有多么激动!那次上昆真是演得好极了,谢幕时我一个人站起来拍手,直到曲终人散还激动不已。所以就约了蔡正仁、华文漪等主演小聚,越聊越投机,我就起意做东吃饭。那时候没有什么饭店的,最后兜兜转转去了越剧院的“三产”——越友餐厅。我一看,这下好了,请客请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也太戏剧性了。那天晚上很难忘,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错觉,但这一感觉我只留给了自己,没有告诉上昆的朋友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都知道这是我曾经的家,只是谁也没有点穿。

文艺复兴
毋庸置疑,白先勇是当代最富盛名的华文文学家。但这十几年来,他却把最大的关注投入到了昆曲艺术之中。于昆曲,白先勇有一生难忘的情缘,小时候在心中埋下的种子,历经岁月更迭,走过天南海北,最终生根、发芽,开出了一朵别样绚丽的花。从2004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到2009年的新版《玉簪记》,乃至近年推出的新版《白罗衫》与《义侠记》……昆曲宛如白先勇的青春梦,伴随着他走过自己的晚晴岁月。
曾经,作为好友的章诒和劝过他,不要为了昆曲而放下自己的写作。在章看来,能拥有白先勇那般优雅文字与叙事能力的作家,并不多见,若因昆曲耽误写作,实在是一种遗憾。可这些年来,每次两位老友相见,看见白先勇青春焕发的面容,如数家珍的神采,连章诒和也不禁感叹:“举止谦恭,内心坚韧。做一件,成一件,没他办不成的事,因为他是白先勇!”如今,章诒和再也不劝老友“回归写作”了,因为在她看来,白先勇不仅在昆曲中焕发了青春,更将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之梦,寄托在昆曲艺术之上。
《新民周刊》:对于昆曲艺术,除了从小而来的缘分,还有怎样的情感,使您为之醉心不已,奔走多年依旧无怨无悔?
白先勇:昆曲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世界级的艺术,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我多次说过,昆曲艺术是以“美”的形式来表现我们中国人最深刻的“情”。可以说,昆曲是明清两朝我们中国最高的文化成就之一,也是中国所有表演艺术成就最高的。它的每一次演出,就和我们展示青铜器、展示汝窑、宋画、唐诗、宋词……它们文化价值和意义都是一样的。多年来看昆曲,我与许多当代大家都成了好朋友。可就在上世纪90年代,我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艺术家们渐渐老去,观众、演员青黄不接,这样下去,昆曲的传承是会出现问题的!我很着急,于是起心动念要为这门我毕生热爱的艺术做点什么。
因缘巧合,我认识了苏州昆剧院一群年轻的刚毕业的“小兰花班”的演员们,看了他们的表演,我感觉他们是一块璞玉,值得好好打磨。于是我选择了昆曲最有名的《牡丹亭》,试图做一个“青春版”,以青年演员,培养青年观众,同时也唤回古老昆曲艺术的青春。回顾十几年前的这一决定,当时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险阻,演员、经费、场地、演出安排、票房收入、社会反响,甚至演员之间的关系,老师傅们来跨团教学的障碍,等等,数不胜数。所幸我们成功了,那么多年下来,青春版《牡丹亭》走进大江南北的一流剧院,走进海峡两岸的高等学府,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其中经历的困难曲折,不计其数,但很奇怪,每次都会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看走不下去了,又得到贵人相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新民周刊》:在制作每一部昆曲的过程中,您都强调遵循昆曲艺术的特点与精神,结合时代,打造“昆剧新美学”。
白先勇:对。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守旧。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目的是要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所以,对于老艺术家们最精湛的表演艺术,我要求青年演员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地传承下来。昆曲是口传心授的艺术,昆曲表演人才实际上是很少的,应该珍惜这些老艺术家,趁着他们能教的时候,赶紧学下来。幸好我和这些老艺术家有点老交情。不过,十几年下来,这点交情大概也快用完了,哈哈哈!
《新民周刊》:有了扎实的传承,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创新与完善。我总觉得,传统万岁,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则可以加一岁。一岁与万岁,天壤之别,却始终有其价值与意义,积少成多,必能换来昆曲艺术的新生。
白先勇:的确。我们制作昆曲的原则就是这样,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剧目做更多完善,每当我们在制作一个戏的时候,都希望在原来的基础上给它一个新的诠释,我们是根据传统文本来改编的,在传统的基础上怎么让它赋予新的意义,这个很要紧。现在的道德观、视觉美学等都不一样了,我们这些戏都是要引起21世纪,尤其青年观众共鸣的。
《新民周刊》:值得欣慰的是,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昆曲艺术已经不再孤芳自赏,而成为全民族的美学标杆。十余年来的普及推广,昆曲艺术真正迎来了新生。在这其中,青春版《牡丹亭》自然功不可没。或许这不是艺术性最高的《牡丹亭》,却绝对是影响最大,观者最多的一个版本。
白先勇:我就是一个“昆曲大义工”。其实,昆曲不光有我,更需要很多很多义工。说好听点,这是文化使命感,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么闯入了本来不属于我的世界,哈哈!与昆曲紧紧捆绑近20年的时间,我想,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布道者”,无论在哪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讲,昆曲有多美,直到大家相信我。很高兴,现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乃至美国伯克利大学等,都开设了昆曲欣赏课程。我们的青春版《牡丹亭》还有了“校园版”传承,北京16家高校的大学生们,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居然可以有板有眼地演出青春版《牡丹亭》了!这让我很感动,老一辈艺术家教苏昆年轻演员,现在这班年轻演员再去教大学里的学生,这不就是传承吗?
《新民周刊》:在您的晚年,从昆曲到《红楼梦》,您始终以个人之力传播普及最美的民族文化艺术瑰宝。您曾和我说过,希望能在21世纪,迎来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
白先勇:对!无论《红楼梦》还是昆曲,这是我们民族最美的瑰宝。我已经是82岁高龄了,其实早该退休,但对于民族的文化艺术,我有一种不舍。我更希望在21世纪,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我们能迎来一次属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以昆曲和《红楼梦》为切入点,如果能做成,相信不久的将来,文学、艺术、哲学……都会迎来繁荣兴盛,我个人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