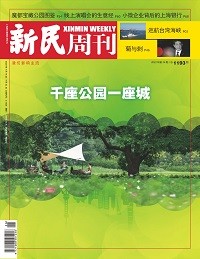抓拍的那一瞬间
口述|崔益军 整理|郑正恕
崔益军:(1952年--),江苏东台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1972年参军入伍,曾任团、师、军宣传、新闻干事。1986年转业,先后任《解放日报》摄影记者、《申江服务导报》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2000年,荣获“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2001年被中国文联评为全国百名“德艺双馨”文艺家之一。有近百幅摄影作品在国内外各种摄影展览、比赛中获奖,其中作品《憧憬》《希望之声》《握手言和》分获第十六届、第十九届全国影展、上海市第五届国际影展、1999年上海市摄影艺术展金、银、铜奖。《瞬间》获1990年全国摄影比赛一等奖。《大凉山里的孩子》获1999年全国新闻摄影展年赛银奖。《邓小平与江泽民在一起》被美联社评为20世纪百幅新闻照片之一。《城市变迁》系列照片30幅,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1992年至今,出版摄影画册《名家明星留真》《院士写真》《大凉山的孩子》《百名校长风采》《震殇5.12》《崔益军人物新闻摄影谈》《上海人家》《教育人生》《城市与人》等。1996年至今,举办了《院士风采》、《大凉山的孩子》《走近西部》《震殇5.12》《孩子,我们是一家人》《底色上海》等摄影展。
1988年,我抓拍小平同志在上海过年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调进上海解放日报社摄影部工作。那时,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摄影记者。
1988年2月16日,即那年农历除夕上午,我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二楼电梯出口附近,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我所尊敬的小平同志拍摄了一幅照片。这是一幅抓拍的照片,后取名《步调一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我摄影生涯中最值得珍贵的作品。
记得那天是1988年2月9日。当时,摄影部主任对我说:“小崔,快到三楼会议室去开个会,报社领导有重要任务交给你。”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惊呆了!时任报社领导——七位正副总编辑齐刷刷地端坐在会议桌旁,又很一致地看着我,而我则一下子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了。
报社领导告诉我,近日有重要中央领导同志要来上海出席有关活动,报社派你去拍照,而且一定要确保完成任务。同时还告知,为落实这次采访报道任务,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厅等都要分别召开会议,布置任务,你都要代表报社出席会议,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果然,我又去参加了两次会议。这样,连报社领导会议在内,为了这次拍摄,我一共参加了三次会议,这在我的新闻拍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市里的两次会议上,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驻沪机构及上海各主流媒体,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那时,新闻界还是很活跃的,大家都在猜到底是哪位中央领导同志要来上海过年。不过,猜也八九不离十了。大家都渴望是小平同志能来上海过年,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为拍摄工作做准备。我一直在想两件事,一是我该怎样装备自己,二是我该如何去拍。当时,报社只发黑白胶卷,这个老规矩几十年都没有改变过。但是,我决定自己掏钱去买一卷柯达彩色胶卷,我要背两架相机进去,多一些装备总不会错。装备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该如何去拍。我一头扎进了上海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报纸与画册,主要就是看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刊发的我国领导人出席各种会议和各类活动的照片。我发现,这类照片因受题材和场地限制,大多数领导同志的照片都是他本人在鼓掌或与其他来宾握手等。我能否有点突破,我暗暗鼓励自己,我一定要设法做到。
1988年2月16日,我背着两架相机,搭乘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陈念云的轿车,和他一起来到了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这个会堂位于上海展览中心北侧的南京西路上,会堂对面就是现在的波特曼大酒店。展览中心是原苏联设计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作品,应当说即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仍是属于那种金碧辉煌的大手笔。所谓二楼会议厅,实际上就是一座剧场。我走进会场立刻扫描了全场:座位分列两侧,中间铺有一条大红地毯,一直连到舞台中央。整个剧场,就像英文大写的“T”字。“一横”是舞台,“一竖”为红地毯。在靠近舞台前几排座位上,标有摄影记者的专用座位,我立刻抢占了一个较为靠前的位置,等待着中央领导同志的来临。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堂里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上海市各级领导、各界人士、中央驻沪各级机构代表,还有外国领事馆馆员等都纷纷来到会场。新华社驻上海分社首席摄影记者来了,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来了,上海主流媒体的摄像师、摄影家们都来了。这些摄影高手名家挤在一块,我这个进报社才一年多的“新兵蛋子”快要给他们“淹没”了。我再次察看了我所占有的机位,确定了我所能拍到的视角范围,心里明白了——即使我拍好了,拍到位了,最多也就和大家一样,其最终结果就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领导鼓掌或挥手致意的片子。那一刻,一种强烈的冲动感几乎掀翻了当时的我自己。我作了一个近乎可怕的决定:离开摄影席位,寻找新的机会,一定要拍出和别的摄影记者不一样的片子。
人生能有几回“搏”?我背起了两架相机,“突围”走出了摄影记者席。我走到了红地毯上,在众目睽睽下,踩着红地毯慢慢地朝前走去。也许是部队的锻炼,也许是军人的形象,造就了我那一刻的气质。我觉得自己很自然、很放松、很镇定。我微笑地走着,还不时向一些陌生脸庞点点头。凭着军人的感觉,我知道一些保安人员开始在注意到我了,但我越自然,他们就越吃不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好在我脖子上套有“新闻采访证”,当我走完红地毯,走出剧场,走到二楼大厅时,我一眼就看到了电梯门。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最新最好的机位。我打开了相机,屏住了呼吸,我想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那一刻,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都无法回想起来了。只记得,那时的“我”好像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紧张的等待,兴奋的企盼,还有就是一直回响在自己耳旁的那句话:稳住,稳住,一定要稳住……
果然,电梯指示灯开始闪亮起来,一层、二层……电梯停了,电梯门打开了,小平同志稳健地从电梯里含笑走出,跟随在他身后的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同志。他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步子,跟上了小平同志的节奏,步调一致地走过来了。我低下身去,用最快的速度调整好焦距,立刻按下了快门:一张、两张、三张……我边退边按,一连拍了六七张彩色胶卷。这时,我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剧场,重新站到了红地毯上。因为,剧场里爆发出热烈响亮而又持久的掌声。小平同志来到了上海人民中间,上海农历除夕开始过大年了,上海沸腾了,上海的春天来临了!
当然,我也回到了摄影专席位置上。我举起了装有黑白胶卷的相机,和我的同行们一起激动而努力地拍摄着:拍小平同志的满脸笑容,拍他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拍他走上舞台和大家一起握手合影。当小平同志与大家联欢会见面结束后,我又被总编辑陈念云拉上了轿车。在赶回报社的路上,他连声说:小崔,你好大胆,我都替你捏把汗啊!而我突然发现自己棉袄背心里的衬衫全都湿了。
从1988年起,小平同志一连八个年头,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而我有幸能在小平同志来上海过第一个春节时,为他老人家拍下那张与众不同的照片——《步调一致》,这是我摄影生涯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张作品。
那天,我大步流星地奔回报社摄影部暗房。不知怎的,心又开始咚咚地猛烈跳起。我要把彩色与黑白的胶卷都冲洗出来,那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似乎变得那么漫长。在灯光下察看胶卷,手都是颤抖的。还好,每一张胶片都是清晰的,这至少说明我的聚焦与曝光都没有问题。但心还悬在了半空。这是小平同志来上海与大家一起过大年的照片啊,片子放大后,小平同志的笑容被拍得如何,这才是成败的关键。我用镊子夹住照片,不停地在洗印药水中轻轻地晃动着。慢慢地、慢慢地露出了他的身躯,露出了他的脸庞,露出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平易近人的笑容和挂嘴角上的那一丝坚毅与刚强。
当照片在定印药水中安静地定格下来时,我悬到嗓子口的心终于放下了。同时,暗房里的电话铃响了。夜班编辑部主任悠悠地问道:照片好了吗?还加了一句:新华社的文字稿和照片都已经到了。我太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就是说我拿出的照片,如果没有入夜班编辑们的法眼,那么,新华社的照片已经等在那里了。我精选了五六张照片,并把我在电梯口拍到的那张彩色照片放到了最上面,又冲锋似的从摄影部奔到夜班编辑部,果然,满屋的名编都在等着看我拍到的照片。
解放日报时任夜班编辑部主任贾安坤对我笑笑说:小崔,照片放在桌上吧!我放了上去,颤巍巍地问:可以吗?他瞧了一眼,说:你先回吧。我感到背脊上一阵冰冷,默默推开夜班编辑部的门,默默回到摄影部办公室,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知道解放日报社的规矩,记者无权干涉夜班编辑部的用稿权。正值大年夜,应该是回家去吃年夜饭的时间了。我推开窗户,发现除夕夜晚的天空中竟飘起了雪花。我决定不回家了,我要在报社等待明天农历新年的到来,我要在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照片发在解放日报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上。那年的春晚毛阿敏第一次亮相,唱起了《思念》。我也在“思念”我的作品明天能否见报。半夜两点,我走进了印报车间,说是还在装版。凌晨四点再去,说刚装上版子,马上就要开印了。清晨六点,我第三次走进印报车间,一眼就看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啊,登出来啦!我拍的小平同志在上海过年的照片,在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上刊发出来了!当年,解放日报发行量接近100万份,这一张张印有小平照片的报纸顷刻之间就会走进千家万户,上海人民在看到报纸的那一刻都会明白:小平同志来了,上海真闹猛!
1988年的农历初一,霁雪已停,天空放晴。我迎着暖洋洋的冬日,回家过年啰!
这张照片,被许多报纸与媒体转载过,我也因为这张照片的成功获得了殊誉。其实,现在看来,那是机会难得,碰巧给我遇上了。1989年9月,《民主与法制》杂志封面用了这幅彩色作品。报社领导还接到来电,要求放5幅20英寸的彩照,装框送至北京。此幅照片被美联社评为20世纪百幅新闻照片之一,也是中国唯一入选的作品。我把这些都看成是对我的鞭策,摄影记者没有停步的时刻,一旦他(她)不按动快门了,其摄影生涯也往往走到头了。
和艺术家们做朋友才能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
《步调一致》的成功,为我今后的摄影打开了一条创新之路。摄影成功往往是一瞬间的,但这“一瞬间”背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纸媒对记者的工作安排是分条线的。我拍了《步调一致》后,报社领导就安排我跑文艺这条线,那可是许多摄影记者梦寐以求的美差。因为,上海的文化活动多,文艺演出多,文化与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就更多。因此,拿到这个条线,就摄影记者而言就会出片子多、见报率高、产生影响也大,我当然乐意接受这个任务。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我几乎拍遍了沪上文化、文艺各界的名流。如作家巴金、王安忆、程乃珊;剧作家于伶、柯灵、张骏祥。大导演有黄佐临、汤晓丹、谢晋、吴贻弓;电影演员就更多啦,有白杨、秦怡、黄宗英、孙道临、刘琼、牛犇、于飞、舒适、程之、陈述、仲星火、向梅、潘虹等。还有话剧演员焦晃,配音演员乔奇、乔榛、张欢等。音乐界有贺绿汀、周小燕、朱逢博、廖昌永,作曲界有朱践耳、叶小纲,指挥家陈燮阳、曹鹏等。戏曲界与美术界也是一大叠:京昆名家于振飞、尚长荣、李炳淑,越剧界有一代宗师袁雪芬、尹桂芳,沪剧界则有邵滨孙、马莉莉、茅善玉。还有滑稽大师周柏春、著名演员杨华生、王双庆、童双春、严顺开、王汝刚等。唱评弹的有余红仙,说书先生吴君玉。至于美术界,我拍到了刘海粟、朱屺瞻、唐云、程十发、谢稚柳、陈逸飞、张乐平等等。我用自己不断的努力,拍摄到了改革开放后上海文化、文艺界的众多“腕儿”,其中大量照片频频亮相于解放日报等各种主流媒体,量大面广,影响甚广。
拍人物,特别是拍文艺界的名媛名人,选择舞台拍摄的很多。我也多次尝试过,但总感到自己拍出的片子与其他摄影家相比,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而矣。我是摄影记者,更是新闻工作者,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舞台人物摄影上。布列松说过:人都有各自决定性的一瞬间。我要的就是最能打动我并通过我的拍摄能打动广大读者的那一瞬间。于是,我离开了舞台,试着和他们交朋友,走近他们,走进他们的生活,去发现、挖掘、抓住那“决定性的一瞬间”。臂如,我和秦怡老师交上了朋友,她请我上她家去玩。当我看到她是那样慈爱那么专心致志地为她患有智障的儿子洗头时,我拍下了这个镜头。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眼眶都有点湿润了,“决定性的瞬间”应该是这样砺练出来的。记得秦怡老师有一回挺认真地对我说:我的照片太多了,只有那张替儿子洗头的我喜欢,你拍的!
我拍上海文化与文艺界人士的那段经历,对我的摄影创新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那一段的经历与锻炼,我才敢向报社领导提出:我要拍中科院108位在上海工作的院士。
拍了中科院108位在上海工作的院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巡视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中国震惊了,世界注目了。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最美好的年代,中国开始讲述着“春天的故事”。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唯科技强盛,中国才会强大,人民才会富裕!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在某次采访中,意外听到中国科学院在沪有100多位院士,他们在上海工作,他们都是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领军人物,或者说他们在某些科技领域中或者在某个攻关项目上都是独树一帜的翘楚!我当时心里怦然一动,能不能拍摄他们——中国科技界的泰斗们!那天,我有意无意地问一些颇有学识的人,听说上海有100多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答复:没有。我再问:什么叫院士?回答:哦,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只知道有护士。
那晚,我敲响了报社领导办公室的门。当我向他表明,我准备去拍上海1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不愿再跑文艺这条线时,他从一大堆稿件中抬起头来摘下了老花眼镜,眯着眼睛对我说:你可要想好啰,文艺这条线是别人抢也抢不到的!我说我想好了,我愿意改跑科技这条线,我要去拍那些科技界精英们。老领导很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我支持你。科技兴邦,科技富民啊!从那天起,我就从纯文艺舞台拍摄中退了出来,我要去找中科院在沪工作的院士们,他们成了我今后一阶段必需去全力以赴拍摄的主人。
拍摄院士们,一开始,这件事还真有点难。他们太忙,忙出差、忙开会、忙讲课、忙带研究生和博士生,当然,还忙着立课题、报项目、申请科研费用等等。因此,我听到最多的托辞就是某院士又出差了,或者还在开会。更有某科研所办公室同志直言相告,老专家对采访、拍照之类没一点兴趣,他们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专题科研攻关上。难度在哪里?难点如何破解?这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个个都像陈景润。
当然,我也不能退缩,有时干脆直奔科研所而去。汪猷,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他是当年“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大生物学顶尖科研项目的掌控人。当我探听到他就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时,就直接奔了过去。办公室小秘书经不住我的死缠硬磨,胆战心惊地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天哪,这不就是一个小而乱的书房吗?他的桌上、椅上、身背后的橱里堆满了书,走道、窗台、门背后又是一大堆一大堆书本与资料。他压根没怎么抬眼看我,轻轻地说:“来啦,辛苦啊,你拍吧!”说话时,他把头深深地埋进书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而从缝隙中折射出的目光,却在大堆资料中来回扫描着,顽强而执着。我拿出了相机,静静地等候着,希望他能在抬头向外望一眼的时候,按下我的快门。一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而他的眼光一直紧紧地行走在字里行间。多么严谨的学者,多么顽强攀登高峰的科学家啊。我还要等下去吗?我还有机会吗?我慢慢沿着书桌,悄悄地走到了汪猷院长书桌的一侧,终于拍下了他全神贯注细读资料的那一瞬间。就汪老而言,这是再也平常不过的状态了。但对我言,却记录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上海籍科学家在世界生物学前沿领域中的顽强拼搏的状态。当我把照片交到报社领导手中时,时任夜班副总编辑的吴谷平连声拍案叫绝。他说,开个“院士风采”专栏吧,争取都上一版版面。科学家——国之瑰宝啊!
在上海籍院士办公室、书房或实验室里,我拍到的中科院院士还有核物理学家朱鹤绂、船舶工程专家杨槱、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植物生理学家沈允钢、通讯工程学家张熙、光学专家庄松林,等等。他们大抵都在埋头读书,或者守在实验室仪器旁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自己的显微镜或者光学仪。也有例外的,我走进有机化学家陈庆云的办公室时,他已累得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而神经生物学家杨雄里则对着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慢慢地说:你来了,我可以放松一下了。随着这些“工作照”不断地在解放日报上的刊登,沪上各大科研机构、高等学府也越来越重视“院士风采”这个栏目,我的拍摄也渐入佳境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要改变我的拍片方式了。科学家不仅仅是只钻在书堆里的书生,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一定能拍出更生动更真实的片子来,这才是我崔益军所要追求的。
一天上午,我来到了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叶叔华的办公室。这时,正好同行的媒体摄影记者也在采访她。记者请她端坐在书桌前,请她提起笔,翻着书,微笑地看着镜头……我在一旁看着,总觉得叶教授感到别扭,我也更感到别扭。我不喜欢布置别人让自己摆拍,特别是我所敬重的中科院院士们。所以,轮到我拍时,我第一次大胆地对叶叔华专家说:叶教授,我能上您家里去玩玩吗?还真没想到,叶教授竟爽爽快快地一口答应了。她说:我这样坐着也挺别扭的,到家里轻松点,随便你拍。
中午时分,叶教授可以回家小歇一会儿,她特意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也一起拉回家。走进叶叔华的家,她先生也在,也是一位学术有成的教授,正忙着煮饭呐。叶教授就住在普通的石库门房间里,没有独立的书房,客厅一隅放有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她爱人看到有客人来了,忙着去找椅子。叶叔华坐的藤椅已经很破旧了,扶手柄上还绑着绳子。老先生找到了一把转椅,想把上面的灰尘弹弹干净,一不小心又把转椅上的坐垫给弄翻了。当他们夫妇俩尴尬地笑着连声对我说抱歉时,我已经把这最动人的一瞬间拍下来了。中国的院士们是最兢业的,在学术上都有着惊世的丰硕成果,他们住在上海这座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中,生活却是相当清贫的。今天,我拍到了,拍到了这张真实记录叶叔华家境的照片。同时,还听到了叶教授的一声叹息,她说:家里坏了的东西实在没时间修。
和叶叔华一样,上海籍院士们都有相似的处境与感慨,但他们却乐于奉献,甘于清贫。我拍到了干福熹院士在老式工房楼梯上的缓步攀登,我拍到了瑞金医院终身教授、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骑着“老坦克”自行车下班,我拍到了生物化学家王应睐步履匆匆地挤上公交车上班,许多读者都被院士们平凡生活的细节所深深打动。直到我拍摄到的周勤之院士从自己三层阁楼里弯腰爬下来的照片见报时,连这位我国机械制造工艺设备专家所在单位的领导们都坐不住了。他们当天赶到报社,一再说明单位正在建造工房,一旦有了房源,第一批肯定分给周院士。
我在拍摄院士的过程中,也尽情享受着摄影给我带来的快乐。我和叶可明院士一起爬上高高的脚手架,拍摄他研究土木工程力学结构时的那份庄重,我和孙敬良院士一起钻进火箭推进器内部,拍摄他检查内部结构时的一丝不苟。当然,他们一旦回到家里,就是一位普通的市民:物理化学家邓景发系上围兜,能做出一桌好菜;而船舶设计专家许学彦在家,其一大乐趣就是追着孙子为他拍点照片。
当然,也有拒绝采访的院士,陆熙炎院士就是。他倒不一定对媒体抱有什么成见,主要是没时间,嫌拍照浪费时间。后来,我从他同事嘴里得知,陆院士就是喜欢每天早晨在公园里打打太极拳,其它就别无爱好了。我想,行,我就拍你打太极拳。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公园。我躲在树丛中,经人指点,找到了正在认真打拳的陆熙炎。当我托人把照片送到陆院士面前时,听说他大大表扬了我一番,说:这个记者好,像我们搞科研的人一样,既执着,又有办法。唯如此,攻关才能成功。后来,我调离了解放日报社,到《申江服务导报》去当摄影部主任了,我拍中国科学院上海籍108位院士的采访任务也告一段落。
总结拍108位中科院院士的心路历程,就是要心怀敬仰地去拍,要一丝不苟地去捕捉。因为我拍摄的对象,都是国家的栋梁,我就知道了我肩上的分量。就拍摄技巧而言,我决不安于一般的工作摆拍,我要让他们处于自然状态中,而所有的背景交代,又要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一句话,要有所追求,有所创新!
我一直在摄影创新之路上探索奔跑着。先后17次来到大凉山地区,为拍摄大凉山的孩子们、为催生希望小学的诞生,拍摄了大量照片,先后出版了《大凉山的孩子们》等数本摄影画册,在国内外摄影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还把目光集中在上海城市改建上,所拍摄的《上海人事》为留住石库门文化,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崔益军不是在摄影,就是在去摄影的路上。
摄影有起点,却遥无终点。我愿在创新探索的路上,去捕捉更多“决定性的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