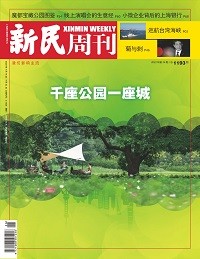龚建华: 一有空就背着相机走街串巷
口述|龚建华 整理|王岚
从兴趣到开始有主题的创作
1971年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吴淞口东海舰队当兵,准备行李时,我把父亲的一架苏制相机放进了行李中,可以说从小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到了部队,我总喜欢拿出照相机给战友们拍点留影照。那时候还没有创作的概念,就是喜欢而已。1975年复员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客车厂工会,专职搞宣传,主要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会议场景、文艺演出等等。工会给了我一个很宽广的舞台,让我有了发挥文艺特长的机会。我的父母亲都是南下干部,父亲是上海文化广场的第一任负责人。文化广场的前身是跑狗场,上海解放后成为第一个公共文化的聚集地。我的家就在文化广场边上,推开窗就能看到里面各种演出,大型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之春》、苏联的《天鹅湖》等等,每场必看,可以说是从小耳濡目染。在上海客车厂,黄永生、俞晓夫和我是当时厂里的风云人物,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多年后,黄永生成了家喻户晓的滑稽名家,俞晓夫成了著名画家,现在是上海美协副会长。因为爱好,我参加了卢湾区工人俱乐部和文化宫的摄影小组,学到了许多摄影技巧。我还在家里搭了一个暗房,和两个兄弟一起想筹钱买一架属于自己的照相机。那时大多数人的工资只有36元,而我们看中的照相机要169元,是外婆圆了我的梦,她拿出私房钱给我们,就这样我拥有了第一部照相机——凤凰205。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调到《音像世界》杂志社做摄影记者和传媒编辑,任职期间,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攻读“摄影理论学”,积累了丰富的摄影艺、技术理论和实践经验。那时本职工作主要就是采访中外歌星,在一般人眼里,这份工作既体面又风光,大陆的刘欢、韦唯、毛阿敏等当时风头正健,台湾的童安格、齐秦、齐豫、小虎队以及香港的张国荣、刘德华、谭咏麟、张明敏等等,凡是到上海的各地歌星,我几乎拍了个遍,有的到现在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杂志是月刊,每星期只要去一次,一个月只要发一次稿就算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了,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拍我想拍的内容了。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一有空就背着照相机走街串巷。
其实,自70年代末起,我就开始关注“上海弄堂之人文、社会、历史文化”与“石库门建筑艺术”,悉心钻研上海弄堂建筑与人文社会历史的特点、变迁与发展。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将诸多真实宝贵的原始艺术和影像资料留在了自己的摄影作品中,用一些摄影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既具有高度的艺术欣赏价值,又成为已永远逝去不可复制的宝贵历史社会遗产”。确实,现在相当一部分石库门弄堂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已不复存在,但我的镜头里永远有他们的影子。
镜头对准普通老百姓
1977到1978年,我在上海市卢湾区工人俱乐部摄影组学习,到过祖国的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去采访,起初,也没有什么主题,看到什么、觉得什么好就拍什么,但是走的地方越多,越是觉得身边的景色不能忽略,我开始关注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上海弄堂进入了我的视野,成为我摄影的第一个主题。
《七十二家房客》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那时,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上海一日”摄影赛,邀请了全国一百多位摄影家,在7月1日党的生日那一天,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拍摄,拍摄主题则由抽签决定。我当时抽到的主题,有徐家汇地铁开挖、凌晨出生的第一个婴儿、残联主席张海迪、出入境管理所、上海弄堂等等。那一天,我真的是从凌晨拍到半夜。7月1日凌晨,我在中山医院拍到了上海第一个出生的婴儿,之后赶到徐家汇地铁工地,拍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然后来到北京路贵州路口的一条弄堂,当时大概是上午八点左右,弄堂里已是人声鼎沸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口做事:有在水斗里淘米洗菜的,有摆个小方凳做作业的,有怀抱小孩“嘎三胡”的,甚至有给小孩洗澡的……最壮观的是几乎所有人家都把洗衣机搬到弄堂里,因为当时不仅住房面积小,而且没有下水道。我向弄堂口一户人家借了个台子,站到上面,对好奇地朝我看的居民们说,你们就做你们的事情吧,不要管我怎么拍,不要影响你们的生活。居民们都慢慢恢复了常态,我一口气拍了十多张,获得“日本Olympus国际摄影大赛”特别奖的《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其中的一张。2017年1月,美国弗吉尼亚博物馆收藏了我50张上海老弄堂的照片,《七十二家房客》也在其中。也是2017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我,我就带他们来到了这条弄堂,正巧碰到一位老妈妈在洗碗,她说怎么又来拍啦。我说是呀,30年前我就来拍过。老妈妈端详了我一会儿说,对,我女儿还保存着这张照片呐。于是我们又进到她家里拍。现在不仅她家里,而且整条弄堂里都已经没有马桶了,家家户户都可以在家里洗澡洗衣服了,弄堂还是那条弄堂,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但除了老年人,其他几乎都是外来租客了。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5000多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遍布上海滩,作为上海基层居民生活的象征——弄堂,正在逐渐地隐退,伴随着弄堂文化各种生动丰富有趣的生活现象,也在青年一代的视野中逐渐消失。美国作家、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就有一段关于美国大城市街头邻居都相互熟悉的描写。摄影大师们镜头中的弄堂,邻居之间如家人般的生活景观,让我们不禁留恋和憧憬城市中,普通市民之间的亲切和信任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在于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柔和的和充满人情味的。我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拍摄的大量具有上海风情的照片,真实细腻地还原了上海街区和弄堂文化的变迁,每次开摄影展,看到观众们驻足在照片前细细观摩,我都很欣慰。
我拍上海弄堂和弄堂里的人,并不是拍了就过去了,而是经常会和被拍者保持良好的互动,不间断地持续拍摄,我希望从弄堂的变迁和被拍者的人生变化,来反映社会的进步。1995年秋天,我受朋友之托,去卢湾区自忠路一条老弄堂里,为一位新娘拍结婚照,其中一张取名为《从自忠路老弄堂走出来的一对新郎新娘》流传甚广。我一直关注着这对夫妇,这次回沪在黄浦区文化馆举办余慧文、龚建华“1978-2018上海黄浦时空影像”摄影展,我又特意拜访了他们,他们给我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就是这幅《从自忠路老弄堂里走出来的一对新郎新娘》照片里新郎。我名字叫谢今,照片拍摄于1995年11月11日,当时我28岁,现已51岁。我的夫人叫俞炯,当时24岁。这条弄堂当时是上海自忠路210弄9号,当天我随迎宾车去接夫人参加婚礼,如今这条弄堂已改造成新天地的太平湖。我们结婚当天,摄影家龚建华先生全程帮我们拍照,留下很多珍贵的回忆。当时的我在交大昂立上班,夫人俞炯在应昌期围棋学校任职英语教师。
2007年龚老师美国回来,又专程来我们的新家拍摄了一组全家生活照,当时女儿也已十岁,在读小学,我们的新家位于徐家汇路上永业公寓,是2002年购买的,三房二厅二卫,146平方米。2017年老师再次从美国回来,继续来我家拍摄,女儿已是上海大学电影学院两年级的学生,那次上海电视台也专程过来采访,并在新闻频道播出。
从1995到2007年,直至2017年,龚老师为我们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它们见证了上海的变迁,见证了我们家庭生活环境的变迁,从弄堂走出来的我们,迈入了崭新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全家感谢龚建华先生。2018.11.23
80年代初,我发现有一位民警总是在帮助一位坐残疾车的女士上下桥,一打听,原来他叫龚健民,是一位普通民警,他乐于助人,身边的群众如有困难需要帮助,他总是及时伸手相助。1981年他调至打浦桥地区值勤,见每天早晨有一位残障女士坐着手摇车艰难地过桥去上班,他便主动给予帮助,每天推车过桥,直到离开这个值勤点。龚健民乐于助人的精神感染了他的三个儿子龚晓平、龚晓春、龚晓庆。
1999年6月5日,全国首家红十字骨髓捐赠志愿者俱乐部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之一的龚晓平为第一任秘书长,晓春、晓庆也先后加入了俱乐部,为壮大骨髓库、挽救更多白血病患者做着努力。他们关心白血病患者及他们的家庭,帮助汶川地震受伤的儿童,支助云南贫困地区的大学生等等。三兄弟长期坚持无偿献血,多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金奖及上海市无偿献血白玉兰奖,他们累计献血487次,总捐血量达14.29万毫升。其中三弟晓庆就捐献了246次计8.61万毫升。老大晓平虽已近60岁了,仍坚持定期捐献血小板。老二晓春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志愿服务基地的一名资深志愿者,在儿科医院志愿服务了13年,带领100多位志愿者关心、陪伴、照顾白血病患儿,深得患儿的喜爱和家长的认可。老大和老三也不定期地参与服务。兄弟三人均为中华骨髓库的五星志愿者。“病人需要,我们能够,我们愿意”,一直是龚氏三兄弟热心社会公益工作的内在动力。而我,只要有空,就去他们做公益的场所拍照。从上世纪80年代拍他们父亲开始,到今年我还在为他们三兄弟拍,我是被他们的爱心所感动,同时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为普通人保留一份视觉档案。
当一名合格的摄影记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创作的一个高峰期。1988年,我就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第一届个人摄影展,时任副市长刘振元为我的摄影展题了词。
虽然我是一名文艺记者,但是我没有把中外歌星的照片拿出来炫耀,也许那些照片更引人眼球,但我更愿意把侧重与关注社会的照片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情,及时又真实地记录这个表情,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摄影家陈海纹先生评价我的作品说:龚建华作品最可贵的地方在于真。他只是凭直觉和本能按下快门,没有调动任何东西,拍下他所看见和感受到的真实,作品却格外具有生命力。
追求真实,是我醉心于纪实摄影的动力。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一夜之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得了甲肝。当时我很震惊。媒体报道的第一天,我一早就赶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到那儿一看,简陋的隔离诊室墙面上已经贴出了公告:各位病员同志,经全院职工的努力,已从原来的24只床位,增加到142个。人们穿着冬衣,在隔离病房门外排起了长队。当时我还在《音像世界》,虽然是跑文艺条块的记者,但是我还是对社会纪实类的题材更感兴趣。见此情景,职业敏感让我迅速举起了照相机,我喜欢在被摄者不知情的状态下按下快门,这样才是最生动真实的。除了徐汇区中心医院外,我还跑到瑞金医院、中山医院、卢湾区中心医院等拍了一组照片,拍下了拥挤而有序的排队场面,拍下了人们焦虑的神色。在人人谈甲肝色变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可能会被传染,就是跑医院不停地拍。也不去投稿,就这样放着,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1988年上海第一届人体油画展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当时的社会对性文化是禁止的、封闭的,传播裸体照片更是流氓罪,起码判三年刑。当得知要举办裸体油画展的消息后,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震惊的。那天的开幕式是上午九点钟,我凭记者证先进去参观。到了开门后,人们一拥而进,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我发现参观者的神色有紧张的,茫然的,兴奋的,恐慌的,有的人甚至流着口水,也有的人在微微发抖。当时室内光线很暗,我穿行在人群里,用1600度胶卷从各个角度抓拍了一组彩色照片。这些照片是谈不上构图布光等技巧的,只能是纯粹的记录,因为许多表情都是瞬间的。参观结束,我赶到照相馆,要求他们把彩色照片特意弄成黑白的,我觉得只有黑白照片,才能反映出某种质感。等冲印好,我就拿回家了,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发表。2018年11月30号,我收到法国蓬皮杜博物馆发来的邮件,问我愿不愿意把其中一张照片作为他们画册的封面?我回复说愿意。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的作品,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照片背后的时代背景,也是我作为摄影记者的一种责任。
我的镜头,更多的是关注基层百姓的日常点滴。我每天背着照相机,拍下了弄堂里手牵手的老夫妻,通阴沟的师傅,泡开水的老人,巡逻中的警察,打乒乓的少年,黄浦江上放木排的工人,外来农民工……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需要大量农民工。那时,我就有意识地想去做一个农民工的主题。我跑建筑工地、黄浦江船码头、北站,发现每天都有大批的农民工来到上海。一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十六铺码头,正好一批农民工下船,我跟随他们沿黄浦江边,一直走到外白渡桥附近。一路上,我不停地观察着他们,望着这些农民工兄弟东张西望好奇的眼神,手里拎着肩上扛的各种行李,我猜测着他们在老家的生活,想象着他们今后在上海的新生活,我不停地按下快门。我始终觉得,上海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
当一名合格的摄影记者,必须具备一些常人缺乏的韧劲和机灵。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双重身份,对我国进行4天的正式访问。到上海访问时,行程之一是到岳阳路普希金像前献花。得知消息,我来到现场,发现安保力量非常强,有中方的警卫人员,有俄方的克格勃。我虽然当时还在《音像世界》,不可能像时政记者那样拿到采访证,但我凭着机灵进到现场,抓拍了一组戈尔巴乔夫与卫士的照片。凭借这组照片,我获得了1989年中国十大青年摄影记者提名奖。
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二十年在故乡上海,二十年在美国。在美国,我一直担任中英文报刊的首席摄影记者,我放不下照相机,镜头里的世界就是我对过往的留恋,对生命的致敬。现在,我还经常回国举办摄影展,2017年就回国举办了4场摄影展;带领上海视觉艺术大学的学生进行现场教学;平时,我还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对老照片进行修正。几十年过去,许多底片都已霉斑点点,我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8小时,只为了修好一张照片,但我乐此不疲。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名文艺的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