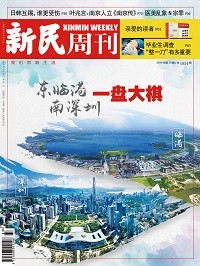2019上海书展: 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根
2019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祖国和故乡,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有家国,才有家园。
而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山村,每天都在发生着可以成为文学素材的故事,为作家诗人们输送着灵感。他们的根,深深扎进家园的土壤中,然后结出丰硕的果实。
2019年的上海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周,试图寻找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根。这里,不仅有我们身体所居住的土地,还有我们的精神家园,需要文学来抚慰。

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家园”
8月13日晚,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在北外滩举行,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题为“家园”。
“家园”这个与全人类相关的话题,引发中外学者的热切讨论。包括中国“先锋派”小说领军人物马原、挪威作家罗伊·雅各布森等在内的近30位中外作家、诗人、学者悉数登场亮相,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家园”。
“关于家园,我的出生地是辽宁省锦州市,”马原回忆起他的童年,“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出生的地方,那片地方后来盖了新房子,所以我不知道我最初的家园在哪里。我是个职业小说家,我知道家园在文学的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有三个家园。”
久未露面的著名作家马原以自己少小离家的经历介绍了在他眼中的家园。在马原,家园是刚开始生活艰辛离开后却开始挂念的辽宁省,家园是向往了许久居住了七年的西藏,家园是他虽患病但依旧安定生活着的西双版纳姑娘寨。
马原曾经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他下乡的地方是辽宁省锦县大有农场。17岁马原初中毕业后来到大有农场,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一个彻头彻尾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完全不懂农村是怎么回事。他住到土坯盖的房子里,喝从压井压出来的水,锄地、割苇子、修水渠,所谓的战天斗地,可以说吃尽了苦头。他从一个瘦弱的男孩长成了一个身高1.84米、体重180斤的壮汉。离开的时候他狂喜同时庆幸,终于脱离了苦海。但是很奇怪,离开得越久,他就越喜欢回想大有农场的那四年艰苦的生活。那也成了他最初关于家园的记忆。压水井、长满盐茜菜的碱滩、土坯房,这些都在他的记忆里定格,成为美好的同义词,成为他一生的幸福象征。
马原第二个关于家园的感受则来自西藏。1976年他中专毕业,申请到西藏去工作,因为所学的铁路专业不对口,组织上没批准,西藏成了黄粱一梦。这个梦做了太久,及至1982年大学毕业,两次申请,居然美梦成真。“我在西藏七年,做过记者编辑,写了诸多西藏小说。我成了西藏那里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也是那个年代的西藏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西藏成为我的另一个家园。我的那些写西藏的小说可以为我佐证。”马原说。
现在的马原,住在云南。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人生中能拥有第三个家园,那就是他现在的家:西双版纳南糯山的姑娘寨。南糯山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普洱茶山,是马原八年前选中的终老之地。八年前,命运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患了重症,但选择了不治。当然,他也不想亏待自己,决意找一处好山好水的地方定居,最后选择了南糯山,并成了姑娘寨的荣誉村民。六年后,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姑娘寨》。如今,东北汉子马原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成为这里的一分子,他说死后也会变为南糯山的一抔黄土:“姑娘寨会是我最后的家园,马原的家园故事在这里定格。”
而日本著名作家角田光代说:“对于我来说,家园是哪里呢?我觉得应该就是书的世界吧。”
角田光代从小就爱读书,翻开书页便感觉自己小小的身体,整个进入书里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童书这种读物就是要引导小朋友轻松地进入那个奇幻的世界,比如《格林童话》里有一对年幼的兄妹,漫步森林,找到那间用各种糖果搭建起来的小房子,我们都曾经相信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打开《格林童话》,角田光代就感觉和童话中的人物一起走进了糖果屋。而合上书本,即使回到现实,他们曾经目睹的那个世界也已经在心里生根,在身体上留下了印记,成为了文学的家园。书中世界体验越强烈,对他们的影响越大,甚至超过了现实经历,并成为他们日后成为作家的文学之根。
作家的奥德赛之旅

8月14日晚,著名作家叶兆言、刘亮程、叶舟来到上海作家书店,这三位都是本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他们对谈的题目是“作家的奥德赛之旅”。
《奥德赛》是古希腊伟大的诗人荷马创作的一部神话长诗,荷马把奥德修斯的10年海上历险,用倒叙的手法放在他临到家前40多天的时间里来描述。这10年惊心动魄的经历,包含了许多远古的神话,反映出经幻想加工过的自然现象以及古希腊人同自然的斗争和胜利。
乔伊斯写过一部天书一样的《尤利西斯》,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改写荷马《奥德赛》,“奥德赛”又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隐喻:漂泊、无根、彷徨。
也许,经历过“奥德赛之旅”的现代人,才更能理解家园的意义所在。也是巧了,这三位作家,最新推出的作品都与他们生活的城市乡村有关。叶兆言的《南京传》,刘亮程的《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叶舟的《敦煌本纪》,分别将目光对准南京、新疆和敦煌。
“《奥德赛》主题是家园,”刘亮程说,“我在这本书里面也写到我的家乡,你来到世间的原点,作为家乡的小村庄,其实在你出生的一瞬间就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了你,从此之后家乡一无所有,剩下的时间就是你慢慢地用自己不断长大的生命去认这个家乡,建构这个家乡的时间。”
活到50多岁,刘亮程觉得家乡已经存在于他的内心中,现实意义的村庄早已被风吹旧了。一个作家带着自己内心的家乡在大地上流浪,在文字中索取,家乡无处不在。
他记得今年5月份的时候,叶舟邀请他们去甘肃平凉采风。刘亮程其实本身是甘肃人,与叶舟是同乡,叶舟是兰州人,他的家乡在九泉。但是说他们是同乡,刘亮程又觉得有点不对:“甘肃那么大,那么长,两千公里长,一个人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大的家乡呢?”
到平凉的时候,朋友也说刘亮程你回到老家了,但是他想,一个人的家乡只是出生长大的那个小小的角落。后来他走的时候,他听到平凉人说话他又觉得这就是他的家乡,因为他们说的语言是他母亲说的甘肃方言,尽管有差异,但确实是这样的语言。听到那种方言的时候,刘亮程突然觉得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他母亲还在说的那样的语言的家乡中,回到他已经过世的父亲的家乡当中,这种语言的怀抱在那个时刻紧紧地把他搂抱在一起,他觉得一个人的家乡是他不断创造出来的,虽然家乡的那个原点只给了他一个世界:“它在那一瞬间,把这个世界的阳光雨露,把这个世界的风声、太阳、月亮、水,把你从祖先接续过来的那一秒呼吸全部给了你,当它给你这些的时候,家乡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家乡已经一无所有。我们在自己的成长当中不断地建构家乡,我在写乡村,你不能天真地认为我的家乡在乡村,我的家乡在唐宋诗词中,在《诗经》中,在零星笔记中,在我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一个人,当他开始阅读文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内心塑造家乡了,这个家乡不断地在变大,不断在变得广远,但是他又不断地在缩小,到最后家乡缩小到那个你出生原点上,缩小到你内心中那个叫灵魂的地方,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就完成一场从家乡出发最后又回到内心的故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