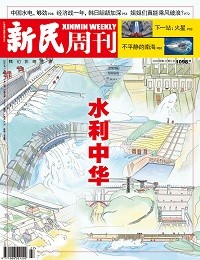致姐姐:你们终将乘风破浪

才写完中年男人的危机与自救,又来了中年女人的乘风与破浪。
男人,女人,折腾,头疼。
但这是个和星辰大海一样古老的话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被拿出来再研究研究。
其实,相当程度上,举凡涉及两性的讨论,剖开表面化验内层切片,得到的结果,基本都和“权利”与“权力”有关——管你是哥哥姐姐,还是太爷爷太奶奶。
然而,做文章,不能在开头便一句话一锤定音,太偷懒了。好罢,围绕近日热播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下简称《浪姐》),记者亦试着披荆斩棘、迎风冲浪一番。
风雨至,水幕起,须破浪。念天地之悠悠,何方神祇呼风唤雨?谁个为你挡风遮雨?
环顾四周,最后,只有我自己。
综艺节目通过女团模式对抗女团,注定是一场南辕北辙的挣扎,一次对“非专业主义”解毒失败的饮鸩止渴。
现实维度的芸芸众女,则注定夹杂在时代更迭、三观冲撞的缝隙里,勠力拼搏,或许跳出深渊,云白天青。
笑。环顾四周,最后,只有我自己。
《浪姐》的正负面
《浪姐》之问世,是事先张扬的。
它符合大部分一线都市女性的内心风向标。因此,它的成功,等于对韩寒《乘风破浪歌》+赵雷《三十岁的女人》的怒斥;等于对“霓虹”《贤者之爱》+“泡菜”《密会》+本土《小丈夫》的击节;等于对脑洞大开的《淑女的品格》的欢呼雀跃;等于对唱着《红色高跟鞋》的敏涛表情的鬼畜追捧。
一档节目的成功啊,固然得靠自身的奋斗,却也十分依仗历史的进程。
虽然《浪姐》的设计整体参考了时下热门的团体偶像选秀“101系”,在参与节目的30位中年女星中选拔5位集结成团,但跟传统的偶像养成素人选秀不同,成名女星绝非半生不熟的小白兔、小黑莲,她们有想法、有主见。“你pick我,我才有价值”?呵呵,弹开。
这造就了节目的火爆。“独立、成熟的中年女性”形象,是受众对荧屏渴望已久的期待。《浪姐》更像女星们尽情放肆的超级秀场——晓明喋喋不休念叨的“加分项加分项哦”,不是什么“卑微”“求生欲”,是事实。
开播之前,不少人依旧暗搓搓地抱着“等互撕”的心态。女人间开启“斗鸡互啄”模式,恰是一种刻板印象,也是很多宫斗剧的逻辑。即,在男性欲望占领导地位的男权社会里,女人们是以男人为归属而彼此竞争的潜在对手,“她”和“她”的友情,难成立。而“坐山观虎斗”的津津有味,也是男权文化下对女性的怂恿——无须更快更高更强,只求更白更瘦更幼,比容貌、比身材、比天真,若争到(男人的)宠爱,就真真是极好的,惟愿不负恩泽。
当然,《浪姐》的意义,是反套路。因此,它的剧本,先天摒弃了甄嬛们那些不入流的招数。给被无视、被遗忘的中年女性群体打回春针,让受到传统规训而习惯隐藏、躲闪的“女子力量”焕发光彩,用实力去证明,才是节目的主旨。
张雨绮说过的一席话很有代表性。大意:人气是人气,业务是业务,两回事。只靠人气站在舞台上,心虚。艺人总要有作品,才站得出去吧……听听,你以为绮绮子不过“武林女宗师”,只懂掌掴(汪小菲)脚踹(王全安)刀砍(袁巴元)吗?错,人家门清着呢,自信和霸气,建立在“实力”的地基上,旁人方觉得这是性格特点,进而构筑了所谓的“人设”。
伊能静一度因为太想表达被群嘲,正跟这个“实力”问题有关。东拉西扯就东拉西扯呗,何必一路岔到梅艳芳?梅艳芳的咖位,是静公主攀得上的么?所以,尽管伊能静的陈述有一定道理,吃瓜群众也只会觉得翻车了,“你也配你也配”的咆哮,回荡于脑际。
反观玛丽亚·凯莉,每逢有主持人在她面前提及其他当红女艺人(红到绝无可能不知道是谁),并试图与花蝴蝶本蝶比较一二,她都微笑着摆出一脸无辜状,“I don’t know her”,竟反而产生贱贱的萌感。You don’t exist to me at this moment——牛姐永远是牛姐,她有那个底气傲,有那个底气装。
坦白讲,《浪姐》的巨大声浪,无疑给予市场一个强力的反馈,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但是,关于中年女星的困境、关于女性如何变老,节目是根本没有答案的。区区一部综艺,尚无法改变整体环境,更何况,伴随着讨论度的加深,冷峻的批评出现了。
前已述及,《浪姐》打造的女团,是非一般女团,倔强不驯的姐姐,取代了言听计从的妹妹。其中,尤以女王宁静的吐槽杀伤力最大:“还要介绍我是谁,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都不知道我是谁。”很爽是不是?爽就对了!但爽完之后呢?仔细想一想,类似这等纯粹碾压式的“爽”,是需要警惕的、是危险的。

初看,《浪姐》希冀强调女性价值和女性之美的多元化,30位在主流观念里已经不年轻了的姐姐,仿佛30记挥向年龄桎梏的重拳。如果单从实际年龄和个性化的角度来分析,《浪姐》已做得挺到位,但在具体突破对女性价值、女性之美的旧时代定义上,节目仍然乏善可陈。
请注意,姐姐们被赞美的、被消费的、被青睐的、成为噱头被营销的,还是标致的外表、纤秾合度的身材、媲美少女的皮肤、始终高指标的活力和自律,以及,视觉年龄远小于真实年龄的“年轻”。
借助这群令同龄人扬眉吐气的姐姐,当下社会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压迫被节目精准命中。《浪姐》打着“反女团”整齐划一青春可爱集体审美的旗号,通过选手之口说出的“哎呀要百花齐放啦”,不能掩盖它所缔造的另一种“集体审美”。
那么另一种“集体审美”,可被哪个问题替换呢?
这个问题——怎样的女性,算活得成功的?
《浪姐》说,“三十岁以后,人生的见证者越来越少,但还可以自我见证,三十岁以后,所有的可能性不断褪却,但还可以越过时间,越过自己”。结合节目所邀群星,我们发现,其中心思想之指向,是在年龄红利逐渐消退的价值体系下,精英群体,依然能以个人的天赋/努力/资源无限期延宕年龄红利的成功学体系。
女星一边拥有多年打拼出的、年轻偶像尚未积累的资历、地位、业务能力;一边又能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拥有力压普通后辈的“形象胜利”。
不知不觉地,节目就给女观众们灌下了一碗“形象焦虑”的迷魂汤。无形中,它传达了这样的价值观:女性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傲人的颜值及精神状态,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肯定。
也就是说,混得好的姐姐,值得被尊称一声“姐姐”。混得不甚如意的姐姐,就成了在社会话语中消匿的大娘。(想到几年前“大叔”与“师傅”称呼间的调侃了吗?)
成功学,非常成功学。
从这样的立场解构,我们可以总结,《浪姐》的慕强倾向颇明显;我们更无语而忧伤地发现,绝大多数的女性,按节目的慕强倾向,都不是姐姐,是大娘。
此外,补充一点,被大加褒扬的“浪姐”间的互相赞美和欣赏,亦弥漫着阵阵缥缈虚幻之味。群芳鲜妍,在道上大大小小各占一席之地,心知肚明,该综艺本质上是无害的,动不了自家的奶酪。既然如此,何不作出磊落、亲切的姿态?全是加分嘛。这就像古时候天冷飘着鹅毛大雪,富人家围裹狐裘喝酒赏梅——大雪,恰是“风雅”的加分项——而流浪街头的乞丐们,只能被迫为抢到一个馊掉的馒头搞到头破血流。
乘风破浪,是要资本的。
现实里的“魔咒”
《浪姐》形成的饭圈生态,一举多得。它解决了大部分一线都市女性选拔“符号玩偶”的困难,也解决了普罗大众的yy之需,更满足了资本等待回报的诉求。我们不必将节目的涵义拔得过高,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改变,是要被鼓励的。权利、权力的斗争,向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目前的社会舆论环境中,《浪姐》所引发的系列对于女性议题的探讨,不啻一个不错的开端。
考虑到女明星们精致华丽的生活没多大示范作用,记者真正关心的是,跳离《浪姐》,进入现实,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平平无奇的中年女性,是否都能打破传统社会残忍施加的那些顽固的“魔咒”呢?
包括——
对女性躯体之衰老的凝视与苛责(标准比男性高得多)。逐渐发胖、身材走形是不可原谅的,性别身份限制了一切,所以,太多可怜的女性,在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广告和医美整容中沦陷。
职场与家庭难以兼得。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甘愿浪费自身才华,受困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吗?当主妇承担着无法被量化的家务劳动,她们如何忍受自我价值得不到承认的痛苦?选择职场,职场有“性别天花板”,各种显形、隐形的歧视无所不在;选择家庭,女人们又在“独立的骄傲”和“讨好丈夫的娇妻”之间徘徊,犹疑不定。
她们并非不具备“出走”的能力,却依然受到家庭与社会伦理的羁绊。2020年了,依然有很多人,将婚姻与生育视为一个女人存在的最大意义。女人不是平等于男人的活生生的“人”,女人是移动的子宫,是教养下一代的免费保姆。
“不被任何人定义”“坚持做自己”,是少数派的特权。
……
不谈了。再一段段罗列下去,《浪姐》的配套众筹节目《水姐》(活得“水”,浪不起来)都能出炉了。

不得不提一提2019年上映的《82年生的金智英》。韩国的这部女权主义色彩浓烈的电影,戏里女主哭,戏外女观众哭,基本把男权社会的“厌女”现象说透了。“厌女”不是新鲜事,非韩国独享,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漫长无尽的偏见,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如是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
20世纪80年代,日本陆续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女性逐渐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但是,大部分的女性仍旧受到传统父权制结构下的暴力统治,女性依旧生存在巨大的割裂中。举个例子,今年7月的新闻:一位日本妈妈在超市买成品土豆沙拉,某路过的陌生大爷居然立即就指责道,“身为母亲,土豆沙拉什么的,好歹自己做吧”。旁观者将此情景发上推特,主妇听闻无不大怒,舆论哗然。
对比之下,中国之所以较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肇始于五四运动的激进,发扬于新中国提倡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居安当思危。时至今日,虽然表面上依傍女性地位的提高,公众舆论场上愈发注重喊一喊女性的自立与审美的多元,但那份聪明外露的“关怀”,更像是“女性主义热”下的漂亮包装,是娱乐资本和消费主义合谋后对“女性可以勇敢做自己”话语的巧妙利用,一种不得罪任何人的、有限度的宣传策略。社会的总体氛围,还是心照不宣地认同着旧往的成功学规矩:女性只有足够“好看”、“有钱”“有人爱”“有孩子”,才是获得了幸福的。此处也举个例子,今年6月的新闻: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发布了一则生活视频,底下某条有上万点赞的热评,却满是恶意——“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你再美再优秀都是逃不过岁月的摧残……”
叹息。
尽管关于“女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现代的女性往往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无可避免地,她们仍旧会被灌输传统的为人妻、为人母的观念,依旧会陷入无爱的惶恐。对于生存方式的苦恼潜伏在现代女性内心深处,很多女性无法掌控好“自立和依存”的平衡,背负着被二者慢慢撕裂的宿命,踏上寻找自我理想的旅途。
“魔咒”的箝制,令亿万女性千年受苦。坐以待毙?绝不。她们要自救,要自强,要成果。
记者获悉,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2020年7月1日为调查时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调查。该调查是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具有全国规模、权威性的重要国情调查、妇情调查。自1990年起,每十年开展一次。而今年又正值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之际。
此前,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
经济状况上,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71.1%,城镇60.8%,农村82.0%。在业女性在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5.3%、14.5%和40.2%。
政治状况上,2.2%的在业女性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92.9%的女性关注“国内外重大事务”,54.1%的女性至少有过一种民主监督行为,18.3%的女性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和村提过建议。
性别观念和态度上,被调查者中有83.5%的人认同“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88.6%的人同意“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86.7%赞同“男女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
高层女性人才状况上,女性高层人才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81.4%,比男性高7.1个百分点。95.9%的女性高层人才“能够主动进行知识、技能更新”;93.7%“能够经常与同事、同行交流对工作、专业的想法”;79.1%“对自己的发展有明确规划”。
这是十年前的数据。我们希望,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结果,能更好。
谁是乘风破浪的女人

2020年5月17日,“敦煌女儿”樊锦诗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她的脸上现沟壑,她的发丝转银白。可是在记者眼里,在许多人眼里,唯有这样的女人,才真正称得上“乘风破浪的姐姐”。
秦时月,汉时关,驼铃声摇醒古敦煌。祁连雪,玉门霜,梦里的飞天在何方?
受父亲影响,樊锦诗从小就对历史文物有浓厚的兴趣。而初中时期历史课本上对于敦煌的描写,更在她的内心,种下了一颗关于敦煌的种子。
1962年,北大毕业前的考古实习中,24岁的樊锦诗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另外3名男同学来到敦煌实习。
她痴了。莫高窟的壮美,让那颗关于敦煌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
和震撼的艺术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恶劣的生活环境。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
一天只吃最简单的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破庙泥屋,没水没电,半夜还会有老鼠掉下来,也没卫生设施,晚上想去上厕所,还得摸黑走上一段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登蜈蚣梯,因为害怕,每天樊锦诗都会在身上揣几个馒头,尽量不喝水,避免要去厕所攀上爬下。
这个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的姑娘,充分领教了莫高窟生活的“下马威”。实习期间,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她的身体本就不算强健,没待到3个月,病倒了,无奈,提前结束实习。
“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可不到一年,她却食言了——毕业分配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跟北大指明要之前过来实习的那4个学生。父亲心疼女儿,曾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学校别让樊锦诗去;信没送出,因为,做女儿的想了想,“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年9月,她再一次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院,这一待,便是大半辈子。
在敦煌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每一寸彩塑。她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诸多领域,皆取得累累硕果。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多次奔走,令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最终偃旗息鼓;她积极谋求文物保护与国际合作,在各大景点中对莫高窟率先实现限流;她提出“数字敦煌”,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建立数字中心,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她的身旁,站着“敦煌女婿”,丈夫彭金章。
两人是同班同学,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起先,一个在敦煌默默耕耘,一个在武汉大学认真研究,婚礼后长期两地分居。可等到1986年领导同意身为业务骨干的樊锦诗调离了,她又不舍得了:“这个石窟,好像我还应该给它做点什么。”
彭金章尊重妻子的决定,他“抛下”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已是武大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赶赴敦煌,圆了“双双对对”的心愿。原本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的他,还勘探清理了莫高窟的北区,将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樊锦诗不止一次表示,彭金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先生,“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2017年7月29日,81岁的彭金章永远闭上了双眼。想必他终归是无悔的吧,得一人,志同道合,知情识趣,甘苦与共,不忘初衷;她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得到他的赞叹,她的每一个眼神,都是那么流光溢彩;有妻如此,不枉青春,与子偕老,幸甚至哉。
乘风破浪的姐姐,就要乘风破浪的哥哥来相配。
樊锦诗目睹了常书鸿、段文杰等大师放弃优渥的境遇,心甘情愿扎根大漠戈壁,“最后就埋在莫高窟的前头,还守望着莫高窟。”而此般“倾尽所有、奉献一生”的信念,也融进了她的灵魂。不说遗憾,但求无愧,“敦煌保护人”代代无穷已,丝路新诗篇年年咏不尽。
除了樊锦诗,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中国天文界第一位女台长叶叔华(小行星3241号命名为“叶叔华星”),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之“恋”的功臣王乃雯,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厂的女性总工程师姜丽萍,以及使鹅厂低下鹅头的国民老干妈陶华碧,和迷之自信的格力耿直girl董明珠等,个个铮铮佼佼,耀眼夺目。谁敢嘲笑她们乘风破浪的资格?谁敢质疑她们乘风破浪的能力?
我是一个女人,我明了不依附他人,明了世间的严酷与温柔,明了自己想做什么,在做什么,明了为了值得的人或事付出,我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无论财富、地位的高低贵贱。
祝全天下的姐姐们,终有一日,豁然开朗,笑傲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