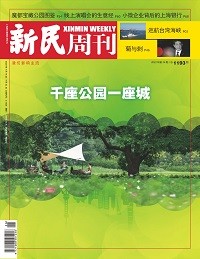专访原创推理大神呼延云: 文艺作品的创作,探索比成功重要
口碑炸裂!
出版一个月后,《扫鼠岭》加印,这是他出版的第八部长篇小说。
十年前,西郊发生导致四人死亡的连环凶杀案,未满十八岁的周立平被捕后,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真凶。而警方认定,周立平只对最后一起案件负责——于是,他只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十年后,深夜的扫鼠岭上,废弃地铁站的隧道风亭里燃起熊熊烈火,消防队员在风亭底部发现了多具尸体,监控视频、现场物证都显示,制造了这起惨案的正是被释放不久的周立平。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真凶?
《扫鼠岭》将刑侦文学的优秀元素和推理小说的诡计悬念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步步推进的情节铺陈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真相,足以让人一口气读完五六百页,大呼过瘾。
2009年,第一本推理小说《嬗变》出版后,名叫“呼延云”的小说家兼小说主人公横空出世。呼延云以其对传统推理小说的全面突破和锐意变革,被誉为“华语推理的革命者”。
他的《黄帝的咒语》一书曾霸占各大电商悬疑推理图书榜首。其作品熔本格派与社会派于一炉,创造出一个个恐怖离奇、悬念迭出的不可能犯罪案件。侦破过程往往展现法医学、刑侦科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前沿成就,同时坚守推理小说的本质:以严密的逻辑性推导出不可预测的震撼结局。
他的每部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且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中国风,被评论界誉为“开拓出推理小说的全新时代”。

从小爱读侦探小说
《新民周刊》:怎么会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毁灭》的?当时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是不是觉得特别累?
呼延云: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一家报社做采编工作,虽然我出身新闻家庭,从小对新闻写作耳濡目染,但理想却是当一位作家,所以在学生时代就勤于练笔。工作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毁灭》,一部青春校园文学,写了三年,六十万字,虽然很累,但一想到出版后就可以实现作家梦,还是很开心的……结果投了二十多家出版社,没人肯出,这件事对我打击非常大。
《新民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侦探小说的?奎因是不是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侦探小说作家?除了奎因,还有哪些侦探小说家对你产生了影响?
呼延云:我从小就喜欢读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学时写过很多侦探小故事,那些小故事现在还躺在我储物柜的最深处。大学时代我更是在图书馆把当时能找到的侦探小说全都读完了。
《毁灭》投稿彻底失败后,我意志消沉,除了工作,就是默默地读书。2005年前后吧,我在航天桥附近的一个小书店看到了三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奎因推理小说,其实我大学时读过他的《希腊棺材之谜》,坦白地说当时有点没看懂,所以并没有对他的作品产生强烈的兴趣,这一次重逢,就信手买了下来。
有时候觉得人与人的相见是缘分,人与书的相遇也是缘分,倘若我那时买的是《西班牙披肩之谜》或者《罗马帽子之谜》,那么可能还是不会对奎因引起太大的兴趣,偏偏这三本是《凶镇》《九尾怪猫》和《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我先读的《凶镇》,觉得跟我以前读的推理小说很不一样,然后读了《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被结尾大段的精彩推理搞得神魂颠倒。他的作品——尤其是后期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作品——直到今天都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创作。
对我影响巨大的另外一位侦探小说作家是杰夫里·迪弗,我最早接触他的“作品”其实是根据他的原著改编的电影《人骨拼图》,当时就觉得眼界大开,于是想方设法找来他的小说阅读,特别是后来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系列作之后,基本上是出一本追一本。迪弗设置悬念的手法、营造氛围的方式、多重反转的构造,以及小说中浓郁的科学探案元素,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多有学习和借鉴。
此外,迈克尔·康奈利、詹姆斯·艾尔罗伊、宫部美雪、横山秀夫、京极夏彦、东野圭吾和樱庭一树也都是给我很多启迪的侦探小说家。
“真相推理师”系列
《新民周刊》:2007年你开始创作《嬗变》,之后的一系列小说,成为“真相推理师”系列,这个系列是一开始就有计划,还是后来才以系列为名出版的?这一系列的小说,是如何进行整体构思和单本创作的?
呼延云:我在一开始写《嬗变》时,别说成系列了,连这一本的成书都没想过,就是通过写作抒发内心的苦闷和彷徨。直到第二本《镜殇》开始才渐渐有了写成系列作的想法。“真相推理师”这个名字是2016年为了影视版权的推广,再版我的几本旧作时取的。《黄帝的咒语》、《乌盆记》和刚刚出版的《扫鼠岭》都不在其中。我迄今为止出版的八部长篇小说,在主要人物和人物关系的推进上都是有联系的,但每本都有独立的故事情节,所以单独阅读也没有问题。
《新民周刊》:在报社工作十年,2010年你为了创作决定辞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写不下去怎么办?一开始生活的压力也很大,家人有没有埋怨?还是给了你很大的鼓励?
呼延云 :2010年我出版了《嬗变》和《镜殇》之后,对自己有了一些信心。我那时在报社当上记者部主任,工作很稳定,但是我一想到终于通过写作推理小说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虽然年纪大了些(那一年我33岁),还是下决心辞职,全力投入到创作中去。
在辞职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收入,全靠过去工作的积蓄和家人的支持。我一直属于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的人,饭吃饱就行,衣能穿就行,所以也好养活。我那时刚刚结婚,第二年有了孩子,在报社工作时的一些积蓄很快花光了,偏偏我接下来的两部作品:《不可能幸存》和《黄帝的咒语》都遇到出版上的困难,我干脆一边写作一边打工:编杂志、做公号、跑会务、当代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七八年。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社会上不同的人,体验到了各种艰辛与不易,这些都是我过去在报社大院里完全不了解的,这段复杂的生活经历,很多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素材和源泉。
《新民周刊》:你的早期作品争议很大,读者的批评很多,但从《真相推理师·复仇》开始,你的作品的口碑越来越好,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呼延云:单就文艺作品的创作而言,我始终认为,探索比成功更重要。
以推理小说为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大师迭出,流派纷呈,其内核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很容易使后来者受到吸引,从而在创作上产生模仿和固化。我出道时雄心勃勃,决心写出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推理小说,经过仔细地思考,我认为如果想有所突破,就要在构成元素上更加多元化,在叙事方法、叙事模式与叙事结构上加以变革,因此从《镜殇》开始,我就有意尝试着用更加大胆的方式进行创作——不管是以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文化为题材,还是基于现实场景下的超现实人物设定,抑或在叙事模式上的一些反常规操作,都可以看成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出的努力。
虽然这些努力受到了读者不少批评,但我认为,既然是新鲜事物和试验性质,就不应过早地否定和放弃,所以在一定时期坚持这样的风格。
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
《新民周刊》 :刚刚出版的《扫鼠岭》,比2018年大热的《真相推理师·凶宅》的口碑还要好,业内预期这可能是2020年爆款的原创推理小说,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作品?
呼延云:如果说《扫鼠岭》和我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是因为题材过于沉重,我在创作时完全放弃了玄奇的诡计和复杂的逻辑,而是采取了一种比《复仇》更加写实主义的手法。虽然小说的故事、地点、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在描写细节时,我把自己在社会上“飘着”的那些年经历过的和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还有近年来对现实的一些思考和感受都写了进去。
《新民周刊》:你是不是对本格推理情有独钟?在《扫鼠岭》出版后,有的读者认为你要向社会派转型,是这样吗?
呼延云:从《嬗变》开始,我的每部推理小说都会反映一些现实问题,比如《镜殇》中的文物走私与拍卖黑幕、《不可能幸存》中的保健品问题、《黄帝的咒语》中的人体器官盗卖、《复仇》中的青少年犯罪、《凶宅》中的房地产乱象……我也一直在尝试怎样能写出本格派和社会派结合得更好的作品,虽然在写作方式上不断调整,但“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的核心思路是不变的。
《新民周刊》:如何设计悬疑桥段?反转又反转已经成为了悬疑小说的套路,如何让这种反转出乎人的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呼延云:悬疑桥段在推理小说中的设定,应该要根据情节的展开而进行,越自然越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悬疑而悬疑,为了反转而反转,那样的话就显得做作和僵硬。中国古典文学讲究“紧要处”三个字,意思是无论怎样的鸿篇巨构,关键的几个地方浓墨重彩就可以了,要张弛有道,否则,全都是紧要处,那一定让人反胃。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瑞士作家若埃尔·迪克的《哈里·戈贝尔事件的真相》,全书臃肿而冗长,而支撑这臃肿而冗长的躯体的,就是不停的反转,以至于读到最后,人物和情节全都乱了套,逻辑完全无法自洽,BUG多到数不胜数的地步。相比之下,迈克尔·康奈利和尤·奈斯博简直成熟和老辣太多了。
《新民周刊》 :很多读者注意到,你的作品中包含有大量刑侦科学的内容,有些细节不仅真实而且非常前沿,而把这一类素材融入推理小说,在国内作者中非常罕见,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呼延云:我在创作中一直坚持当新闻记者时养成的职业习惯——无采访,不创作。早在写《嬗变》的时候,就托朋友的关系采访过刑警和法医,后来虽然因为工作变动等原因,与他们疏于联系,但是因为受到迪弗的影响,所以一直对刑侦科学的前沿研究和突破予以关注,除了下载和阅读论文外,在一些科技类媒体上看到这类报道都会收集,此外,我有很多朋友是科普工作者,有时遇到问题我会虚心向他们请教。不过,小说毕竟不是学术论文,不可能在科学方面做到绝对严谨——感谢读者们没有求全责备。
《新民周刊》:你对原创推理的现状怎么看,你认为原创推理什么时候才能像原创科幻一样“火”起来。
呼延云:去年四月份吧,“华斯比推理小说奖”的颁奖仪式在北京举办,当时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担心原创推理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那之前,《推理世界》杂志纸质版停刊了。我是做媒体的出身,媒介形式的变化对媒体内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如果供年轻一代出道的渠道堵死了,那么原创推理的前景就非常不妙了……一年多来,我发现我的担心是错的,因为大家在用各种办法不断推进推理小说的创作、出版、宣传和推广,比如华斯比推理小说奖、QED大奖、星火奖等等,给新人不断提供出道机会,然后直播、短视频等新的媒介形式都在慢慢利用上,今年很多新老作家都在出版实体书新作,整体水平都有提升,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形势。
至于原创推理什么时候能跟原创科幻一样“火”起来,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于中国都是舶来品,而近代以来,所有舶来的文化和文明,在被我们接纳和吸收时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如果太急于求成,那么最终即便是看似接纳成功,实质上一定是走向这种文化和文明的反面:以正向的姿态走向逆向,以愚昧的方式注解科学,以反智的喧嚣抹杀理性——我相信推理小说也不会例外,就像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里说的:“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哪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原创推理复兴迄今不过二十年,虽然无数优秀的创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整体上看,底子依然很薄,无论在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无法与日本和欧美相比。一种类型文学的兴盛,应该是多产、多样和多元缺一不可,在题材、风格、评价体系等诸多方面彼此包容、促进。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前,倒不妨放长预期,埋头创作,致力于作品本身的精进,而不要去奢求原创推理也出一个刘慈欣,拿一个大奖就能带动起来,那是不现实的。(记者 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