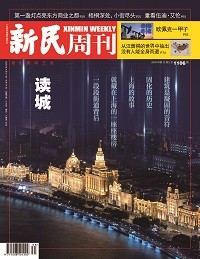从汪曾祺的世界中抽出, 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
一个老乡告诉我,“生命须珍惜,远离汪曾祺”。我有些惊诧,又觉得有道理,更能知道话中的“反意”,毕竟他也是来自高邮,汪老的故乡。因为越贴近汪老的文字,就越恬静释然,越走进汪老的人格,就离真性情更近。他不急又不缓,贪吃又迷物的精神似乎与这个狂飙时代格格不入,却又时刻在敲打我们最敏感、温柔的神经。他把自己一生活成了最炙热朴实的生命。
从汪曾祺的世界中抽出,没有人能全身而退。如果读罢不能微笑,展眉,挠头,搓手,或者猛拍大腿,大概你对生命无感麻木。“生活,是很好玩的”,汪老这句是态度,更是阅历。重读汪曾祺,会发现经久未碰的内心深处的某处柔软。他在《手把肉》文末介绍“拔丝羊尾”,“吃过拔丝山药、拔丝土豆、拔丝苹果、拔丝香蕉,从来没听说过羊尾可以拔丝。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是啊,汪曾祺也宜供佛,人不能阅,因为太诱惑了。
文字的魅力

这份魅力首先源自文字。汪氏的散文、小说和回忆录是中学课本里除了古文和鲁迅之外最好的馈赠。只可惜我们读书时候还没有选入,亏得还是来自江苏,这份热爱是课后读《受戒》,读《故乡人》,特别是想到“别名就叫做盂城”的县城(高邮别称;盂城驿是显赫一时的大运河驿站)。亲切透浸骨子里。
江南出才子,然有才又能写的,其实不多,形成风格的更少。汪曾祺肯定算,从民国一直写到大器晚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他每个阶段都保持了创作水准,融合了国学传统、现代元素和西方技巧,浑然天成。
“中国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的他来自大儒家庭,后又转商。而才气与敏锐,汪曾祺都继承了。少时就和父亲一样书画俱佳,唱戏爱青衣,嗓子高亮甜润。文采是最突出的,可能部分天生,部分受灵气熏润,更多是纯粹爱好:“山顶有两棵龙爪槐,一在东,一在西。西边的一棵是我的读书树。我常常爬上去,在分杈的树干上靠好,带一块带筋的干牛肉或一块榨菜,一边慢慢嚼着,一边看小说”(《耳目所接皆是水》)。这让我想起鲁迅《野草》中那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鲁迅看到“这上面奇怪而高”的天空,汪老却顽皮地爬上去读小说!
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实在他的《小说笔谈》里已总结过:
语言上: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结构上:随便。
叙事和抒情: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
悠闲和精细:唯悠闲才能精细。
最关键的一点,不要着急。“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散文《葡萄月令》中规中矩从一月开始,“下大雪。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葡萄出窖,到三月上架。细到极致,张弛有度。汪老的文字处处透着时光的韵味。
风格冲淡调和,节奏气韵生动,但汪曾祺的人物是“贴着写”,词句拿捏准确自然,有自己的考量。才气傲然考入西南联大,读沈从文的小说,“没想到小说可以这么写”,受到教诲,“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后来写《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三子和巧云相爱,被打重伤,只有灌陈年尿碱才能保命,“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汪曾祺忽然加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他坦言,“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七里茶坊》里写掏粪,“平地上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受戒》“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最后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写家乡拾字纸为生的老白,“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更痛快淋漓的,“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人间草木》)。疏疏落落的长短句,顾盼有情,既干净熨帖又百无禁忌,还略带粗口,恰当的词句在恰当的地方。抛开情节,语言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摄人的美。
客观说,先生身上的“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有几分天成,更多是阅历浮沉之后的积淀。汪曾祺早年吸收很杂,钟爱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追伍尔芙的意识流,也看弗洛伊德和萨特,古文的底子来自私塾诵读,常喜桐城派,尤其是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篇。在西南联大以博杂、偏科、散漫、任性著称,喜欢的课爱不释手,体育、英文却是一塌糊涂,为此还留级。阴差阳错,认识了华侨之女施松卿,后来的老伴。早期的《复仇》《鸡鸭名家》《异禀》,华丽,犀利,也有恨气。
写家乡客来昆明开小饭店,“扬州人老板,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样。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又来了一位南京伙计来做包子面食,“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脑后的褶纹不停地扭动。周身上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的白案师傅”,两人抵牾,结尾颇有欧亨利式惊讶,“扬州人南京人原来是亲戚”,情感上竟然是恨:“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落魄》)。哪里是恨,哀其不幸啊!
建国后,汪老辗转各地,终和夫人在北京团聚。散文、剧本和小说都尝试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还获得了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但大环境终不允许。戏剧的底子让他成为革命样板戏的领军人物,执笔沪剧《芦荡火种》,主笔京剧《沙家浜》,成就了红色经典。我小时候看春晚,常常醉心《沙家浜·智斗》,觉得唱词好,两面三刀的气氛也好,阿庆嫂“沉着机灵有胆量”,一句“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被借来去哄班上笔记最好的同学。
晚年的汪老恰似新春,沉静自如、圆通融和,作品如雨后春笋。早期的飞笔凌云,中段的齐整贴切、起承转合都淡去了,无论是回忆的散文,还是小说,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一点不见斧凿。六十岁写《受戒》,反而活泼俏皮,“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像装在银罐子里的清泉水,清澈明快。写饥荒、写“文革”也是,笔墨淡淡,情绪幽幽,《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鞋匠高大头,挨完批斗后回家修鞋,生意还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讥讽中带着些温和笑意。
人格的魅力
悲中裹着怜悯,是文字,也是性情。“大跃进”时候萧胜“一直跟着奶奶过”,后来才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黄油烙饼》)。汪老的笔下、心中都是摇曳多姿的生命个体。其一生,坎坷颠沛,哀而不伤,悲天悯人。汪曾祺自称“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汪氏悼念沈从文先生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写沈先生,何尝不是对着镜子看自己,借汪氏自己的话,“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文人总是想到别人。
全身癖好、用情极深、一片赤诚是汪曾祺人格光芒。讨论小说,也在说着自己:“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桥边小说〉后记》)
立其诚,人生、感情、待人接物又何尝不是呢?
汪老天分高,天性散,对政治疏离,却一度和政治靠得过近,还因《沙家浜》成功上了天安门;“文革”结束,被晾了两年,写了17万字的交待材料,划清界限。大家印象是,“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
“文革”遭遇,不经意间汪老有了戏剧、文学双高峰。但为此他想轻生,要砍掉手指表明心志,他终究成了那个贪吃、贪玩、贪恋世间一切可爱风景的老人,所谓妙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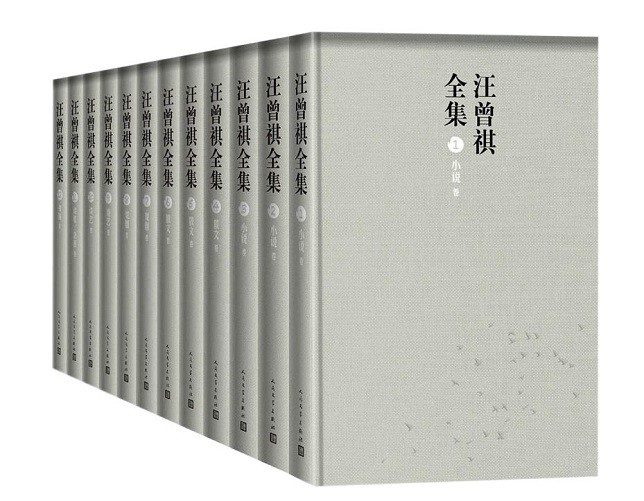
精神的启示
好的作品除了真美,“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对人生,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又读〈边城〉》),这是老师沈从文所思,更是汪曾祺汲取的最大营养。学者翟业军曾经写道,“沈从文的‘善’的着重点不在济世,而是要让读者从作品中得到启示”(《蔼然仁者辩》)。这也是汪老的文字与人格的核心所在——文章之效,滋润而非疗救。不在于济世,而关乎净心,或者静心。
淡和俗是汪氏的审美趣味。脱俗又世俗,脱俗是精神追求,世俗则贪恋这世间一切美好:赏心悦目,大快朵颐,饱览五色,遍尝奇珍。这和如今狂飙突进,效率优先并不相称;他的精神气质也是反崇高、反英雄、反恢宏的格局,有着儒与道的反哺,但也少“匹夫有责”“铁肩道义”的情怀,是缺点,也是特点。
向善首先有纯心,或童心。和丰子恺一样,汪曾祺骨子里返璞归真,文学的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的倾向,打破一切规矩、束缚、界限和框架。所以他“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中国人》)。汪老想起父亲的绝顶聪明也很随和,和儿子关系不错,“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多年父子成兄弟》)。
净心是他一生践行的“不着急”,忠于所学、所思,生活的真谛。他念旧又长情,字里行间,皆是故乡、故人——高邮的鸭蛋与茶干,扬州的酱园和剃头匠,昆明的牛肝菌,北京的咸菜,后研究宋朝人吃喝,自创“塞馅回锅油条”。行文似与人聊天,长短错落,闲说着话,含蓄隽永,口齿留香。白话的传统来自老乡柳敬亭。每多读一分,就对这世间多一份理解和热爱。
所以,汪老说,“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撰稿 马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