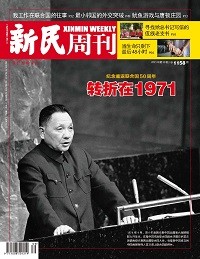考古百年,寻找中国
10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强调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1921年10月,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从发现仰韶以及殷墟考古时的筚路蓝缕,到近年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考古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二里头夏代后期都城遗址、马王堆汉墓、秦始皇兵马俑、四川三星堆古蜀国都邑遗址等一大批重要考古发现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在这里,我们寻找中国。

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4年,瑞典人安特生受聘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1921年,他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安特生极为兴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的工作中去。这样的考古工作,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了不起的开始,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安特生证明了在今日中国这个地方确有史前史的存在。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史时曾经说过,安特生发现这“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后,关于它跟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出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
除此之外,安特生同时也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
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1918年3月,安特生骑着毛驴,到周口店,并考察了两天。
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啮齿类的数量很多。当地老乡之前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误认作鸡骨,因此这座小山得名“鸡骨山”。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在一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
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瑞典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尽管当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这消息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安特生因仰韶文化和北京猿人的发现,在中国的考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谁是“中国考古之父”
五四运动后,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一批学者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形成了“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这一学派对上古历史提出了强烈质疑,堪称“疑古派”的“旗手”顾颉刚更是提出了“东周以前无信史”、“夏商皆伪史”的论断,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研究部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第一任所长。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发掘。次年春天,从晋南西阴村等地考古归来的李济,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正式接任殷墟发掘负责人。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而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则证明,商代确实存在。
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童心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顾颉刚的疑古派对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其实是起到比较大作用的:“这是当时的各种条件促成的,在上个世纪初,顾颉刚等人开始质疑史料,是对历史学根本性的颠覆。在考古学产生之前,中国的学者都是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如何来证明或者证伪顾颉刚的观点呢?正好这时候西方的考古学进入中国,它能够回答中国古代的人是怎么样的,顾颉刚的疑古派只是指出中国古史是有不合理的地方的,但是合理的部分他们没有指出来。他认为大禹是条虫,我现在告诉你,大禹时代中国人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他们的文化面貌是怎么样的。正好使得考古学科传入中国不久就被人们所接受,考古这种学科,对于认识古代的真实历史面貌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顾颉刚‘疑古派’只是破了对史料的迷信,但并没有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而考古学就是要告诉大家,中国古代可能更真实的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
另一个对中国考古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李济。李济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指导,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直至今日,殷墟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也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系他的弟子。
民国时期,在装备简陋、战乱频繁的年代,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却在艰苦的环境下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当时的条件确实非常差,”张童心说,“当时是战乱年代,国家积贫积弱,跟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相比。这些老一辈的考古学家,靠着爱国情怀,坚持了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甚至看到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土匪来侵扰的情况都时有发生。新中国之前考古工作做得不是很充分,也跟这种情况有关。李济虽然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但是人类学和考古学毕竟是两门学科,有关系但不等于完全一样。据李济的儿子对我讲,他父亲在哈佛上的考古学其实是选修课,结果到中国来了之后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纯学术上来说,这是英式的考古方法,不过在殷墟发掘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的考古发掘方法也做了一些调整,逐渐形成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这个学科看上去很中国化,其实完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人的传统对祖先是非常崇敬的,你要去挖坟掘墓,在很多朝代都是要判刑的。国家层面上就不允许,所以这种学科不太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

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
著名学者张光直说: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李济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因而,他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成就、遗憾与走向黄金时代
1937年之后,因战乱,殷墟、周口店和仰韶的考古发掘都停顿下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视,国家将考古学机构、人员重新组织起来。一个契机是新中国的建设比较多,地下发现的文物也比较多。
1959年夏,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张童心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前,考古学者已经解决了顾颉刚的疑问——商代是真实存在的,学界就开始想证明夏代也是真实存在的。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很大力量去全国各地调查夏文化可能的遗址。徐旭生是具体的组织协调者,他先在文献上梳理早期资料,有一部分可能就像顾颉刚说的,像神话,还有一部分则有可能是信史。当时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做这方面的工作。探讨夏代考古,这本书现在仍然是必读书,就是《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献梳理完之后,他认为夏都应该在黄河中游的两岸,于是他有针对性地派出了很多的考古调查队,黄河两岸只要是这个时段的,比商代早比新石器时代要晚的遗址,他一个个排查,从相吻合的遗址中找到了二里头。”
在徐旭生带领下,经过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1972年发现马王堆、1974年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不过,新中国的考古工作也有一些遗憾。比如,1956年至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明定陵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由于当时人们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和发掘技术有限,使定陵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未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迅速风化,成为一大遗憾。
张童心教授认为这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是用的当时世界上比较好的技术和方式,但是当时技术的发展还达不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现在看来这样的技术和方式不能很好地保护文物。这我们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对皇陵级别的遗址,国家是不审批挖掘的。”
现在,张童心教授正在四川三星堆参加考古发掘工作。有了明定陵的前车之鉴,现在的考古工作更加慎重。
三星堆挖出大量象牙,如何保护它们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张童心说:“像我现在在四川三星堆,这里挖出来的象牙,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办法。我们想着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来讨论,最好有一种比较有前瞻性的办法来保护它们。但我想一百年后的人们看我们现在的保护手段,也会觉得比较low。这是科学发展的水平决定的。”
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发现至今的历史,正可以看做中国考古史的一个缩影。从1934年春天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组成考古队开始发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再到改革开放之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三星堆考古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而最近这二十多年的考古,可以说是三星堆考古的“黄金时代”。
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这些造型怪异的青铜器给人无限联想,也留下诸多未解之谜。在三千多年前的这片巴蜀平原上,到底曾经存在过什么样的政权,有什么样的人类居住过,是考古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开的谜题。
除了三星堆之外,浙江良渚大型水利坝、陕西石峁巨型山城和周原西周都邑遗址、江西海昏侯墓、新疆通天洞遗址、青海热水血渭大墓、上海广富林古文化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实物的发现,我们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更加具体了。这是“黄金时代”的考古,正在重新书写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所说:“100年来的考古学实践不仅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中国历史。”
同时,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考古机构和考古工作者走出国门。张童心介绍说:“海外联合考古我们主要还是参与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考古项目。比如在斯里兰卡我们展开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又比如陕西与中亚历史上有联系,西北大学的考古团队会去中亚、西亚寻找线索。现在做的最多的是水下考古,我们在许多沉船中发现了古代中国的器物,这是当时贸易的遗迹。”
从中国本土拓展到海外,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审视中国,这样的考古,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相信不同的视角,会极大丰富我们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经过100年的发展,现在,中国考古学又走到了新的起点,那是黄金时代的开始。(记者 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