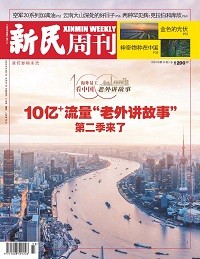最后的白鲟
在地球生存繁衍已有一亿余年的白鲟,最近一次进入人类视野却是永别。
北京时间2022年7月21日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更新后的报告显示: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白鲟“灭绝”。
“白鲟灭绝”很快出现在互联网的“热搜”上,可是作为一直关注白鲟新闻的记者,我并不感到意外。2020年1月,类似的标签同样登上过“热搜”。当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江所”)的危起伟研究员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指出白鲟可能早在1993年就已功能性灭绝(即自然种群无法进行繁殖活动)。从那时起,我知道灭绝的这一天迟早会来。
对于IUCN认定白鲟灭绝这件事,危起伟其实比外界要提早知道,也有心理准备。他曾担任农业农村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是中国著名的鲟鱼类专家。可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危起伟还是在微信朋友圈连着转发了四条相关动态和三个流泪的表情。从7月21日起,将近半个月时间里,超过100家媒体采访了他。电话一个个不停地打来,可他几乎来者不拒。
这一幕在两年前同样上演过。当时近200家国内外媒体对白鲟“功能性灭绝”进行报道,《新民周刊》也是其中之一。那一天,我从早上打他的电话,一直占线,打了5次,打到下午,终于接通。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有什么白鲟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但要抓紧时间,后面还有媒体等着”。
两年后,当白鲟灭绝的新闻传来,其灭绝的原因已不是新鲜话题。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白鲟真的就此从地球上消失,那么全程参与2002年和2003年先后两次白鲟救治过程的危起伟,就是这颗星球上最后见过这一古老生灵的人类之一。从1984年开始参加工作时就研究白鲟,直到今年退休,危起伟大半辈子都在和鲟鱼打交道。
和白鲟多年来数次相遇、救治和搜寻,其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样的疑问,8月初我去往武汉。在长江所的办公室,危起伟向我讲述了过往近40年间见到的那些白鲟,同时更呼吁外界对于目前尚存的中华鲟,以及其他濒危水生物种,需要投入更多关注。
消失的信号
很多人都看过一张白鲟的照片:那是在湖北宜昌的长江江滩边,青灰色的白鲟静静地贴在地面上,它那标志性的汤匙长柄一样的鼻子微微泛着红色。这也是如今为数不多、拍摄清晰的活体白鲟照片,拍摄者正是危起伟。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条日后成为珍贵照片资料的白鲟,其实在被拍完照几天后就离世了。“当时它被我们救回,放到养殖池,也就是‘土池’,没几天就死了。”危起伟告诉我。

上图:1993年10月,宜昌艾家河抢救的活体白鲟。摄影/危起伟
1993年遇见这条白鲟,可以被看作危起伟研究和救助白鲟多年时光的一个“分界点”:他见到过的大部分白鲟,集中在1984年到1993年之间,但大部分是“死鱼”,或者已经受到重伤,救不活;1993年后,救助条件日益提升,但见到的白鲟,只剩下2002年和2003年两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一条白鲟被捕捞时已经受了伤,后面几乎百分百是救不活的。“普通百姓对这种巨大的鱼类完全不了解,碰到它就是手足无措。它这么大一只鱼,你没法用平常钓鱼或者捕鱼的方法去简单对待它,比如钓到后给它随手放进岸边笼子里,或者随便找个水池给它养着,这都不行。”
普通人平时钓到一条几十斤的“大鱼”,可能激动一阵,得花上不少力气弄上岸。可白鲟是“淡水鱼之王”。平常人们眼中的“大鱼”,只不过是白鲟日常捕食的目标。
白鲟太大,太特殊,可毕竟还是鱼类,和大象或者老虎这样强力的陆生生物不同。所以一旦被人类碰上,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从捕捞上岸到后续救治,都必须用上专业、科学的手段,否则就会加速其死亡。
“对于白鲟,怎么抓怎么救,这当中很有讲究。”危起伟告诉我,“首先你得有一个简单的尼龙胶带设计把它固定好,而不是很粗暴地把它鼻子或腮拴住,这样就没法呼吸了;然后它这么重,两三个人都抬不起,这就需要一个机械臂(吊车),还要有一个担架,像抬人一样把白鲟放上去,最好装载这个设备的车要能开到江边;白鲟不能离水太久,所以要有水箱,里面还得是活水。”
危起伟和团队这些专业而宝贵的经验,开始形成于1993年那次在宜昌见过白鲟后的几年里。“早年我们技术还不成熟,救助体系也没建立起来,这就导致见到的白鲟百分百活不下来;现在假如白鲟没有灭绝,只要让我去救,我百分百能让它活下去。”
阔别白鲟多年后,2002年12月和2003年1月,危起伟团队接连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潜洲江段和长江上游宜宾的南溪江段各发现了一条白鲟,当时大伙特别激动。但没人能想到,这会是人类与白鲟最后的照面。
“2002年之前,我已经将近5年没见过白鲟。所以听说南京那边有了,这边团队一共8人,马上从荆州收拾出发。我们那些年都在葛洲坝附近做中华鲟繁殖,积累了很多经验,是一支很能‘战斗’的团队。”
那年12月11日下午,长江所驾驶技术最好的司机,开一辆装有活鱼运输箱的东风车,载着危起伟一行人,从荆州奔向南京。查阅当天南京本地报纸,有这样的记载:“11日下午2时左右,正在长江下关潜洲以北水域捕鱼的渔民孙永来,捕到一条大鱼。这条大鱼与众不同,有一个硕大的‘长鼻子’(吻)。 孙永来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拖到岸边。”第二天晚上赶到南京,危起伟发现这条白鲟已经遍体鳞伤。
采访时,危起伟向我展示了当年见到这条白鲟时的照片。他指着照片说:“能看出它不仅受了伤,有些还是反复受伤。你看,它两个鳍条是卷曲的,变得很小,正常不是这样,应该是舒展的。这就是被船打的外伤,还不止一次被打到过。其他的伤痕说明它还被渔网捕过,又挣脱逃走。而且它的肚子很大,整条鱼翻了过来,说明它鳔里充了气。”看着照片,他回忆起那个寒冷冬夜的心情。
为了给白鲟的肚子排气,他们还请教了鲨鱼专家。成功排气后,团队成员就把受伤的白鲟装到水箱,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到昆山,那里有一个合作的中华鲟养殖基地。“这条白鲟我们后来量了有3.3米长,117公斤重,大概十几岁。运到基地后,我们先把它放到一个直径8米、深2米的圆池里,多次辅助它,它就游起来了。后来又给它转到一个更大的养殖池。”
为什么当时决定把这条白鲟运到昆山基地救治?白鲟实在太大,绝不是一般养鱼的水池就可以容得下它。危起伟介绍,这最好需要一个长度是鱼自身体长6倍、深度是2倍的水池。在昆山,正好有一个之前养过中华鲟的水池。“它水里稍微一摆就游出去好远,如果活动范围太小,很容易就把自己撞伤、撞死。”
看着白鲟在池子里打转,伤口一天天愈合,危起伟特别高兴。当时他已经研究了18年鲟鱼,可这种和白鲟朝夕相处的机会仍是第一次。
除了高兴和激动,危起伟还小心翼翼,恨不得每天睡在水池边。生怕出现意外,可意外还是来临。时间来到12月下旬,气温下降得厉害,池子开始结冰。农业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要给锅炉加温。“白鲟的吻很灵敏,正常来说不会乱撞。可能是敲敲打打的声音,和新建材料的油漆味,让那条白鲟躁动起来。锅炉加温的循环管道和池壁之间有一个不太严实的缝,它游动的过程中,长长的鼻子不小心插到缝里了,插进去后又拼命地一退,鱼一下子就翻了,翻了就活不过来了。”
于是迄今人类公开有记录的倒数第二次见过的白鲟,终究没能长久地活下去,在它游动了半个多月的水池里猝然地离开。“那些天我们都养得很好,它也游得好。直到1月8日那天晚上,值班的同志说,你们快来,鱼不行了。我听到心里一紧,过去看鱼已经翻了。大家站在水池边,都流泪了。”
照例做好解剖,采集完生物样本,危起伟和同事又回到了荆州。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在四川宜宾又有渔民发现了活体白鲟。那条白鲟同样体长超过3米,重达300多斤。危起伟又赶紧启程前往宜宾。经历过上一条白鲟的意外,这一次他的第一反应是——养,还是放?
最终,经过和其他国内专家商讨,又和国外专家沟通,考虑到宜宾附近当时没有昆山这样的养殖基地,危起伟和同事决定将这条白鲟放流。“从1996年到2001年,每年都有十几条野生中华鲟被我们在葛洲坝附近放流和跟踪,所以积累了经验。”
他们也为这条白鲟安装了声呐追踪器,希望由此能找到洄游产卵场,发现更多白鲟。2003年1月27日,那天是农历大年二十五,白鲟回到了江中。3天后,意外又出现了。白鲟突然加速进入长江主干道,江面大雾弥漫,水流急,漩涡、暗礁数不胜数。当时这条白鲟可能游进了暗礁之间,超声波检测不到。

上图:2003年1月24日,宜宾白鲟抢救。图片提供/危起伟
后来在宜宾九龙滩,危起伟乘坐的快艇触礁,船上3人差点因此丧命,追寻白鲟的计划随即搁浅。正逢春节,危起伟在忐忑中熬完了新年的每一分每一秒。等到修好船体,危起伟和同事乘船再从宜宾顺江而下,一路过三峡,一直追到了长江口。起初他还有信心,觉得能找到那条白鲟,但希望渐渐地变得茫然,白鲟的信号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年我们长江流域还没有水下专门追踪鱼类的‘固定站’。如果有这个设备网络,可以大致检测到带着追踪器的鱼游到了长江的哪一段,能很快缩小范围,不至于像当时那样搜寻。”危起伟告诉我。
其实,无论是“固定站”这样的设备,还是对于白鲟人工繁殖更关键的生物技术,都在2005年前后被研发出来。从时间上看和2003年相差不远,可谁也没想到,2003年就是人类目前为止已知的最后一次见到野生白鲟。今天,技术更加先进,但失去就是失去,一只也找不到。
从科学上说,白鲟之所以在2022年被正式认定灭绝,因为白鲟的寿命一般是40年。最后一次发现的白鲟,当时已经超过二十岁。直到今天,人类仍未找到存活的其他白鲟,而那一条自从消失在暗礁后,如今在理论上也走到了生命尽头。危起伟说:“根据我们模型计算的结果,可以判断这个物种最后一个个体已经死亡,所以物种灭绝了。”
大江与大鱼
长江从格拉丹东的雪山冰川中挟着冰雪融水而流出,沿途汇纳700多条支流,流经高原、峡谷、盆地、平原,最终从东方的崇明岛奔向大海。这条超过6000公里的长河中,孕育了丰富的水生物种。
在这些物种中,白鲟可能是最古老的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金帆曾在文献中指出,“已知匙吻鲟科最早的化石,是我国早白垩世的原白鲟”。
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有关白鲟的记载不在少数。从古至今,它徜徉在长江等大河中,见证了人类活动演化和朝代更迭,自身也在古人的记录里变得神秘,甚至成为一种传说。
《淮南子》中的“瓠巴鼓瑟,而淫鱼出听”,认为白鲟懂得欣赏优美的音律;《酉阳杂俎》中的“蜀中每杀黄鱼,天必阴雨”,暗示人们担心杀死白鲟会导致天气异常;至于郭璞在《江赋》中写道:“鱼则江豚海狶,叔鲔王鳣……或鹿觡象鼻,或虎状龙颜”,为白鲟带来了“象鼻鱼”的别称。
等到明朝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提到鲟鱼,还配了图像,重点突出了其长吻和鼻孔,意味着当时人们对这一物种的认知已经较为准确。

上图: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摄影/王仲昀
从这些文字不难看出,白鲟不仅存在已久,而且一直以来与人类都有着连结。这种连结发展到现代社会,意味着白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越来越大。根据危起伟介绍,白鲟平时习惯于在浅水域活动,有时还要把吻探出水面换气,一不小心就被捕捞或者船桨误伤。
更重要的是,这种大型洄游鱼类,活动范围遍布长江上中下游。上世纪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后,将白鲟分隔成坝上和坝下两个群。被阻隔在坝下的繁殖群体,无法上溯到位于金沙江下游的产卵场进行自然繁殖。这是白鲟灭绝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绝大多数生活在长江里的水生生物的命运,因为在长江18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中,历朝历代生活了太多人。人们依水而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比想象中更紧密和复杂。
正如何伟在《江城》中写道:“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历史,根本无法幻想哪里还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块岩石看上去都像某种东西,每一条支流都充满了传奇,每一座小山都饱含着往日的故事。”
大鲟找小鲟
在研究鲟鱼38年后,62岁的危起伟在白鲟宣布灭绝的同一年退休了。他还没想好休息,想继续发挥余热,因为另一个他长期研究的对象——中华鲟,也进入自然种群灭绝的倒计时。
“白鲟已经没了,没了就没了吧。这个教训应该起到警醒作用,让我们去保护还没灭绝的鱼类。你是上海来的记者,上海在中华鲟的保护中很重要。”为此,危起伟建议我回到上海,去找他的学生郑跃平聊聊。
郑跃平是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和他的老师一样,自打从学校毕业后,鲟鱼就成为郑跃平在过去17年里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家里可能柴米油盐还剩多少,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一年365天,春夏秋冬,基地的中华鲟该吃什么,我了如指掌。”
IUCN最新评估结果显示,约2/3的鲟鱼种群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其最新的红色目录里,中华鲟属于“极危”。
中华鲟和白鲟都是大型洄游鱼类,可又有点不同。中华鲟是江海洄游,它虽出生在长江,但生命中90%以上的时间都在海洋里度过。此外,中华鲟的嘴巴是朝下的,它并没有白鲟主动捕食的天性,通常是嘴巴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
按照习性,每年夏季,性成熟的中华鲟会从海洋游回长江,逆流而上直至金沙江段。在那里,曾经有很多它们的产卵场。那些有幸未被其他鱼类吃掉的鱼卵会孵出鱼苗。只有1厘米大小的鱼苗顺着江水一路向东,通常会在第二年4月到达崇明岛的江段。“春季是水生生物繁殖的旺季,中华鲟的幼鱼会在这里索饵育肥,不断长大,然后完成由江入海之前渗透压的调节。”郑跃平说,“就像人类上高原时,最好能够缓慢爬坡上去,给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一下子就上去了,高反就会比较强烈。”

上图: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内的中华鲟。摄影/王仲昀
中华鲟幼鱼进入海洋,北边能一直游到黄海,南至海南岛附近。等到多年后它们再回来产卵时,同样得在长江口完成渗透压的转换。因此,位于上海的长江口之于中华鲟,是“幼儿园”“待产房”和“产后护理所”,是其生命中不可替代的集中栖息地。正因如此,为了加强长江口以中华鲟为代表的水生生物的研究和保护,才有了如今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和白鲟的境遇有所不同,中华鲟的人工繁殖早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1999年,危起伟在荆州建立起养殖基地。那一年12月31日,在跨入新世纪之前,他的团队成功放流了10万尾中华鲟。如今在湖北,在上海,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人工养殖中华鲟放流。但依旧严峻的是,2017—2021年连续5年人们都未发现其自然的繁殖活动。中华鲟的自然种群延续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局面。
很快,2022年秋天就要到来。今年会不一样吗?会有野生的中华鲟来到葛洲坝下的产卵场繁衍后代吗?这些问题牵动着许多和鲟鱼相处多年的人类。
郑跃平的微信名叫“鱘寻鲟”。他向我解释,三个不同的鲟,代表着大鲟找小鲟,有一种传承的意味在其中。在采访中,他和他的老师危起伟都提到“责任”。他们当年进入这一行,要么出于兴趣,或只是将其看作一份工作。但随着时间流逝,所有的想法都最终化为一种责任。
小孩教大人
如今在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有14778种动物级别为极危、濒危和易危。其中,6009种物种生活在内陆淡水系统,占比超过四成。不只是长江流域,放眼全球,水生物种都是灭绝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
在危起伟看来,水生物种保护相较于陆生动物更困难,这与其特性有关。“水生物种不会叫,一直在水下,很多长得也不可爱。哪怕是白鲟这样在地球生存上亿年的有灵性的鱼,也不会和人类互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水生生物的濒危程度与关注度之间的巨大落差。

上图:2009年11月19日上午10时许,上海市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暨长江口区涉渔工程水生生态修复活动在长江口举行。图为工作人员在崇明长江口放流中华鲟及鱼苗。
2022年6月,多家外媒曾报道过一位柬埔寨渔民捕获了有记录的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一条体长超过4米、重300公斤的黄貂鱼。在当时的新闻中,还有一位美国内华达大学的鱼类学家被报道,他就是近年来一直专注找寻和记录大型淡水鱼的泽布·霍根。
危起伟告诉我,霍根在很多年前就到过长江所,他们有过关于白鲟的交流。“霍根主持的电视节目有点做秀的范儿,但他做得挺好,有时候需要这种秀。他的节目不是要解决某一个问题,而是把一个问题展现给公众,引起更多关注。”
不只是电视节目,危起伟认为水生物种保护是系统性工程,而政府、学界、媒体和公众,缺一不可。当然他也坦言,这需要一个过程。“白鲟灭绝后有很高的热度,上了几次热搜。这说明除了娱乐明星,水生物种同样可以嘛!至于如何把这种热度真正转化成实质性的保护,需要时间的积累,不会一下实现。上一代人看到鲟鱼,第一反应是它美不美味,哪里能吃到。现在经过科普,至少小孩子知道中华鲟不能吃,很宝贵,他会去教育大人。”
从整个地球的演化史来看,人类也必然要和自然和谐相处,因为人类所谓的漫长历史与自然相比并不算什么。
这让我想起约翰·麦克菲在《阿查拉法亚河》中的那段话:“在人与自然这场持久而缓慢的较量中,到底谁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没人知道。但看看圣海伦斯火山,听听人们对它发展形势的猜测。如果一定要我们作出抉择,我们会把赌注押给这条河。”(记者 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