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重回C位?
忽如一夜诗风来。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几年,诗歌似乎开始呈现出重回C位的隐隐势头。有人穿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倾倒孤注一掷的狂热(余秀华);有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王计兵)。职业诗人笔耕不辍,专家学者也灵光乍现,赋诗自乐。美术馆、书友会传来朗诵诗歌的声音,各类微信公号、App推文亦经常发送“睡前小诗”一首,追慕雅人深致的风度。明星、要人们读诗,普通百姓们同样读诗——虽然,这一轮滚滚诗潮目前看来,远未覆盖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光芒,但的确已经足够闪烁,构成话题。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拘形式和体裁,充满魅力的诗歌,探讨爱情、社会、艺术、人生、哲学……每一行文字的吐纳,回应着一颗心脏的悸动,宛然拨开喧哗鼎沸到抵那个鸿蒙初辟的原点,宛然一梦。
飞光煎人寿,幸好我们还有诗歌,不管天高地厚。
中途诗事
老早的年岁见过璀璨的星群视作日常
此后所有的夜空 都会被它们的前身
暗自增添深邃的可能
汨罗江畔,芙蓉雅集。今年5月20日,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芙蓉文学图书榜”入选作品揭晓,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三行集》,成了此次唯一入选的诗集。该书一页只印三行字,有大量留白处理,充分释放字、词、句本身的能量,使之自由自在。上榜辞称:“心开意适,三行成诗,记述细微的人事,倾听微弱的声音,即便是关于词语、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深沉思索,也低语徘徊、轻声争辩。凝视生活的瞬间,辨析内心的响动,张新颖以他的敏锐、体恤、想象和思力,发现渺小事物的光泽,也守护了语言的尊严。”
但时间倒退回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大一新生小张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一个房间,人已经聚集了很多,灯光忽然一暗,又忽然大亮,复旦诗社的活动正式开始。诗,关于诗的理念,主张,辩论……灯光下那些年轻的脸,泛着特别的光芒,激动的情绪混合着不羁的才华,满屋子横冲直撞。“我好像是要躲避这些才华和热情,活动还在高潮迭起,就悄悄退了出去。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沮丧吗?多少有点,但远远谈不上严重。那个年纪,会以为人生的可能性选项多到数不过来,这只不过是在纸上划掉其中的一项而已。”
诗歌风行的年代,校园里弥漫着特有的兴奋和抒情气氛,张新颖置身其中,却仿佛又绕开了。他不写诗。更准确一点说,偶尔写,写得不好,也不怎么当回事。例外的是,用心做了一个“实验”:写了一组“读书笔记”,形式却是诗。
这种含混的写作从1988年持续到1995年,可见兴致和轻微的沉迷。张新颖以为,随着青春时代的结束,此般“自娱”大概会渐渐消失。不料,40多岁的时候,2011年,忽然又写出一组《“剪辑”成诗:沈从文的这些时刻》来——“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慢慢洪流中挑出来,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诗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力量。”“写这组诗当然与我的沈从文研究有关,但私心里,并不情愿把它看成研究的‘副产品’。”
教书的头两年,张新颖编选了一本《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年了,这本书还在印行。“当时做这个工作,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的学生方便,我开了一门‘中国新诗’的课嘛。每次面对新一级的学生,我总是这样开口:你选这个课,要想想它和你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如果你不写诗,将来也不做新诗研究——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吧,你和它可能形成什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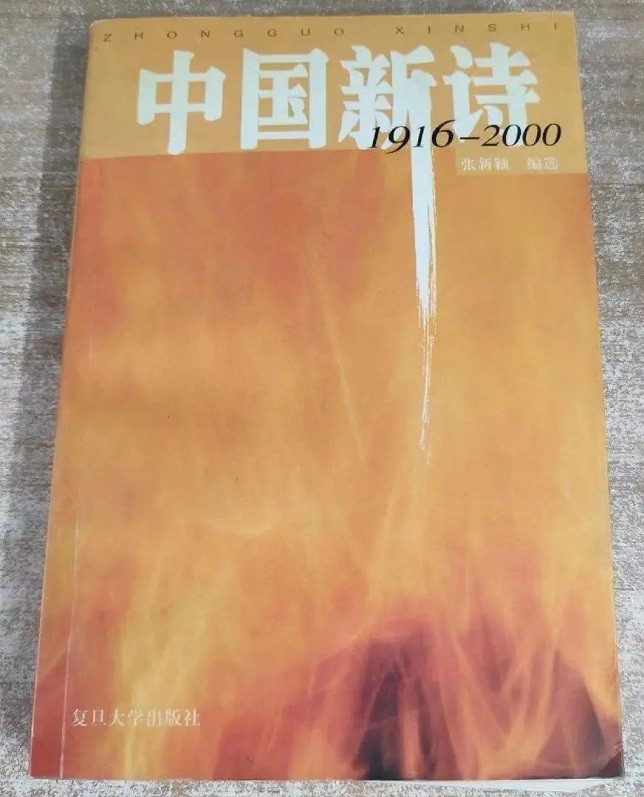
这样说了十年之后,张新颖发现,自己不能再用“如果你不写诗”作开场了。2011年的某天,他在办公室写毛笔字,裁纸时不慎碰倒了杯子。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碎了一地,刹那工夫,张新颖“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紧张地盯着它,仿佛要用眼神阻止它跌落;等到碎裂的声音响起,倒是松了一口气。我把这个心理过程用毛笔写下来;又想,杯子是个器皿,盛水或牛奶或酒,也有别样的‘杯子’,盛的是事业、感情、身份或者其他种种,这样的器皿,也可能会碰倒、碎裂。那么,我顺手涂出来的句子,似乎多少有点意思。就又在电脑上重写一遍,短短地,叫它《杯子》。”
之后,在各种各样事务的间隙,不那么经常地,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促使张新颖拿起手边的铅笔、钢笔或水笔,在眼前的一张纸或一个本子上记下来,等待其完整成形。他放松地写平常的经验,平凡的呼吸,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2017年,诗集《在词语中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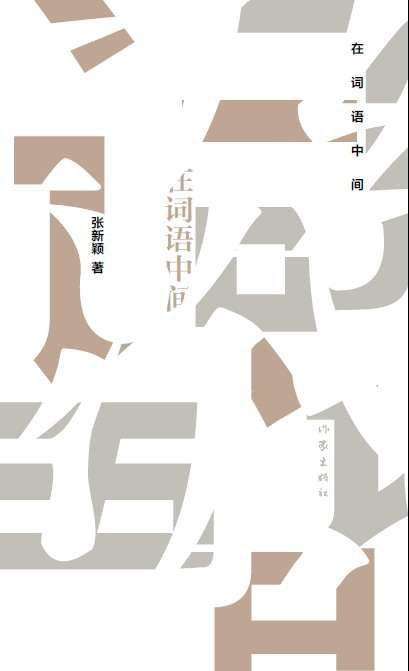
2020年,《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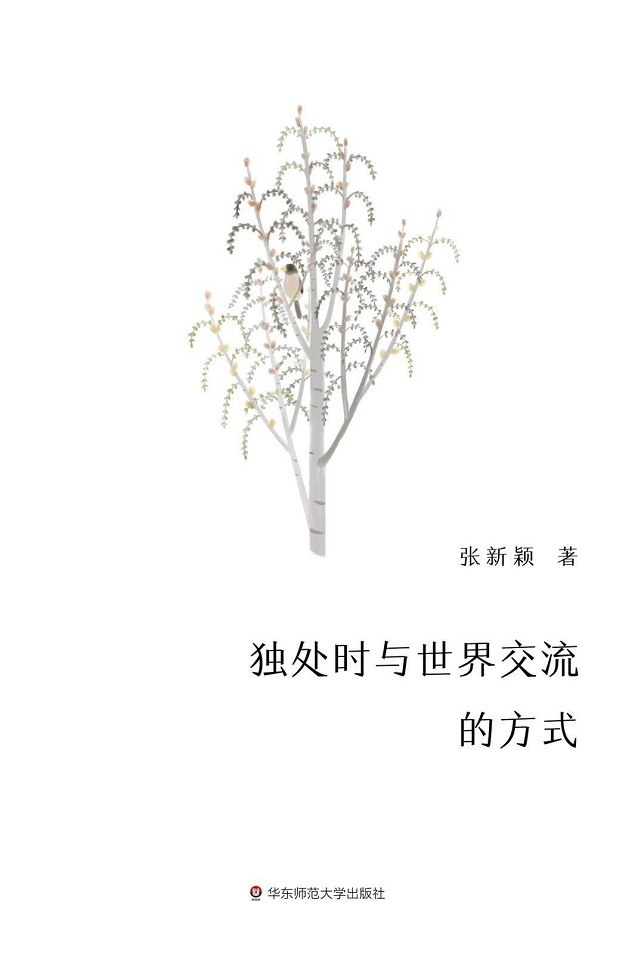
2021年,《三行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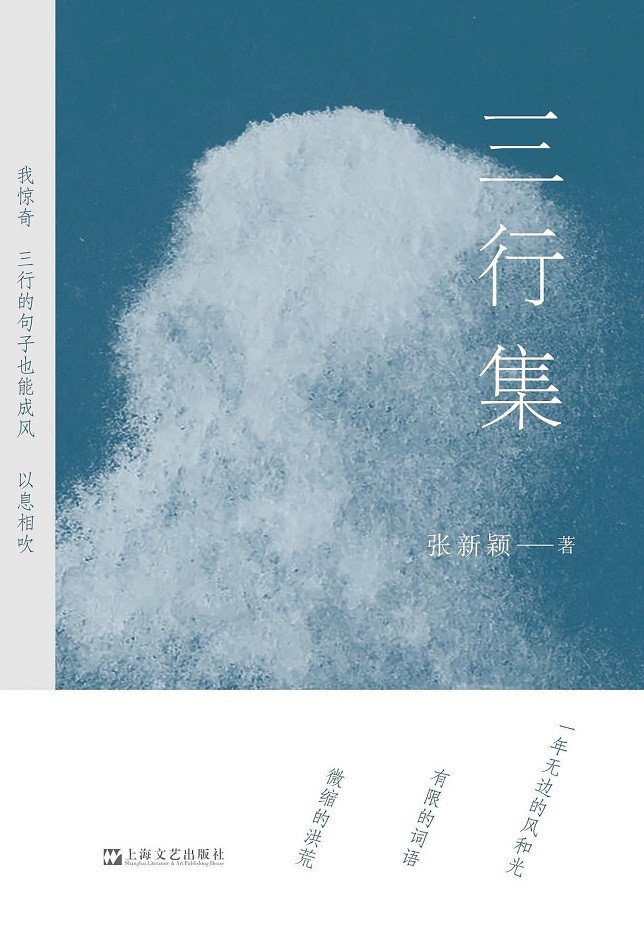
但张老师仍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表面一点说,我不想要诗人的习气;根本上,我不想要诗人的限制。我要随意、自由一点。”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他亦强调:“我实际上不是诗人……很难说我写诗具体是从哪里入手,不过最终的‘成品’,表现的好像都是日常的生活,是一些‘细枝末节’,碎屑的感觉和想法。我对自己没有限定、没有要求,就是当突然有个东西、有个时刻击中了我,不管这件事是大是小,是现实是虚幻,我可能就被触动,从而写出一首诗来。所以,于我而言,一首诗的诞生是没法计划的,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我也不会产生‘写不出’的焦虑,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罢。”
身边写诗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张新颖的回答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写的人,不少;更多?没有注意。“当然,总归会有诗歌的,会有诗人的。我们需要寻求一种表达的方式,有人选择了‘诗’。我想,或许现在身边的确有许多人在写诗,只是没有张扬,大家还不知道。事实上,诗歌与普通人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要深。一个人与语言的关系,是最长久、最亲密的关系——你很难想象比语言更亲密的东西了,它可以从你的出生陪伴到你的死亡。那么我们通过与语言的关系,不自觉地就跟诗歌也产生了一个关系。在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诗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了语言的塑造、变化等等。一般人不一定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恰恰基于此,我们是在‘享用’诗歌的。我也相信,任何一个普通人,偶尔都会迸发出某个特别的、难以命名的时刻,如果他抓住了这种近似‘诗’的时刻,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何尝不算潜在的诗人呢。需要指出的是,从现代诗的角度来讲,将‘文字的表达’转换成彻底的、生动的诗意,最好还是有专门的意识,受过相关的训练。”
悠悠此心
张新颖有《三行集》,同济大学的张生教授也在写诗:
……
终于可以随意翻阅王维的诗句
去凝神观看云林的清寂的山水
随意写下一行含义不明的诗句
只是为了怀念不停消逝的岁月
……
《新民周刊》记者和另一位复旦教授王宏图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亦展示了一首近期兴之所至、漫笔挥洒的诗作:
……
我就是宇宙的中心
甩动太古神祇的舞步
拨弄出幽雅的琴音
我就是快乐的精灵
抹着淡淡忧郁的美目
弹去昔日的万千艰辛
……
王宏图告诉记者,今年五一节前去杭州玩,朋友带他去见了几个诗人,“他们自己精心印制的诗集非常精美,和几十年前油印的册子相比,完全更新换代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系统地培养了王宏图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小王读了《古文观止》《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等书,以及数百首唐诗宋词。酷爱古诗词创作的外公,也常常在古诗词方面指点孩子。受长辈的影响,王宏图萌生了创作古诗词的念头,“几年间胡抹乱涂了几十首”。
尽管王宏图最后没有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但这方面的阅读训练使他终生受益,让他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时,潜意识里有一个古典文学的框架。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正是谈韩愈诗歌的情感结构的。
上大学时,王宏图尝试写过一些诗歌,一度还很痴迷,但后来完全转移到小说上来。正式从事创作,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创作了十来部中短篇小说后,“长篇”的计划,开始提上议程。他的文字繁复华美,被誉为“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气息”。“我是一个不灵敏的人,对事物的反应有一个‘滞后期’。因此,我表达的方式也是偏向‘腼腆’的,写起东西来也不算快。我习惯层层叠叠的长句,而非干脆利落的短句。绵密的风格,或许更吻合我本人的性格吧。”王宏图笑道。
诗歌写得好,小说也能写好吗?反之呢?对此,王宏图表示:“这当中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我觉得,诗歌写得好的人,散文更容易写好。不过,诗人对语言的感觉可能强一点,写过诗的小说家,文字还是‘不一样’的,会显得比较空灵。纳博科夫的小说很好,他的诗歌也不错,但毕竟不如小说,到不了叶芝、艾略特的高度。”
2006年,复旦中文系设立了“文学写作”专业,后经陈思和教授和王安忆教授的不懈努力,教育部在2009年正式批准设立中国大陆第一个MFA“创意写作”硕士点。近年来,王宏图一直负责着这个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我们的创意写作班,开设过新诗写作课程。过去,胡中行老师还给学生们上了七八年的古诗词写作课。开始几年,学生对古诗词写作兴趣蛮大,而近年入学的学生,很多人不再有那么高的兴致,有‘知难而退’的趋势。我是希望他们下硬功夫的,只要入了门,按照格律,你多多少少总能写几句。先不要去管好坏,不锻炼、不积累怎么行呢。”

近年来,王宏图(前排中)一直负责着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兴起。当时略有矫枉过正,很多人觉得新诗一定是好的,而旧诗人又觉得新诗语句颠倒不通,不屑与之为伍。王宏图回忆,曾经负责复旦诗社工作的黄潇(笔名肖水),“对复旦校园诗歌的复兴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个颇为有趣的花絮是:一些没有接受过现代诗训练、对新诗无感的学生,曾经与肖水的粉丝争执不下。“中国的一般读者,从小读的还是唐诗宋词,不大会去读新诗。大众对现代诗的认可,是不可能到对古诗词的那种(偏爱)程度的。新诗的兴盛发达之路道阻且长,眼下尚未抵达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完美融合的地步。”
在“猫奴”王老师眼里,喵星人百面千相,色色可爱,有的胆大莽撞,有的退缩羞怯,有的撒娇黏人,有的孤芳自赏。同理,诗歌也该如此,繁花锦绣,各逞娇颜,唯一的建议是:追求一点韵律、节奏。“诗歌的节奏,和人呼吸的节奏是相互契合的。它有一种音律的美在里边。你想,我们中国很多古诗词本来都是可以配乐唱的呀。一些诗歌仅在纸面阅读,好像显得平淡,但真的念出来了,感觉倒挺好……所以我说,但丁的《神曲》,是文学史上写作难度最高的诗歌——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典,用的是隔行押韵、连锁循环的‘三连韵’,一万四千余行,内容那么丰富,有抒情、有议论。总而言之,诗人可以不被韵律束缚,但完全不讲究节奏、不讲究语言的质感也是不对的。”
很多文学写作,其实常从诗歌入手。王宏图发现,“相对小说、散文,诗歌所指的对象不是那么明确,有种朦胧的美感。而学生青春期的感情,最适合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了——它比较‘悬空’,不需要通过非常复杂的叙事手段……虽然到后来诗歌中的叙事因素也是重要的”。提及“叙事”一节,王老师又突然记起,今年有个学生提交的毕业作品,恰是一部叙事诗,最终“学校让他通过了”。
交谈中,王宏图分析到,这一轮“诗歌热”的形成,大抵离不开以下三点:一是网络催化了“天赋诗权”的时代。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诗歌借助网络及BBS、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的“草根性”时代(余秀华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二是上世纪90年代起,剧烈的社会转型,促使大家的情绪慢慢积淀、升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火候已到,遂在近几年爆发出来了。三是疫情这种“非典型经验”的刺激。二战的时候,英国读诗者甚众。也许,和平繁荣,只道寻常,灾难临头,诗歌解忧。当曾经的井井有条变得岌岌可危,人们转向诗歌传递安慰,勾连感情。“诗歌永远是勾连感情最好的办法之一。不然为什么以前我们通常给恋人写情诗,而不是写小说?这是人类原始的冲动,所谓不忘初心也。只要这份感情是真的,一个碎片,一个瞬间,它就是能打动你。”
多年以前,王宏图参加过一次诗会,他敏锐地察觉,身处各个社会阶层的诗人都有,“这点与小说家有所不同”。而诵读诗歌的时候,众人自然形成了一股“气场”,“读散文、读小说,不一定有这样的气场、这样的效果”。创作者的多元,独特载体的加持,让王宏图看好诗歌的未来——“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诗歌。”
昔影难追
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诗歌。但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自然界的基本元素,比如人的基本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并且,渴求愈热烈,呐喊愈响亮。
于是,我们很难不去追忆上世纪80年代。以顾城、海子、北岛为代表的诗人们,在一个充满改变和未知的世界,将理想和使命都投射进了诗歌里。

顾城

北岛
人近古稀的于坚,至今依然怀念尚义街。“那时候,昆明尚义街六号吴文光(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作品有《流浪北京》)家的、由云南大学一些文学青年组成的文学沙龙,正处于狂热时期。我们留着长发,跳迪斯科,酗酒……在‘主动疯狂’(金斯堡语)的边缘,大多数人都穿灰色中山装的城市里,我们看起来就像疯子或逃犯。讨论诗歌,深夜步行穿过整个昆明,又在黎明的硝烟中散去。”

于坚
尔后,于坚写下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尚义街六号》,写下了《0档案》《飞行》等作品,还出版了《诗六十首》《于坚的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便条集》。他的《诗集与图像》《棕皮手记》,影响了当代很多诗人的创作。
身为中国诗坛“第三代诗歌”的领军人物之一,于坚在诗歌写作上代表了南方、昆明、口语、日常生活、反抗遮蔽、拒绝隐喻、回到事物本身、诗言体、诗歌领导生命……他的诗被反复讨论、争辩,既被视为“口水”,亦被视为不朽的景观。
在1985年以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尚义街六号灰飞烟灭。而退休前的于坚调入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课、带研究生、创办刊物《诗与思》、创建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他想在学生中培养“后西南联大诗人群”。
近年,于坚出版了很多散文集,也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小说作品。他还举办过摄影展览、拍摄过纪录片。
今年3月,《漫游:于坚诗选2011—2021》出版。

67岁的欧阳江河,也在今年出版了《宿墨与量子男孩》(收录了2018—2022之间的主要诗歌作品)、《删述之余》(1985—2021诗歌自选集)。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坦言,“80年代被浪漫化了”。“确实,没有个性的‘好诗’(它们的词汇、语法、情绪已经被反复写过)泛滥的情形,在那时还没产生。但80年代一定要在它一去不返后,才会勾起人们的乡愁。不同人的回忆是不是事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把自己现在成为不了的那部分投射在叙述里,自我感动,自我神化。我对这些总的来说比较警惕,兴趣也不大,但不得不承认,8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在战争年代、自然灾害年代、政治动荡年代,唱主角的都不是诗人。80年代之所以给人幻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时候诗人、小说家与思想家构成了一个共同体,扮演了传奇的角色,这在中国近一百多年里是仅有的。80年代的历史形象和80年代的结束有很大关系,大历史的突然介入,强行终止了这个时代,在这之前,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小历史就是大历史,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大历史和小历史是不同的。我个人认为80年代的传奇性和狂欢性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个大历史,它只是散布着大历史的氛围和气味,实际却属于一个漫长的历史过渡。然而80年代的无数小历史所构成的幻觉,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耗尽其能量,我们每个人可能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还没有结束的、残余的80年代。”
“80年代构成了我写作很重要的一部分,1984年的《悬棺》可以视为我的诗歌起源,1987年的《玻璃工厂》《汉英之间》一直传播得比较广泛,后来1990年的《傍晚穿过广场》、1994年的《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则是关于80年代在不同意义上的终结,也是我的转型之作。……为什么生活在消费时代的我们会这样缅怀80年代,因为它爆发出的文学的、精神的能量,曾极大震撼了中文和使用中文的十几亿人,让人们短暂获得了语言和心灵的抗体。不管我们后来怎么看80年代,我们都要感恩这点。”
花甲之年的西川回忆:“我是在(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认识的骆一禾,但是海子并不是五四文学社的。他是快毕业的时候,给中文系的《启明星》杂志投稿,杂志的负责人沈群看了他的一组诗歌,就跟我讲,海子的诗写得好。我通过沈群认识海子,海子、骆一禾和我,后来就来往比较多了。”
西川眼中的骆一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文学的理想,对于国家的理想,对于生活的理想,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生活,他都有自己的想法。骆一禾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是一种气质,一种文化气质,一种对世界的关心,一种问题意识。”海子则是“干干净净,平易可亲,使人想跟他呆在一起”。“那会儿我给另外一个人写信,说海子将来一定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是的,我愿意用‘天才’来形容海子。他写生活,写家乡,写历史转折大背景里产生的稀奇古怪的想法,写出了中国农业文明的挽歌,抓住了别人抓不住的问题。”

青海省德令哈市,海子诗歌陈列馆
风华正茂的年纪,“北大三剑客”最感兴趣的,只有写诗和读书交流。大伙儿去五四操场边的“燕春园”喝酒,毕了业挨家聚会,不嫌麻烦。他们谈论着黑格尔、康德,憧憬着但丁的《神曲》,奈何好景不长——1989年3月,海子在秦皇岛山海关卧轨自杀;5月底,骆一禾过世。“骆一禾28岁,海子连25岁都没有。海子选择自杀,骆一禾是生病去世的,突发性脑溢血。骆一禾还是认为人在世上,应该好好地生活。”

骆一禾
大学毕业后,西川去了新华社工作,在全国各地奔波。他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看也看不完,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传说、民俗。陕北吕梁旷野里的风,风里断断续续的歌声,山西黄河风陵渡浩浩荡荡的东流水,千米长的铁桥上独他一个人,“你知道,这种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冲击。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还是太有限了,做了记者,漂泊社会,不断地在绿皮火车、长途汽车上颠,把我的学生腔全颠没了”。

左起:西川、唐晓渡、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 王瑞芸、臧棣,1990年代中期,摄于北京。
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面前,“文学”一度坠入谷底。“我的东西越写越没人看。别人看不懂,我还是继续写下去。……我的诗好不好,这世上其实只需要四五个人明白就够了。马尔克斯说,作家写作可以获得的最大好处是:一个经过写作训练的头脑,能够一眼认出另一个被写作训练的头脑。”
现在,西川的诗歌早已得到国际文学界的肯定。更难得的是,他始终“行动”着:从写作到翻译,从大学任教带研究生到通过互联网参与视频音频节目,普及诗歌审美。哔哩哔哩上有《西川的诗歌课》,他如是解读自己的动机和目的:“通过诗歌,我们和世界保持私人的关系,这是一种有温度的、有弹性的、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关系。诗歌充满不稳定、不安与深不见底的幽暗之物,需要读者认真体会,体会的结果,或形成自我审美的革命。对写诗的人来讲,就是推翻过去定型了的自己,推翻那个如果不控制就向庸俗滑过去的自己。”
谓我何求
我们读诗写诗不是因为它好玩。
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
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
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
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
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
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死亡诗社》

20世纪初的中国,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经验摧枯拉朽般袭来。当旧体诗词的表述方式、词汇体系、情感抒发等已难滋生新的可能,同真实生活间撕裂出愈发明显的鸿沟,汉语诗歌渴求一场变革。
从“诗界革命”时期“我手写我心”的呼吁,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须言之有物”“去陈词滥调”的主张,“新诗”之“新”,须体现于经验内容和语言方式两方面。坦白讲,探索之路艰难曲折,有目共睹:第一本新诗诗集《尝试集》青涩乃至幼稚;而中国近现代翻天覆地的历史激荡,也使得诗歌语言频繁地被宏大话语所征用收编;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充满先锋精神和西方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浪潮注入活力,为今日的汉语诗歌写作奠定根基,然其艰深晦涩处,也在某种程度上排斥了更广意义上的理解与对话。综上,人们发现,欲使诗歌真正重回C位,“术”上仰仗手机移动端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助力,“道”上等待汉语新诗自身的成熟壮大——百年摇摇晃晃的反叛、摸索、吸收转换之后,如何在当代语林中树立对当下生活有效言说的参天巨木。
诚然,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们大可以做音乐、拍电影、写戏剧,诗歌似乎不过是迷花眼的无数“文艺选项”里的一条。但是,这个错彩镂金又千疮百孔的尘世,其实依旧需要诗歌的点缀与抚慰。诗歌是“无用的”,它不能抵挡一把匕首、一颗子弹;它又是“有用的”,足以用来抗衡狂热的煽动、虚无的挫败、现实的荒谬与颓丧,抗衡逼迫我们变得枯燥乏味、变得麻木不仁的一切。
2013年,利物浦大学的研究者就诗歌和散文对于人脑神经元活动的改变做过分析,他们认为,文本越复杂越棘手,大脑语言中心的反应就越强烈,因为它们在试图理解其含义。数年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丹尼·W·林格内戈罗(Danny W. Linggonegoro)亦撰文,称“医师们渐渐开始明白,在医学中,语言和人性表达的地位突破了那条模糊的边界——医生和病人并非只能讨论治病的疗程。‘血氧含量’‘药物使用规程’和‘外科干预’这类适用范围有限的词汇或许会导致医生和病人之间难以互相理解,乃至会阻碍病人精神层面的痊愈。医生们正学着突破这些限制沟通,他们尝试运用新的工具,比如诗歌”。
研究人员已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证明,背诵诗歌可激活大脑中的主要奖赏回路,也就是中脑边缘系统通道(mesolimbic pathway)。音乐亦能做到这点,但诗歌引发的大脑回应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具体机制仍不明确,诗歌、音乐等非药理性的辅助疗法,仿佛缓解了疼痛,从而减少了阿片类药物的给药量。
来自马拉尼昂大学(University of Maranhão)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随机临床试验,被试共65人,均在一家癌症治疗中心接受治疗。试验旨在研究播放音乐或诗歌时,被试的疼痛、抑郁和希望指数变化。结果显示,两种艺术形式的辅助疗法都能减少被试的疼痛和抑郁指数,且程度类似,然只有诗歌能够增加被试的希望指数。比如,聆听了克劳迪娅·金塔纳(Claudia Quintana)的诗集《偶数行》(Linhas Pares)中的几首诗后,一位被试称,“我觉得心中更平静了。那种极度的痛苦和悲伤消失了。这些诗句十分重要,它们告诉我自己并非孤独一人”。
第九次希波克拉底诗歌与医学年度专题研讨会(Annual Hippocrates Poetry and Medicine Symposium)上,林格内戈罗的导师、医师、诗人拉斐尔·坎波(Rafael Campo)和诗人马克·多蒂(Mark Doty)皆感叹道,当药物起效、疗程结束,病人仍然需要一段精神治愈的时间。尽管每天读一首十四行诗不能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但它也许可以帮助预防糖尿病倦怠——也就是糖尿病人对控制病情感到精疲力竭的心理状态。
简言之,科学为证,生理上、心理上,优秀的诗歌确有“抚慰”之能。倘若按照现在的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又名耳音等,指人体通过视、听、触、嗅等感知上的刺激,在头皮、背部或身体其它部位产生的奇特愉悦爽感)来看,诗歌绝对算是一种颅内极致体验了。
除不啻一剂迥异于俗烂心灵鸡汤的良药外,优秀的诗歌也可以是尖刀,是冰与火的洗礼。即便你不需要所谓“虚妄的温暖怀抱”,你还是能在诗歌宇宙里找寻到自己的位面,发散自己的思考。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表示,诗歌萃取了人类思想、感觉和经验的精华,因此,若他只能在余生中选择最后一本书来读,他会挑一本上万页的、集合全世界诗歌的“最厚的诗集”。“我会尽力去记诵这些诗作,这会让我剩下的生命充实且快乐,哪怕我会活到一百岁。”
历史长河漫漫,你我沧海一粟。而所有那些踽踽独行的迷茫、愤懑、寂寞、释然,所有那些猝不及防的喜悦与悲伤,所有那些难以归纳的幽微情绪,俱都能够召唤一首诗歌的降临。渺小有时,神圣有时,我们咏叹。在这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面前,“解法”不重要,“存在”很重要。(张英对本文也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