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安忆闲聊上海
杨锦麟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上海阿婆总有几分势利,街上弥漫着消费主义的味道,弄堂流传着市井八卦。但在知名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里,上海的弄堂是无比性感的。我在8月27日腾讯视频播放的脱口秀节目《夜夜谈》中,请来了王安忆,让她和我聊聊上海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男男女女们。
众所周知,王安忆小说的题材有三大块:文工团题材、知青题材、上海题材,其中知青题材给我的印象最深。王安忆是一名擅长描写情欲的作家,有人说张贤亮的情欲描写非常狂野奔放,而王安忆的情欲描写虽然看起来含蓄,却非常入味,让读过的人有一种文字入心的感觉。很难弄清这种欲说还休的风格,和王安忆成长于上海这座城市有多大的关联,但是无疑在其广为流传的长篇《长恨歌》中,上海这一题材,成为她小说中最为人所知的标签。
我喜欢《长恨歌》,从头到尾读过四遍,细腻笔触下男人和女人的缠绵悱恻,老上海弄堂中散发的淡淡忧伤百转千回,无一不彰显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风貌,所以我很好奇王安忆本人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一种怎样的理解?
然而她跟我说,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太熟悉,反而会缺乏了解。她其实是很晚才动笔写《长恨歌》,刻意和上海拉开了点距离,比较客观地去看它。
《长恨歌》之所以选择写上海的弄堂,是因为王安忆想要表达的就是夹杂着小布尔乔亚的优雅,讲究情调、世俗、实惠的小市民生活文化,而小市民的生活空间就是弄堂。只不过她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建成和外来资本有很大关系,即便是小布尔乔亚精神,也是外来文化侵袭的一种结果。
一说到上海,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争论总是经久不衰。王安忆觉得很多人对上海人有成见,比如上海男人是小男人,会做菜、会带孩子,女人很作……其实这只是因为上海男女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但是所谓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上海的女性得到平等待遇的代价就是要自己赚钱养家,所以上海的女性相对更为独立自主。而“上海”,很大程度上还是“都会”的代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真正可以完全称得上是“都会”的城市,只有上海。“都会”表明这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型城市,而是一个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商业型城市。所以上海的女人很会“发嗲”,善于取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江南的地域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上海的女人因为身处消费社会对物质安全感的一种渴求。
“时髦”是形容上海人的另外一个关键词。物质匮乏的年代,买布需要布票,大家穿不起衬衫,上海人就发明了一种“假领子”,即便是在物质严重缺乏的年代,上海人也在最大的程度上维护着自己的体面。王安忆解释上海人的这种气质,可以说是很“俗“,也就是很务实,一点都不虚无,但是其中蕴含着对生活不可遏制的热情。这是因为上海是一个没有什么历史的城市,五口通商之前还是一个小渔村。所以上海人很少忧伤,因为往往有历史才会忧伤,上海人对生活始终充满着希望和热情。
不过也正因为没有历史,王安忆出人意料地认为上海这个城市的内心比较粗粝,因为当年来上海的人,多半没有好身家,拎个皮包就出来闯世界。当年她外公家在杭州败落不堪,迫不得已才来到上海打拼,生下她的母亲,像这种破产后来上海找机会的人不在少数。
刚说完上海的“粗粝”,王安忆又跳出来一句更让我惊讶的话。她其实一点也不喜欢上海,至于不喜欢的原因,则是因为她小时候随父母从南京部队迁移到上海,一点都不会说上海话,从那个时候埋下了阴影。不过现在随着全国其他城市的崛起,尤其是北京越来越强势,会讲上海话的优越感也就渐渐消散了。可能怎么保护上海方言,才是当下更紧迫的话题。(本期节目已经在腾讯视频上线,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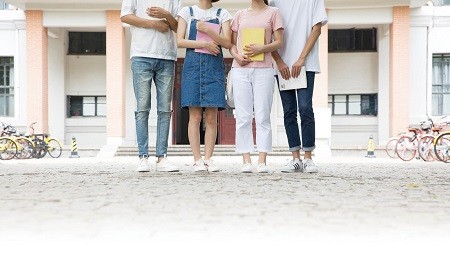


(1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