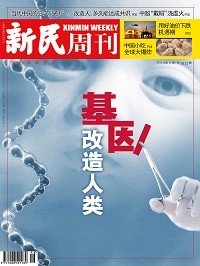噪音和合唱团
1869年,一位美国的自然学者来到了优山美地公园玩耍了一番,他看到瀑布山川也看到了很多和他一起来的游客。在日记中,这位学者说,游客们来到公园,就知道抓鱼嬉戏,他们面对大自然为什么不能“虔诚地静默”呢?为什么不能倾听一下鸟鸣风声呢?如果这位学者穿越回来到今天的游览胜地转一圈,他可能更受不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及人们不停拍照不停吆喝放出的噪声。
有科学家说,我们对他人发出的噪音更为敏感,是因为我们无法“关掉”别人的声音,我们能够关掉自己发出的声音,比如将手机调成静音等等,当我们并不掌控关掉别人声音的“开关”时,我们就更焦虑更烦躁。
北京的景山公园虽然比不上优山美地,但也可以“静默”一番,看看皇宫,看看崇祯上吊的歪脖树啥的。最近有一条新闻说,景山公园里有53支合唱团,他们使用乐器和扩音设备练合唱,最大音量可以达到130分贝,相关部门出台一条规定,责令合唱团发出的声响不得超过90分贝,超过三次予以警告,超过十次就驱逐出去。
我有很多年没去过景山公园了,但坐在家里就能领略合唱团的威力。我家楼下有个小广场,每天都有合唱团在活动,他们使用劣质的扩音设备,我近距离欣赏过他们的演出,听不出任何美妙的和声,只觉得聒噪。在这个小广场上,还有两位独唱艺术家,一位长笛爱好者,都在面前摆上麦克风。广场边上有一溜儿商店,德州扒鸡店不断播放录音带,宣传德州扒鸡的悠久历史,哈尔滨红肠商店也有个大喇叭,不断宣扬哈尔滨红肠是多么好吃。
据说,巴西城市萨尔瓦多非常吵闹,天主教教堂和新来的基督教教堂争夺信众,教堂大门永远敞开,布道和圣歌都用大喇叭向外扩散,神职人员讲话完毕,“传道DJ”就继续工作,用音乐来进行这场灵魂的争夺战。我们的合唱团多年来一直在演唱“我的祖国”啊“保卫黄河”啊这类歌曲,按理说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为什么合唱团还要在音量上下功夫呢?后来我意识到,合唱团的对手是扒鸡店和红肠店,对手是无边无际的消费主义。
“一战”之前,纽约城管清除城市噪音的第一步,就是取缔露天市场的麦克风,不许用麦克风招揽客人,而后,报童、流动的小商贩、玩滚轴溜冰的、踢铁罐子的小孩子都受到了限制。当时的一份研究说,打字员在嘈杂环境下会多出7%的错误,会多消耗19%的卡路里。资本主义的城市管理者为了生产效率,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噪音的规定,结果发现,如果没有商贩叫卖儿童嬉戏,城市交通的巨大噪音更让人受不了,卡车、小汽车、哈德逊河上的驳船汽笛声、建筑工地的机器声,都在显示1920年代的纽约是世界的中心。
如此我可以这样理解,中老年合唱团在公园里演唱革命浪漫主义的歌曲是为了对抗现在这个过于商业化的庸俗的小时代。反省一下,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提着一个录音机,放出迪斯科音乐,招摇过市,那也是宣示一种“存在感”,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销声匿迹了?有一天晚上,一位年轻朋友带我造访了北京五道营胡同里面的一个摇滚俱乐部,那是北京的老城区,胡同里有公共厕所,有穿着背心裤衩乘凉的老大爷老大妈,摇滚现场就在一处平房改建的club里。只要有演出,邻居们必然报警,警察来了,摇滚乐手们就更兴奋。如此缠斗多次,俱乐部建了一道隔音墙,给邻居们一些补偿,终于相安无事。
我买了门票买了酒水进入摇滚现场,没呆十分钟就跑了出来。我上岁数了,宁愿去公园听老年合唱团,也受不了年轻人的摇滚了。但这次探访终于揭开了我的谜团,当年拎着录音机放迪斯科的年轻人,并没有和消费主义结合的机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把他们的噪音商业化,扎根于老头儿老太太的卧榻旁边。
【请注意:新民周刊所有图文报道皆为周刊社版权所有,任何未经许可的转载或复制都属非法,新民周刊社保留诉讼的权利。】
※版权作品,未经新民周刊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