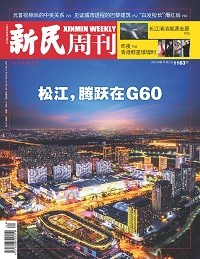煮羊头
上海民众对羊肉颇有好感,以前闻羊肉而避之不及的朋友现在也敢吃了。上海崇明、南汇、七宝以及周边的海门、湖州、太仓、苏州等,都有好羊肉值得大快朵颐。周浦和七宝的白切羊肉最有人缘,蘸面酱吃,味道端的细腻,回甘持久。青浦的烂糊羊肉,大锅煮过夜,酥而不烂,一大件上桌,蘸虾子酱油吃,我一个人可以吃一大盆。
老上海告诉我,过去不少街区都有羊肉粥店,半爿羊肉煮熟后平铺在松木板上,结冻后用快刀切成纸片样薄。切羊肉是需要一点技术的,临街操作时带有很强的表演性。羊肉汤烧粥,一点也不浪费。热气腾腾的羊肉粥加一盆白切羊肉,鲜、香、暖胃充饥,是劳动人民的美味。红烧羊肉多在面馆应市,凌晨烧好,在大砂锅内保温,客人起叫后用小碗盛满上桌。一碗面,一碗“红羊”,过桥制式,食客先用羊肉佐“小炮仗”(瓶装土烧),再用羊肉汤拌面,经济实惠。
北方天寒地冷,冬天吃羊肉是题中应有之事。北方人爱穿羊皮袄,所以淮河以北的羊肉都是去皮销售的。南方人爱吃带皮羊肉,北方人看了表示不懂。老北京在涮羊肉之外还喜好酱羊肉,并出了个以此著称的月盛斋。还有烧羊肉,梁实秋在蜗居台湾几十年后还一直垂涎三尺地回味这一民间小食。“北京烤羊肉以前门肉市正阳楼为最有名,主要的是工料细致,无论是上脑、黄瓜条、三叉、大肥片,都切得飞薄,切肉的师傅就在柜台近处表演他的刀法,一块肉用一块布蒙盖着,一手按着肉一手切,刀法利索。”读这段文字可以想象老北京人如何伸长了脖子围观的情景。
老北京的烤肉季和烤肉宛,是烤羊肉行当的双子星。十几个吃客围在一个炉子四周,一条腿踏在长凳上,一双筷子在“支子”(一种铁丝编成的网架)上面翻动,吃一块烤羊肉,喝一口二锅头,江湖豪情,令人神往。
北京人还吃羊头,白煮的。听上去有点可怕,不过我有心理准备。小时候读过一本普希金编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有个胆子很大的旅行者来到西伯利亚某小村庄,听说当地有一恶魔,每夜必来闹事,骗吃骗喝,还要一个姑娘陪睡。旅行者有意为民除害,当夜就挑灯坐在魔鬼出没的羊棚里,一壶酒,一个白煮羊头,自斟自饮,从容淡定。一阵怪风吹来,烛影摇晃,魔鬼如期而至,见屋中坐着一小帅哥,一愣。旅行者拿起羊头跟魔鬼说:“你算什么东西?以后再来捣鬼的话,就叫你跟这只羊头一样。”说完手一紧,羊肉被他捏出淋漓的水来。魔鬼见了大骇,掉头就跑,从此全村太平无事。其实那个旅行者手里捏的不是羊头,而是一只煮烂的大萝卜。
上海人对动物的脑袋向来情有独钟,鱼头、猪头、鸡头、鸭头、鹅头,都是下酒妙品,不过我没听说过有人爱啃羊头。最近被朋友拖至一家酒店吃火锅,紫铜锅端上来,赫然一只全羊头坐窝锅中,瞑目作沉思状,却依然霸气十足。不一会,汤沸卜卜,诸位兄弟紧搛筷子向羊头猛击三番,羊耳、羊眼、羊唇等活肉一眨眼就没了。方才还在迟疑的我,赶紧挟了一块面颊肉试味。咦,味道不错啊。鲜嫩自不必说,还有特殊的香气。
再环顾四周,无论老叟还是美眉,每桌均有一只羊头盘踞中央,酒酣耳热之时,个个眉飞色舞。少顷,锅中只有白花花的湖羊头盖骨独立寒冬,活像一个考古现场。这情景,至今想来仍十分发噱。
洪长兴以涮羊肉闻名江湖已久,他家的葱油饼其实特别好吃,用羊油起酥,层层叠叠,香气四溢,一口饼一口羊杂汤,特别带劲,多吃一只也不会腻滞。(撰稿 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