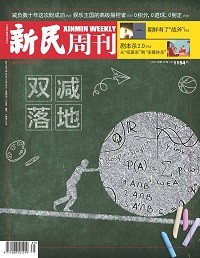我们业已习惯的外来词
给外来的物件起名字,最简单省事的,便是安个现成名。比如古代中国人图俭省,习惯这么起名字:西域来的,都给个前缀,叫“胡什么”,如胡瓜、胡豆、胡萝卜、胡椒、胡桃、胡饼,那都是西边来的。如果是海外来的呢,就叫“洋什么”,比如洋烟、洋葱、洋芹菜、洋芋,那就是海外发来中土的。
也有音译的,而音译也分辞藻好坏。比如鼻烟这东西,英文叫snuff,清末大家都好闻这玩意,就给起个译名叫“士那夫”,纯是音译。词也不算好看。烟草tobacco,在菲律宾种得甚好,中国士大夫听了,按字索音,就译作淡巴菰,这就属于用心了,比士那夫好看多了。乍看字眼听读音,会以为是种清新淡雅、适合熬汤的菌类。
咖啡,英语写作coffee,读音更接近“柯非”;法语Café,跟汉语里“咖啡”两字更像些;其本源是阿拉伯语的قهوة :读音像是“咖哇”,“植物饮料”。但“咖啡”两字,的确比“柯非 ”、“咖哇”好听又好看。
咖啡里头的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è latte,法语写作Cafe au lait,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和法语lait,都是牛奶。拿铁和欧蕾说白了,最初就是“牛奶咖啡”,但稍微想一想:中文读做拿铁,听来范儿十足,是给成年人喝的;嚷一句“伙计来杯牛奶咖啡”,立刻落了下乘,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
粤语许多翻译比较随意。比如把salmon翻成三文鱼,把sandwich翻成三文治,很容易让人疑惑:三文治和三文鱼有没有远亲关系?粤语里某种水果叫士多啤梨,不知道的会以为很神秘,细一看是草莓,再一想就明白:strawberry,直接音译过来啦。葡萄牙人拿来做早饭吃的煎蛋omelette,粤语里叫做奄列;当时的上海人则用吴语念做杏利蛋。欧陆面包toast,广东人叫做多士,上海人则翻成吐司。
也有些翻译,年深日久,已经觉不出是翻译了。比如,唐僧所穿的袈裟,其实是梵文काषाय,读作kasaya。莳萝则是波斯语。比如我们熟悉的琉璃,段玉裁注解《说文》时说得明白:最初叫璧流离,“胡语也”。比如我们日常吃的葡萄与苜蓿,都是张骞出西域带回来的。《汉书》都还分别叫做“蒲陶”和“目宿”。最不显的,比如印度有一种墓式建筑,स्तूप,stūpa,中文翻译很多,其中一个翻译是卒塔婆,慢慢就成了塔——中国的佛塔,就这么来的。虽然现在说起来,宝塔、佛塔,没人会觉得那是印度来的了。
类似地,读《封神演义》的诸位一定好奇过:闹海的哪吒有两个哥哥,金吒,木吒。按排行,他该叫水吒,为啥叫哪吒?因为哪吒其实也是印度来的。说多闻天王俱毗罗有个儿子,名字大概类似于Nalakūvara,在中文的翻译,叫做那吒矩钵罗。南宋时一度被叫做过那叱太子,后来就演化成我们所知道的哪吒了。
所以乍看之下,当代中文外来语颇多,大家会大用日语中的词汇如“人气”,会用英语词汇“我get不到你的笑点”;但稍早一点,如上海话“十三点”,如雪茄,如吐司,如三文鱼,如拿铁,也都是外来语;更早一点,如塔,如袈裟,如和尚,如葡萄,如苜蓿,如哪吒,也都是外来语。只是已经深入我们的语言习惯,丝毫不觉诧异了。
世上生命力旺盛的语言,从来都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外来语随处可见。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觉得很可以代表中国民族风味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茉莉这个词,也是外来的:出自梵文मल्लिका,读作malika。(撰稿 张佳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