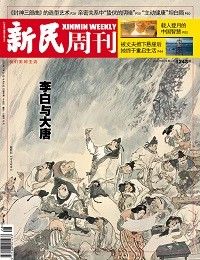杨德昌的“重构”
一位已逝的电影作者的展览,明看是展示这个人“成为自己”的“证物”,骨子里,却有盘根错节的故事有待重述。
“一一重构:杨德昌”是嵌入了几重意义的题目。《一一》是杨德昌生前收获最高认同的电影,又是遗作,两个一字的文化意蕴,如顺手拈来又是柳暗花明。切合了被引述的杨对怎样说好一个家庭故事的追求:它简单得无可再简单了,但它又是复杂中的复杂,恰如比“一”只多出了一个笔画的另一个字:人。
“一一”指涉的,还有跟展览有关的另一重意思:要自上万件杨的遗物中整理出一位电影作者的精神面貌,便得决定哪些比哪些重要,或哪些比哪些适合。“重构”如是提供了取舍的标准,只是“重构”什么又让过程变得复杂。
正如前述,客观来看,自是合乎最多数的利益的议程最宜优先,但当被重构,“重述”的这一位是如此独特、唯一,并因此沾上争议色彩,其主观一面所造成的,对于创作动能、个人际遇,以至社会关系,极可能并不是客观叙述就能把故事的千丝万缕理出头绪。
杨德昌的映像书写常以Reflection 为“物象”,于我,可以是自我观照过程中的主客易位:反射物是外在的,但因反射而被看见的,往往是镜子照不见的内在。
不少人以手术刀形容杨德昌电影的冷冽、锋利。刀在杨的电影中大多不会缺席。它与它的使用者,均象征以小博大。第一次那样的寓意,出现在《青梅竹马》,当年的少棒英雄阿隆(侯孝贤),正是死于名字也没有的青年刀下,新旧交替的无情,由都市的建筑到人心没有两样。之后类似的大人死于年青人的刀下,还有《一一》中的胖子杀了为人师表的程礼华。更脍炙人口,自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戮进小明身体里的那一刀。除了刀,还有枪。《恐怖分子》《麻将》里,都有枪声响处血溅当场。
在杨七又四分之一的银幕作品中,烙有危险标记的占了五部。只是,刀/枪作为武器,与手术刀作为救人工具的差别,在于前者服务个人(利己),后者服务大众(利他)。杨的电影风格,既有手术刀的象征性,说明其令人不安的手法,也旨在带出忠奸对错二元对立的辩证,而不是借渲染暴力,推崇英雄崇拜。
有趣的是,制造英雄崇拜才是商业世界的金科玉律。电影固然没有例外。杨德昌从不逃避面对男性的无力感如何通过暴力来发泄,所以,刀和手术刀的一体两面,便是呈现即批判。这便回到尖锐性作为杨德昌的特质,与他在华语商业电影市场的处境之吊诡所在:会不会他的才华愈被看见,他的电影便愈不容易被看见?“一一重构”背后若有什么值得“重构”,我会说是杨德昌有生之年作为华语电影作者,为什么总是在思想上与华语社会“格格不入”。
因为他(一)相信讲真话比讲别人想听的话更重要;(二)创作不只要做自己没做过,而是别人也没做过的;(三)要独立就要能承受孤独;(四)纯真是最长久的陪伴;(五)自我启发对比建制教育才是真的学习;(六)无须属于这也不用属于那;(七)兴趣赋予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并有助拥有灵魂。
所以对我来说,他的手稿(心声)比影像(电影)是这次展览中更为珍贵及值得考究的素材。只是要把文字(日记、书信、札记、文章)“一一重构”后转化成为映像做成展览,工程和心思便更见庞大。当然,这次在展览最后一个空间已见这方面的尝试。撰稿 林奕华